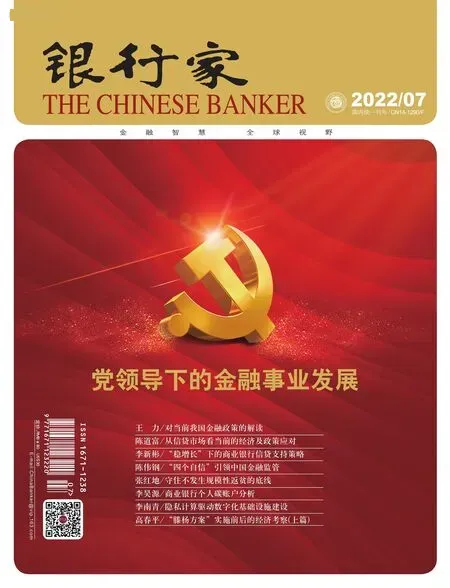刺激焦慮與增長的煩惱
王松奇
隨著2014年5月宏觀統計數據的出爐,人們對中國經濟形勢也出現了樂觀與悲觀兩種明顯不同的判斷。樂觀派認為,5月經濟有企穩跡象,根據是(1)匯豐PMI為50.8較4月的49.4回升1.4的百分點;(2)全社會用電量為4492億千瓦時,同比增長5.3%,增速比4月份上升0.7個的百分點;(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8%,比4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從環比看,5月份比上月增長0.71%。悲觀派則認為,今年前兩個季度的中國各行各業從采礦業、運輸業、制造業到服務業,除建筑業以外的所有行業都處于明顯衰退和疲弱之中,特別是考慮中國各地根深蒂固的弄虛作假惡習,單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似乎已很難得出與我們深入基層后的直觀印象相符的客觀判斷。考慮到經濟運行常常存在不確定性,因此,中國經濟是維持克強總理所說的“中高速增長”還是會繼續疲弱下行甚至出現硬著陸,仍是未定之天。
我猜想,宏觀經濟運行存在不確定性的原因在于決策層和經濟學界目前普遍存在一種宏觀決策上猶疑不定的情緒,我將之歸納為“刺激焦慮”。
那么,怎樣解釋“刺激焦慮”呢?
這是一種在宏觀政策選擇方面過度瞻前顧后引發的精神癥狀。2008年年底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出臺的4萬億刺激計劃事后遭到詬病,及至去年3月政府換屆剛剛3個月,即2013年6月,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黃益平教授撰寫了一篇所謂的內部報告,這個報告發表在巴克萊銀行的內部刊物《全球資本客戶》“北京明信片”專頁上,報告首次用英文提出Likonomics這個新詞,在很短的時間內“克強經濟學”這個詞匯立刻紅遍全球。不管此事是精心策劃還是某個文人的突發奇想,我們從黃益平總結的所謂“克強經濟學三大支柱——不刺激、去杠桿、搞改革”,聯系到從去年6月到今年6月這一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就可看出,“克強經濟學”的提出決不會是一個教書匠拍腦門拍出來的那么簡單,因為這個“克強經濟學三支柱”恰恰同新一屆政府的所有政策選擇動作大體吻合。
不刺激就是不再出臺類似于4萬億刺激計劃那樣的強力需求拉動政策提振經濟;去杠桿在中國的主要涵義就是降低負債比率特別是降低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負債比率;搞改革就是通過體制制度條件的改革尋找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后兩條顯而易見毫無爭議,問題是第一條“不刺激”,到現在仍然眾說紛紜。
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不刺激行不行?接下來的問題是刺激到什么程度?最后是選取什么樣的政策工具刺激?這三個問題扭纏到一起就構成了本文標題所說的當下中國存在“刺激焦慮”的基本內容。
2013年3月政府換屆后,克強總理在一次講話中提出了“上限”“下限”和“底限”的說法,即通脹容忍上限為3.5%,經濟增長下限為7.5%,而GDP年增7%為底限。2013年中國GDP增長7.7%,略高于下限,進入2014年,中國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于是在春季的博鰲論壇上,克強總理提出“中國不搞強刺激”。演講當天,總理的講話曾遭到某權威媒體的扭曲性解讀,如該媒體說,克強總理演講后,“不刺激的信號立即傳遍全球”。我不知道該媒體記者的中小學語文是怎么學的?“不搞強刺激”怎么會成了“不刺激”?這明明是說肯定要搞刺激只是刺激程度不要太強而已嘛!那么,中國為什么一定要有刺激政策出臺呢?原因在于中國經濟本身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而且就是成熟的市場經濟,看看美國看看日本看看歐盟,該刺激時就刺激,沒有哪一個國家愿意放棄發展良機。中國原本就是一個政府既主導改革也主導發展的國家,在經濟增長中存在著嚴重的政府依賴,因此,在外需萎靡不振,微觀主體缺少支出意愿時,政府再縮手縮腳不出臺有力的需求提振政策,經濟下滑的速度肯定會超過同樣無刺激政策條件下的發達市場經濟體。因此,只要經濟下滑趨勢明顯,政府就應當及時出手。至于刺激到什么程度,那當然就是使經濟增長率達于克強總理所說的“下限”之上,準確說應當是8%左右。雖然7.5%是增長下線,但考慮中國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統計造假習性,做一些統計水份剔除,讓目標數據稍高一些,似乎正好使經濟增長率接近基于資源能力和部門平衡可能的自然增長率。
在過去多年中,中國似乎始終處于一種“增長的煩惱”之中,許多國家經濟怕冷,我們卻始終處于發燒威脅之中;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常常想破腦袋在琢磨怎樣能使本國的年度GDP多增加一個百分點,而中國決策者們常常要向專家咨詢,如何讓經濟保持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即使在2014年這樣經濟趨冷傾向出現以后,我們的領導者還是矜持有加,常常用“冷靜面對經濟新常態”這樣的話語來寬慰自己,寬慰國人。但實際上,決策層已向有關宏調部門下達了預調微調的指令,這說明,在新的慣常的增長煩惱中,與其說是害怕熱,毋寧說是更害怕冷。多年來,給人們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中國GDP增長7%同西方國家GDP增速為0%大體相當,而低于7%的增速好像是西方國家的負增長一樣,因此,我們千方百計要把GDP年度增速搞到7.5%以上,7%就成了一個永遠不超越的增長底限。
摒棄“刺激焦慮”去放手刺激,為8%左右的經濟增長正名而丟掉增長話題上被人說三道四的煩惱,那么,用什么工具來刺激才能實現最佳效果呢?
我們除了已經采取的三項政策(棚戶區改造,城際鐵路和小微企業減免稅)外,最近還搞了兩次定向降準,4月25日央行對縣域農商行農合行下降存款準備金,6月9日央行又決定自6月16日起對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由于本次定向降準的機構并不包括國有五大行和一些規模較大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因此釋放的流動性總量據說也不過區區1000多億而已。
兩次定向降準,按照央行文件的解釋,一是當前流動性充裕,穩健政策的基調沒有變化;二是定向降準的目標是為了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將資金更多配置到實體經濟中需要支持的領域,促進放貸結構優化。問題就出在這兩點解釋的合理性方面。首先,當前流動性充裕的判斷并不準確。去年6月和11月的兩次錢荒是流動性緊張(盡管是短期緊張)的外在表現。流動性緊張的結構性原因是中國貨幣M2總量世界第一,至2014年5月底已達118.23萬億元,但M1余額余額只有32.78萬億,M1占M2比例約1/4左右。也就是說,真正在流通中起作用的活躍貨幣總量其實不大;其次,享受定向降準獲得可貸資金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如何才能有效保證流向“三農”、小微等金融服務供給薄弱的領域?誰來監管?有人提出,貨幣政策只管總量松緊,資金結構和流向問題由市場來解決,這種建議細想一下也不是沒有道理。我多年來一直在說貨幣政策有兩大特性,一是總量二是微調,這也大體暗含了貨幣政策不應該承擔它不該承擔和無法承擔的結構調整功能這層意思。如果硬要讓貨幣政策或央行去干結構調整方面的事,從目前情況看那就是定向取消貸款規模控制,如商業銀行五萬元以下的微型貸款不計入規模、對于農發行這種天生以“三農”為支持對象的政策性銀行不納入貸款規模指標管理等等,這樣干,貨幣政策的結構調整功能自然會顯現,我們的秀才們也不必絞盡腦汁“為賦新詞強說愁”了。
問題說開了,我們就會坦然許多,刺激不刺激?該刺激就刺激,無須用“三個支柱”說來作繭自縛;增長高或低?在有利于壓縮過剩產能不損害環境和提高可持續增長能力的情況下,經濟增速能高就盡量高些,實在高不上去就相對低些。只要這樣想了,宏觀決策者們就會減少許多畏難情緒,至于一些國外關心中國經濟問題的所謂專家學者們常發表的那些隔靴搔癢式的言論,姑妄聽之,他愛說什么就說什么,我該咋干還是咋干,畢竟,經濟學家們重視的永遠都是效果,誰說過什么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