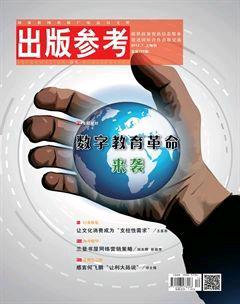情滿廿載風(fēng)雨路
周崇尚
《難忘的二十年——在習(xí)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里》一書,張志功同志以一位秘書的視角和親歷者的口吻,為我們講述了習(xí)老文革前后波瀾壯闊的曲折經(jīng)歷與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為更加細(xì)致地了解一貫低調(diào)的習(xí)老打開了一扇窗,為重新認(rèn)識那兩段崢嶸的歲月推開了一扇門。掩卷長思,感慨萬千: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習(xí)仲勛同志“一生光輝,歷經(jīng)坎坷”,既有為民族解放馳騁疆場的革命豪情,又有為國事鞠躬盡瘁的孺子牛精神;既有獨當(dāng)一面的風(fēng)發(fā)意氣,又有改革開放的超群膽識;既有蒙冤受辱的磨難傷痛,又有光明磊落的高風(fēng)亮節(jié)。習(xí)老仍為當(dāng)今共產(chǎn)黨人所學(xué)習(xí),所敬仰。
張志功同志前后曾兩次擔(dān)任習(xí)仲勛同志秘書:一是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國務(wù)院任習(xí)仲勛同志秘書;二是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在廣東省委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任習(xí)仲勛同志秘書,加起來剛好二十年。這部充滿深情的回憶錄,不同于一般人物傳記的結(jié)構(gòu)布局,而是以四字對句為小標(biāo)題,將作者跟隨習(xí)老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共分為“蒙冤受屈患難與共”“身處逆境心系人民”“葉帥點將主政南粵”等22個部分,向人們展示了習(xí)老“既是一個原則性很強又是一個人情味很濃的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形象。通覽全篇,筆者認(rèn)為:此書至少有以下四個值得關(guān)注的話題。
一是用翔實資料厘清所謂的“反黨事件”終究經(jīng)不起歷史的檢驗。
作者在開篇“蒙冤受屈,患難與共”提要中指出:“蒙冤受屈”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與八屆十中全會和小說《劉志丹》息息相關(guān)的所謂“習(xí)仲勛反黨事件”,又是一個繞不開的歷史話題。作者首先回顧了習(xí)仲勛一生兩次蒙受重大冤屈的情況:第一次是1935年中央紅軍即將到達陜北之際,被黨內(nèi)“左”傾路線的執(zhí)行者構(gòu)陷入獄,命懸一線,幸被黨中央、毛主席解救;第二次是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康生一伙誣陷為“利用小說反黨”,即所謂的“習(xí)仲勛反黨事件”。接著,作者交代了以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提出的“反對黑暗風(fēng)、單干風(fēng)、翻案風(fēng)”為引子,以時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在八屆十中全會預(yù)備會上的發(fā)言(后被編為“總72號簡報”)為導(dǎo)火索,康生一伙宣稱“習(xí)仲勛勾結(jié)劉景范、李建彤夫婦”,授意他們炮制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政治風(fēng)云瞬間突變,不僅習(xí)仲勛本人被打成“反黨分子”,被審查、關(guān)押、監(jiān)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文革”中身陷囹圄,七年沒有見過家人,而且他的一大批親朋故舊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誣陷和迫害,成千上萬的干部和群眾受到這一冤案的株連。據(jù)統(tǒng)計,受小說《劉志丹》和“習(xí)仲勛反黨集團”案株連者近2萬人。直到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發(fā)[1980]19號文件”發(fā)布了《中共中央為所謂“習(xí)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指出這是“康生等人蓄意制造的一起冤案”,“對因所謂‘習(xí)仲勛反黨集團問題受到株連迫害的干部和群眾,均應(yīng)予以平反,恢復(fù)名譽”,這起冤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數(shù)據(jù)觸目驚心,公理自在人間,是這一事件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
二是用典型事例再現(xiàn)了習(xí)老主政南粵“殺出一條血路”的生命張力。
1978年2月,備受磨難的習(xí)仲勛在政壇上消失16年之后再次出現(xiàn)在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為那個春天增添了幾多暖意。葉帥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向中央推薦習(xí)仲勛主政廣東省,并鄭重交代他說: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那里問題比較復(fù)雜,還有大量冤假錯案沒有平反,希望團結(jié)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決廣東的歷史遺留問題,率領(lǐng)廣大干部群眾把廣東各項工作搞上去。歷史把習(xí)仲勛推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他也不辱使命,帶領(lǐng)廣東省委一班人,擔(dān)當(dāng)起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以大刀闊斧的改革力度,“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胡耀邦語),創(chuàng)辦了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1979年1月,習(xí)仲勛帶領(lǐng)廣東省委,開始摸索舉辦旨在脫貧致富的“貿(mào)易加工區(qū)”的具體辦法,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贊許和支持,后來鄧小平同志一錘定音,把“貿(mào)易加工區(qū)”叫作“特區(qū)”,要求廣東“殺出一條血路來”。7月15日,中央下達了批轉(zhuǎn)廣東省委及福建省委兩個報告的文件,即著名的[1979]50號文件,創(chuàng)辦特區(qū)自此獲準(zhǔn)正式啟動。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wù)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zhǔn)國務(wù)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shè)置經(jīng)濟特區(qū),“經(jīng)濟特區(qū)”的名稱從此譽滿中外。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習(xí)仲勛在廣東改革的破冰之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愈加凸顯。正如2009年8月26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wù)院副總理張德江同志所講的那樣:“在廣東搞改革開放,是習(xí)仲勛同志一生中為黨、國家和民族做出的重大貢獻之一。”深圳特區(qū)的建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一個舉世公認(rèn)的創(chuàng)舉,充分彰顯了習(xí)老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具有的過人膽識、超前意識和生命張力。
三是用生動細(xì)節(jié)刻畫了習(xí)老在“文革”結(jié)束后撥亂反正、昭雪冤獄的政治智慧。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是我黨的宗旨。習(xí)仲勛同志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lǐng)袖”,對人民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認(rèn)為,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應(yīng)當(dāng)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去關(guān)心國家大事。人民群眾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只要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yè),順耳的話、刺耳的話都應(yīng)該聽,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才能生動活潑,熱氣騰騰。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為“李一哲案”平反,為“反澎湃烈士事件”昭雪,為所謂的馮白駒和古大存“地方主義的反黨聯(lián)盟”洗冤,都起到了別人難以替代的關(guān)鍵作用。1978年4月,習(xí)仲勛到廣東上任之初,平反冤假錯案成為擺在他面前的首要艱巨任務(wù)。經(jīng)過認(rèn)真地分析和梳理,廣東省“文化大革命”和歷史遺留問題竟有11大類之多。習(xí)仲勛同志在廣東3年期間,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使多達20萬干部群眾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昭雪。而他做這些工作的時候,他自己的冤案還沒有得到公開平反。
四是用眾人感受梳理了習(xí)老嚴(yán)于律己、寬以待人、樸實無華、樂觀向上的赤子情懷。
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中,習(xí)仲勛同志都情系民生,即便是1967年他被西北大學(xué)的紅衛(wèi)兵從洛陽揪到西安批斗時,仍然輾轉(zhuǎn)兩次上書給毛主席,呼吁“制止武斗”,建議“保護春耕生產(chǎn)”,一如既往地關(guān)注國計民生的大事,真正無愧于毛主席在延安時為其所寫的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習(xí)仲勛不僅關(guān)心、保護干部,而且非常重視人才,敢于站出來為基層干部說公道話,敢于大膽使用有才能而身處逆境的干部,最大限度地保全和培養(yǎng)了很多人。延安時期,他曾對一位要處分一個干部的領(lǐng)導(dǎo)說:“我們處分一個干部很容易,可培養(yǎng)一個干部很難。”建國初期,他堅持采用政治瓦解為主的方針,以十分慎重的態(tài)度對待民族問題,成功收服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千戶項謙的故事,不僅被人們廣泛傳頌,而且獲得毛主席的高度稱贊:“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當(dāng)年,他還成功策反黃正清、團結(jié)十世班禪大師、指示范明穩(wěn)妥處理西藏問題、三次救援王含章的女兒王權(quán)華等,這些事例都是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大手筆。在那些不正常的歲月里,他仗義執(zhí)言先后為張西銘、王超北、黃羅斌說過公道話,推薦過蘇翰彥赴香港開展招商引資的前期工作,溫暖了很多人的心田,在黨內(nèi)外被譽為“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典范”。他為人豁達大度,不記私仇,即使對那些做過錯事、甚至傷害過他的人,也都是以德報怨,從不計較。遇到事情,他寧可自己一個人承擔(dān)責(zé)任,也從不愿連累別人,常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表現(xiàn)出不怨天尤人、不叫屈喊冤、堅定不移、寵辱不驚的大擔(dān)當(dāng)、大胸懷、大境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綻放出自己寧折不彎的生命力,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鐵骨脊梁。習(xí)老寬以待人,有口皆碑;嚴(yán)于律己,毫不留情。他非常注意政治影響,對自己、對親屬、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yán)格:在廣東任職3年期間,無論上下班、開會、下鄉(xiāng)還是參加外事活動,他坐的都是一輛小面包車,堅決不坐省委配備的進口小轎車;身邊的工作人員離開時,大都被分配到邊遠貧困地區(qū);他鼓勵妻子齊心安心做基層工作,要“以事業(yè)為重,不耽誤工作,有困難自己克服”;幾個孩子也成為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有用之才。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兒女們眼中,習(xí)老五個方面的品質(zhì)最值得繼承和學(xué)習(xí):一是學(xué)他做人,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并且要求孩子也這樣做;二是學(xué)他做事,視革命業(yè)績?nèi)鐭熢疲瑥牟痪庸Γ瑥牟粡垞P;三是學(xué)他對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執(zhí)著追求,身處逆境,從不言棄;四是學(xué)習(xí)他的赤子情懷,“像一頭老黃牛,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著。這也激勵著我將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服務(wù)的事業(yè)中去”;五是學(xué)習(xí)他的儉樸生活,“有時幾近苛刻”,“這樣的好家風(fēng)我輩將世代相傳”(摘自習(xí)近平總書記2001年寫給父親的拜壽信)。在女兒橋橋眼中,習(xí)老是“一個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情味十足讓人倍感親切的普普通通的人,同時,更是舍棄了自我,把一切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令人敬仰的人”。在秘書眼中,習(xí)老無論大小事情、方方面面,都保持著嚴(yán)謹(jǐn)認(rèn)真的工作作風(fēng),還以實際行動告訴身邊的人怎樣做人:那就是實事求是,不虛不浮,實話實說,堅持真理。
周恩來總理說過:“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了后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習(xí)仲勛對他的孩子也說:“我沒有給你們留下什么財富,但給你們留下了個好名聲。”堂堂正正做人,正正派派做事,這是習(xí)老那一代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是習(xí)老那一代人所踐行的革命信仰,更是比生命還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本回憶錄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dāng)年的政治風(fēng)云變幻,成功地傳達出作者對習(xí)老的濃濃深情,那發(fā)自肺腑的景仰和血濃于水的情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也產(chǎn)生了極大的反響,是一部頗有功力的精品之作。 (作者單位系中國出版博物館籌建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