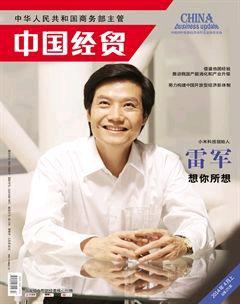借鑒他國經驗推動我國產能消化和產業升級
張茉楠
金融危機開啟了“大調整”的序幕,世界經濟結構將被迫做出調整,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去杠桿化”正在改變全球的需求結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疲弱的消費需求嚴重制約了發達國家的復蘇進度,其家庭資產負債表遭受嚴重損害,居民消費總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資產的去杠桿化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既往的負債型消費模式。受外需萎縮、貿易壁壘、通貨膨脹、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出口產業受阻,這也激化了外需產業的“產能過剩”矛盾。
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頑疾
產能過剩并非此次危機獨有。對于中國而言,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頑疾。歷史上,我國曾出現過兩次產能過剩:一是1996~1999年,出現產品積壓,工業企業開工嚴重不足。據統計,1996年末全國28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有4成處于閑置狀態。國家統計局1998年對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普查,多數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輪產能過剩問題凸現。國家發改委統計,我國有19個行業產能過剩,其中鋼鐵、電解鋁、汽車等行業問題突出,水泥、電力、煤炭等行業也潛藏著產能過剩問題。
從深層次看,我國的產能過剩既存在市場性“過剩”,也存在體制性“過剩”。除了經濟周期性波動帶來的產能過剩外,我國工業產能的過快擴張還與投資體制轉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資沖動、資金和資源價格扭曲等體制性矛盾有關。
中國式產能過剩問題比以往更加嚴重。產能利用率是考察產能過剩的重要指標。根據美國經驗,當工業產能利用率超過95%以上時,代表設備使用率接近全部;當產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續下降時,表示設備閑置增多,產能過剩出現;工業產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時,為正常的產能過剩,低于81%時,為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與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相比,我國工業行業的產能過剩從局部行業、產品的過剩轉變為全局性過剩。在我國24個重要工業行業中有19個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水泥等重工業行業產能過剩都是比較嚴重的。2012年,中國產能利用率為57.8%,這要遠遠低于1978年以來中國的產能利用率達到72%~74%的平均水平。
美國針對不同類型產能過剩的不同策略
二戰后“馬歇爾計劃”加快美國過剩產能輸出。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1948~1952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給予西歐的經濟援助達131.5億美元,其中贈款占88%,其余為貸款。拋開“馬歇爾計劃”控制西歐的戰略意圖不談,單就計劃本身就實現了“雙贏”。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不僅促進了西歐聯合,邁出了走向歐洲一體化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鎖定了歐洲的后續采購方向。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后產能。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先后經歷了三次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二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三是21世紀初期。在前兩次產能過剩中,1986~1987年和1991~1992年,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汽車、鋼鐵等傳統制造業。為解決工業產能過剩的危機,美國采取了大力發展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業升級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重心向第三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工業經濟也開始向信息經濟轉型。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工業部門的生產波動對整個經濟穩定性的沖擊減小,而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投資增長點和工業生產增長點。
在美國21世紀初的產能過剩中,2000~2002年,工業產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這一次過剩的產能不是出現在鋼鐵和汽車,而是集中于電子制造業和信息通信產業。這輪高新技術產業“產能過剩”,最終通過相關企業破產和并購重組等方式得以緩解。
日本大規模海外投資實現產能轉移和產業升級
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通過有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響,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東亞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進行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形成了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
從不同時期日本制造業對外投資的重點產業領域看,對外投資額排在前三位的產業,在1969~1973年間是紡織、化學和鐵及非鐵金屬,分別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7%、6.1%和4.8%;1978~1984年間是鐵及非鐵金屬、化學和電氣機械,分別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6%、5.0%和4.8%;1986~1989年間是電氣機械、運輸機械和化學,分別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4%、3.3%和2.7%。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上述制造業行業在相應時期大多已進入產業發展的成熟階段,在日本國內市場上開始面臨過度競爭、生產過剩等問題,而通過向海外進行產業轉移,無疑有助于過剩產能的消化并推動這些產業的優化升級。
中國過剩產能輸出的長期戰略
如果從上述視野來審視當前產能過剩問題,就能夠將我們目前認定的產能過剩行業進一步細分,并能更客觀、科學地尋求解決產能過剩的新途徑和可能性。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勢在必行。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過程中,將按照國際分工價值鏈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中國要實現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的目標,既要加快“走出去”步伐。
首先,對于紡織、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可以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
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也就是三年后,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占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
再次,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從時間周期看,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因此,積極主動的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積極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