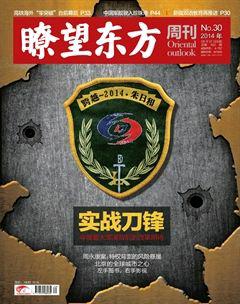用段子編織故事
劉耿
《后會無期》注定是部在評價上兩極分化的片子。不喜歡的人會覺得沒主線、沒劇情,甚至連基本的伏筆都不講究,出現過的人物即用即扔,沒有后戲;喜歡的人會感覺看了四篇韓寒寫的小短篇,意猶未盡。
從一個專業“碼字員”的角度,能推測出《后會無期》的創作過程是以句湊文,先于胸中攢了許多段子,再打造了一個敘事框架來裝這些段子。公路片無疑是最方便的現成結構,那輛無牌照的Polo是裝載這些碎片化思考的盛器,自東徂西,永不回頭,后會無期。時間線、地理線都是單箭頭地向前竄,遇到前后無關聯的故事也很正常,一條條的段子就像鋪設了車軌的枕木,通向不思憶、不解釋。
當然,以句湊文只是一種推測,可信度卻較方舟子對韓寒代筆的揣測為高。一名工匠捧著另一名工匠的茶壺琢磨出其工序并非難事。以句湊文是很多人的寫作方法,有些文章就是從最精彩的一句生發出來的,作者偶得的佳句成為筑文的拱心石,全篇圍繞它來打造。
這不是說以句湊文不好,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在采用這種寫作法。是微博改變了我們。
當我們談論140字的微博時,最耳熟能詳的詞是“碎片化”。但吸引我們關注的往往是碎片化閱讀,認為微博正在使人喪失讀長文的耐心和能力。人性在選擇上有兩種傾向——舍難從易和舍貴從廉,微博恰好順應了這兩條。
現在,很多人的寫作不再習慣整體構思之后動筆,而是會把一些偶得佳句無關聯地擺上紙面,然后連綴成篇。這些佳句往往一百多字,按照大腦的思考與停頓節奏,每寫一百多字,正好敲一下回車鍵——這很讓人懷疑微博的字數設計符合人體生理學指標。
新媒體悄悄地改變我們的寫作或創作方式已不止一天了,“微博化寫作”之前應是“百度型作家”。
“1942年,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1984年,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里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件,他發誓要做中國的IBM;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辟自己的工廠……”
這是“百度型作家”最喜歡的開場白,之前,只有陳寅恪、錢鍾書這樣飽讀群書的大師才能鋪陳得這么瀟灑。
其實,微博化創作沒什么不好,只是浪費了電影這個聲光電的熱媒體形式。最前沿的新媒體倒是與最傳統的紙媒結合得好,段子聯播發個書面通稿也就夠了。即便以孔夫子之才,他的微博體巨著《論語》——也算是一部公路片——能切換的鏡頭也不過是在推銷觀點的游說之路上,雙輪木轂轆車碾過隴上青苗,揚起一路風塵。
這不是一篇針對《后會無期》的批評,而是針對批評的一種解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