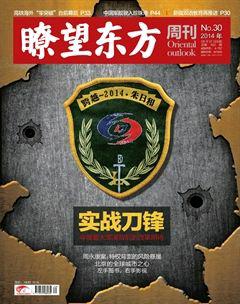讓每個人都能在家門口聽相聲
于曉偉


2014年七月,驕陽如火。站在沒有樹的空地上,格外的熱。
北京市朝陽9劇場外門前,相聲“連鎖店”寬和茶園的掌門人李寬正對著電話嚷嚷,腦門上布滿細密的汗珠。因為已經溝通好的演出場地出現問題,他對電話那頭表達著強烈不滿。
李寬與走在北京街頭的那些年輕人沒有什么不同,一口京腔。掛斷電話后,李寬抱怨“這種事經常有”。管理團隊尚未成型,即使是演出場地的一些細節問題,包括位置、座椅等,都要靠他自己協調。
“寬和”兩字的來歷,除去與他名字有關,在李寬最初的想象中,這里應該是一個24小時營業的茶樓,有演出的時候觀眾買票免費喝茶,或者買茶免費聽相聲;沒有演出的時候,可以看書、聊天。在這個休閑的地方,可以找到安靜與平和。
這個夢想暫時還沒有實現。現在李寬希望寬和茶園能夠盡早獨立運轉,由成熟的團隊進行管理,“作為一個演出和聽相聲的平臺,希望它能融入社會,或者交給街道去經營和管理。”
曾經反感說相聲
28歲的李寬出生于相聲世家。父親李金祥是相聲名家唐杰忠的弟子,每逢演出,李金祥總把李寬帶在身邊。
小時候的李寬對說相聲非常反感,“覺得說相聲的都是江湖人”。看到父親到處跑,接觸各種各樣人,還得說很多話,非常累;每次都要提前兩小時到場,但每場演出的時間卻只有十幾、二十分鐘。
“特別麻煩,也掙不到多少錢。”李寬決心以后不干這個。李寬17歲時,父親李金祥病重入院,收到了病危通知書后,他把未成年的兒子托付給多年的好友李金斗。
看著病床上的父親,還沒成年的李寬忽然覺得,父親說了一輩子的相聲事業應該有人去繼承。
不久,李寬搬到李金斗家里,一住就是三年。李金斗不僅教弟子們說相聲,還給他們講相聲的歷史、老一輩相聲藝術家的故事。慢慢地,李寬開始覺得,把相聲傳承下去是個有價值的事情。
在李金斗創辦的周末相聲俱樂部里,李寬不僅參加一些演出,還參與一些管理工作。
2014年春節前后,68歲的李金斗從周末相聲俱樂部退休,李寬也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一個月后,他決定自己單挑一個“攤兒”,創辦北京第一家相聲連鎖店——“寬和茶園”。
這樣的決定,一方面考慮到相聲的確有它的市場;另一方面,李寬也想確認自己一個月的思索是否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相聲現在有很多種方式,比如主流和非主流、小劇場相聲、院團相聲、電視相聲等,雖然表演手段和風格略微有區別,但都是相聲,都要接地氣,要有深厚的功力和符合展現平臺的技巧。”
連鎖店的經營模式,首先是考慮到為年輕的相聲人提供更多的演出平臺。
“一個作品如果有一兩個小亮點,偶爾演出還可以,但是在寬和茶園這么多劇場,每個星期有十場八場演出的時候,就會覺得經不起推敲。”李寬說這迫使演員們不得不在內涵和功力上下功夫。
對觀眾而言,相聲連鎖店的方式,可以把時間成本從觀眾身上轉嫁到演員那里,“將來希望把劇場開到每一個社區、街道,沿北京二環到六環織一張網,讓每個人都能在家門口看到自己喜歡的相聲。”
十塊錢聽一場相聲
2014年3月底,寬和茶園在北京的第一家分號——永外曲藝會,在永定門管村社區活動中心開張。社區給了他們免費的一個場地,大概可以容納150名觀眾,所以這個分號從開始就沒有什么經濟壓力。
為了回報社區的支持,經過認真討論后,演員們都同意不從那邊掙錢,而且要提供盡量高質量的演出。很快,寬和茶園就向當地群眾宣布,十塊錢聽一場相聲,永遠不漲。
“北京人都有曲藝情懷,”在永外曲藝會上,李寬發現很多六十多歲甚至八十多歲的老人也來看演出,“也有的是夫妻倆一塊來,看他們坐在一起開懷大笑,很溫馨。”
永外曲藝會開張之后,幾乎場場爆滿。
看到第一家分號的成功,李寬開始擴大經營,在北京陸續開出五家分號。現在,河北、遼寧、山西、山東等省也正在陸續開辦分號。李寬說自己管不過來,只能輔助管理,具體經營還得靠分號自己。
不同地方的場地也完全不同。比如永外曲藝會場地較小,容納一百五十人左右;天方劇場可以容納三百人。滄州分店更大,位置開在滄州大劇院,可容納一千四百名觀眾。
李寬覺得把連鎖的經營模式和傳統的相聲藝術結合起來,對相聲、對觀眾都是一種機會,“連鎖真正的意義是把觀眾與劇場、觀眾與演員之間的障礙都解決了,就是個方便。”
以密云、懷柔或石景山的觀眾為例,李寬說,如果他們開車去國家大劇院看一場相聲演出,不堵車也要一個多小時,而在“連鎖店”的模式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師傅李金斗至今也沒弄明白,相聲“連鎖店”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他看來,大概就是一味地鋪攤子,開得多就是連鎖,所以一直擔心李寬的資金會出問題。“師傅主要是擔心客源,哪有那么多人來聽?”李寬說,低價和近距離的社區化模式恰好解決了李金斗擔心的問題。
與永外曲藝會的半公益性質不同、寬和茶園在北京的其他分號采取了低價位商業經營模式。票價多在30至50元,依據位置前后、桌椅配置等略有不同。
“像京劇、相聲這樣的傳統曲藝的小劇場的演出,非常艱難。”李寬的朋友,寬和茶園的策劃參與者陳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一方面經營者得不到社會資金的支持,偶然找到了,也很容易斷裂;另一方面,傳統曲藝并非主流文化,“江湖味較重”,所以寬和茶園的模式在陳憶眼里比傳統班社更科學。
免費贈票被謝絕
“寬和茶園演出的作品,重復的概率非常小。”李寬說,除相聲外,還有三弦、快書、大鼓、快板、雙簧等,寬和茶園的常駐演員接近百人,“即使觀眾每周都來看演出,基本上一年內看不到重樣的節目。”
開張短短三個月,李寬得到了諸多支持,前輩、師兄弟、同行好友紛紛捧場,很多人分文不取;一些觀眾看完后,也會幫忙轉發微博、微信。李寬曾經提出送一些免費票回報給轉發微信的觀眾,但被一些觀眾謝絕了,他們堅持掏錢買票,“這讓我覺得這個事情深得人心。”
相聲行業里有句話叫“各使家衣”,意思是各有自己的傳承,各有自己的看家本領。但在寬和茶園,演員們可以互相學習和切磋,“如果非常喜歡別人的節目,對方還會一點點耐心地教,氛圍非常好。”李寬說,任何一個行業,如果能做到這點,都會很繁榮。
李寬說,雖然逐漸贏得了觀眾的口碑,但因為場地費用以及演員的演出成本等,現在寬和茶園每個月平均虧損五萬元左右。
好在票房情況越來越好。有的分號開張第一周賣不出十張票,但第二周就能賣出二十張左右,然后到四十多張……“預計到年底,應該能實現盈利。當然,即使盈利也會很少。” 李寬覺得,票房之外的一些附加價值,更值得看重。
最近演員們出鏡的頻率和商演活動明顯在增加,“以后我們也計劃向話劇、影視劇轉型,希望能做獨立的影視作品。”
年輕人的機會
經常在寬和茶園演出的近百名演員中,以八零后的年輕人居多。
寬和茶園的定位是演出平臺,李寬說,所有演員都可以自由流動,薪酬按月結算,“如果簽約,演員固定下來,就違背了創辦這個平臺的初衷。”
目前寬和茶園的演員酬勞為每場兩三百元,每人一個月大概有十場演出。“現在聚攏的一批年輕演員的素質非常好,如果觀眾不是抱著一個看名人的心態來看演出,應該會很滿意。”
有時候,李金斗、石富寬、孟凡貴等相聲名家也可能作為嘉賓演員出現。
觀眾的需求永遠是第一位的。李寬的師兄萬宇告訴本刊記者,在CBD商圈的朝陽分店,因為年輕觀眾多,他們就提供時尚、超前的話題節目;而永外曲藝會老年觀眾多,則多選擇有京味兒、文學性和知識性較強的段子;位于西直門的天方劇場分店,觀眾群體多樣,甚至可能是住店的外地人,“這里的包袱要易懂,笑料密集度更高,也就是通常說的皮薄餡大。”
雖然創辦了這個連鎖相聲店模式,但李寬希望寬和茶園能盡快脫離自己獨立運轉,因為他的目標,是做一個“不太有名的相聲演員”,每周能在小劇場里演出一兩場,然后再去外地演出一兩場,掙點錢養家就可以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