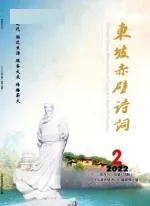淺談歷代軍旅詩詞的傳承與發(fā)展
□涂運(yùn)橋
軍旅詩詞是中華詩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抒發(fā)了每個時代的最強(qiáng)音。它往往以戰(zhàn)爭、邊塞、征戍、軍旅生活、軍人情感、軍旅事物、軍旅人物等作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的一種風(fēng)格獨具的詩歌類別。軍旅詩詞歷史悠久,源遠(yuǎn)流長。
中華詩詞的兩大源頭《詩經(jīng)》和《楚辭》中都有一定篇目是表現(xiàn)軍旅內(nèi)容的。當(dāng)代軍旅詩詞如何創(chuàng)新,如何繁榮,如何為強(qiáng)軍夢服務(wù),向歷代優(yōu)秀的軍旅詩詞學(xué)習(xí)和借鑒是必要途徑,傳承是根基,發(fā)展是枝干,創(chuàng)新是花葉。
當(dāng)代長安畫派大師石魯曾道:“一手伸向傳統(tǒng),一手伸向生活”。這正是當(dāng)代軍旅詩詞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方法。“一手伸向傳統(tǒng)”,是要求我們?nèi)グl(fā)掘,去鑒別,去學(xué)習(xí),去提高,達(dá)到對于前人成就的真正繼承,以便走向新的更高的目標(biāo)。好比攀登,前人的成就像一部梯子,后來者總要努力站到前人的肩膀上才會進(jìn)步。生活,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任何人都不能離開他的時代而存在。生活中不是缺少激情,關(guān)鍵是缺少善于發(fā)現(xiàn)真、善、美的一顆心。傳統(tǒng)也是生活,但那是過去的生活。歷史是一面鏡子,所以必須向傳統(tǒng)學(xué)習(xí),不能停留在過去,所以必須抒寫當(dāng)代。“不薄今人愛古人。”央視《三國演義》片尾曲《歷史的天空》所唱:“黯淡了刀光劍影,遠(yuǎn)去了鼓角錚鳴,眼前飛揚(yáng)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古人雖然遠(yuǎn)去,但歷史的天空永遠(yuǎn)回響著英雄的吶喊。
《詩經(jīng)》中的軍旅詩并不注重戰(zhàn)爭的渲染,而是以戰(zhàn)爭場面作為背景,表現(xiàn)主人公在戰(zhàn)爭中的生存狀態(tài)和情感世界。如《王風(fēng)·揚(yáng)之水》主要反映軍人屯戍不得歸的幽怨情懷,此詩和《鄴風(fēng)·擊鼓》被后世稱為征戍詩之祖。尤其《秦風(fēng)·無衣》,朱熹《詩集傳》道:“秦俗強(qiáng)悍,樂于戰(zhàn)斗……足以相死如此。”后來秦一統(tǒng)六國,從這首詩可窺端倪。其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 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
這首詩一共三段,以復(fù)沓的形式,表現(xiàn)了秦軍戰(zhàn)士出征前的高昂士氣。他們互相召喚、互相鼓勵,舍生忘死,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從軍曲!是秦國人民抗擊西戎入侵的軍中戰(zhàn)歌。
《國殤》:“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云,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摯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yán)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yuǎn)。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qiáng)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屈原的《國殤》是中華軍旅詩詞中第一首有明確作者的詩:這首詩表達(dá)了慷慨悲壯之氣和屈原“雖九死猶無悔”的愛國情懷與憂患意識,是軍旅詩詞史上的杰作,對歷代詩人影響深遠(yuǎn)。學(xué)者李桂生認(rèn)為:“《國殤》反映了戰(zhàn)國末期的戰(zhàn)爭情況,是楚辭中唯一描述戰(zhàn)爭的作品,是一篇重要的兵學(xué)文獻(xiàn)。”當(dāng)代軍旅詩詞的發(fā)展和研究,繞不開這首開個人創(chuàng)作軍旅詩先河的《國殤》。“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qiáng)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讓人感受到了將士生死與之的愛國情懷,激起的是對生命價值和國家命運(yùn)的思考,楚人愛國尚武的民族精神和信鬼好巫的風(fēng)尚,以及戰(zhàn)國末期諸侯紛爭的現(xiàn)實在《國殤》中都得到了真實體現(xiàn)。《國殤》發(fā)出了慷慨壯士之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在詩中詩人進(jìn)一步將自己對生命價值的體驗通過詩表現(xiàn)出來,死亡不僅是維護(hù)人格操守的手段,也是對有限生命的超越,閃爍著永恒的道德價值和人文光輝。詩人以楚軍陣亡將士的魂魄表達(dá)了至死不屈的勇者無懼精神,贊揚(yáng)了楚國將士雖死猶生的人生價值觀。
曹植《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xiāng)邑,揚(yáng)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fā)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shù)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qū)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詩通過描寫歌頌了邊疆地區(qū)一位武藝高強(qiáng)又富有愛國精神的青年英雄,借以抒發(fā)作者的報國之志。本詩中的英雄形象,既是詩人的自我寫照,又凝聚和閃耀著建安風(fēng)骨的光芒。詩歌以曲折動人的情節(jié),塑造了一個性格鮮明、生動感人的青年愛國英雄形象。
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征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yán)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qiáng)。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fēng)沖塞起,沙礫自飄揚(yáng)。馬毛縮如猬,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jié),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代出自薊北門行》是樂府舊題,屬雜曲歌辭。此詩通過邊庭緊急戰(zhàn)事和邊境惡劣環(huán)境的渲染,突出表現(xiàn)了壯士從軍衛(wèi)國、英勇赴難的壯志和激情。在表現(xiàn)壯士赴敵投軀的忠良?xì)夤?jié)時,穿插胡地風(fēng)物奇觀的描寫,是南北朝時期罕見的接觸邊塞生活的名篇。杜甫《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足見鮑參軍對李杜的影響。“俊逸鮑參軍”,就是贊美李白的詩有鮑照的俊逸風(fēng)格。鮑照墓在湖北黃梅縣城,今年清明前夕,為了表達(dá)我們后輩對詩人的敬仰,我組織了幾位詩友驅(qū)車前往祭奠,一發(fā)“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fù)登臨。”之慨。
李清照《夏日絕句》:“生當(dāng)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詩的背景是國亡家破的慘痛血淚。詩雖短,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jīng)時代的苦酒釀造,妙手偶得之。詩人呼喚英雄,然而那個時代缺少力挽狂瀾的人物,只落得“凄凄慘慘戚戚”的境地。詩表現(xiàn)了人格的挺立,再現(xiàn)了屈子精魂,表達(dá)了一種所向無懼的大無畏犧牲精神。這種凜然風(fēng)骨,浩然正氣,充斥天地之間,直令鬼神變色。詩人鞭撻了南宋投降派的無恥行徑,借古諷今,正氣凜凜。全詩僅二十個字,連用了三個典故,但無堆砌之弊,因為這都是詩人的心聲。如此慷慨雄健、擲地有聲的詩篇,不愧為軍旅詩中的戰(zhàn)斗進(jìn)行曲。
文天祥《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jīng),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fēng)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首詩表達(dá)了作者為了挽救國家,不惜獻(xiàn)身的壯烈情懷。“丹心”是指赤紅熾熱的心,一般以“碧血丹心”來形容為國盡忠的人。“汗青”是指歷史典籍。古時在未有紙的發(fā)明之前,要記錄軍國大事,便只能刻寫在竹簡之上。但必須先用火把竹簡中的水分蒸發(fā)出來,這樣才方便刻寫,并可防蟲蛀。后人據(jù)此引申,把記載歷史的典籍統(tǒng)稱為“汗青”。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兩句是說自古以來,人終不免一死,但死得要有意義,倘若能為國盡忠,死后仍可光照千秋,青史留名。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所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作為新中國的軍警,一顆“丹心”當(dāng)然時刻準(zhǔn)備著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惜揮灑和奉獻(xiàn)自己的鮮血與生命。夏完淳《別云間》:“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xiāng)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別云間》是作者被清廷逮捕后,在解往南京前臨別松江時所作。“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詩人在《獄中上母書》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矣”。“已知泉路近”的詩人坦然作出“毅魄歸來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堅決復(fù)明的決心,生前未能完成大業(yè),死后也要親自看到后繼者率部起義,恢復(fù)大明江山。詩作以擲地有聲的錚錚誓言作結(jié),鮮明地昭示出詩人堅貞不屈的戰(zhàn)斗精神、盡忠報國的赤子情懷,給后繼者以深情的勉勵,給讀者樹立起一座國家與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豐碑。全詩思路流暢清晰,感情跌宕豪壯。起筆敘艱苦卓絕的飄零生涯,承筆發(fā)故土淪喪、山河破碎之悲憤慨嘆,轉(zhuǎn)筆抒眷念故土、懷戀親人之深情,結(jié)筆盟誓志恢復(fù)之決心。詩作格調(diào)慷慨豪壯,令人讀來蕩氣回腸。
陳毅《梅嶺三章》:“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圍。余傷病伏叢莽間二十余日,慮不得脫,得詩三首留衣底。旋圍解。(一)斷頭今日意如何? 創(chuàng)業(yè)艱難百戰(zhàn)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二)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后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dāng)紙錢。(三)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fēng)應(yīng)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梅嶺三章》是1936年冬天中國共產(chǎn)黨人陳毅在梅嶺被國民黨四十六師圍困時寫下的三首詩。陳毅雖然處在危難之際,但獻(xiàn)身革命的決心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心卻矢志不移。
于右任《國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xiāng);故鄉(xiāng)不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海茫茫,山之上,有國殤。”
這首詩發(fā)表于1964年。晚年在臺灣的于右任非常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山要高者,樹要大者,可以時時望大陸。我之故鄉(xiāng)是中國大陸”。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寫下了感情真摯沉郁的詩作《望大陸》(又名《國殤》)。這是他眷戀大陸家鄉(xiāng)所寫的哀歌,其中懷鄉(xiāng)思國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觸動炎黃子孫靈魂深處隱痛的絕唱。閱讀此詩,給人一種悲愴深沉、愛國情真的感覺。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先生久居臺灣,不能回歸桑梓,但是海峽波濤卻隔不斷、阻不斷他望大陸、念故鄉(xiāng)、思親人的深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正是這真摯強(qiáng)烈的情感和刻骨銘心的思念,給讀者以強(qiáng)烈的震撼,引起讀者感情與思想上的共鳴。詩的最后一節(jié)開頭兩句借用了北朝民歌《敕樂歌》里的兩句話,采用疊字,狀物形象而生動!最后兩句“山之上,有國殤!”語意雙關(guān)而寓意豐富。《國殤》出自屈原楚辭《九歌》。《九歌》是屈原流放途中模仿楚國南方的祭歌而創(chuàng)作的一組詩篇,《國殤》是其中一首,是追悼將士的挽歌,所謂“殤”,《小爾雅》說:“無主之鬼之為殤。”詩人巧借“國殤”,抒寫自己死后不能葬在大陸,不能魂歸故里的遺憾。
綜上所述,當(dāng)屈原《國殤》成了中華民族憂患意識愛國精神的象征以后,歷代詩人都懷著無比崇敬與熱愛之情將其傳承下來,不僅在詩的創(chuàng)作手法上借鑒了《國殤》,更重要的是繼承、發(fā)揚(yáng)了《國殤》所弘揚(yáng)的憂患意識與愛國主義精神。從他們作品中,充分看出他們都為屈原的《國殤》而感動,足見《國殤》影響之深。“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用這兩句詩來說明傳統(tǒng)和生活是寫作的源頭活水。湖水之所以總是清澈見底,是因為不斷地有新的水灌注。我們從這首詩中可得到啟發(fā),只有思想永遠(yuǎn)活躍,兼容并包,海納百川,繼承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方能才思不斷,新水長流。成語“源頭活水”來自此詩。縱觀一部中華軍旅詩詞史,就是一部不斷繼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詩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