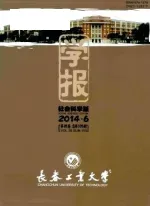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域下《圣經》中的生態書寫研究——以《路得記》文本為例
姜貴梅 賈丹丹
(1.天津外國語大學 基礎課教學部,天津300204;2.天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300387)
20世紀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促使學者們探究生態思想文化根源。國外生態思想家在回顧和總結生態思潮時達成基本共識,認為“生態思潮的主要使命是重審人類文化,進行文化批評,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1](P2)在生態批評狂潮中,《圣經》因為其中所宣揚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備受指摘,被認為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同時,西方思想家也開始反思基督教傳統理論與生態危機的關系,在生態批評的語境下對《圣經》進行新的闡釋,關注《圣經》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現代人類生態美學站在歷史的高度,重新審視了人的身心關系、人與生態環境關系,提出了內在統一的和諧思想”,[2]雖然成書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是《圣經》中一些文本所書寫的生態思想契合了現代生態美學的一些觀點,引起廣泛關注。由于《圣經》在人類歷史文明變遷以及現世生活中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和作用,發掘其中的生態思想能更好地提高人們的生態審美和生態保護意識。鑒于此,本文在生態批評的視域下,以《圣經》中的經典經卷《路得記》為例,討論文本的生態書寫及其所蘊含的生態思想。
與《圣經》中的其他經卷不同,《路得記》是以一個普通異族女子為中心的故事。經卷講述了古希伯來人以利米勒因為家鄉饑荒攜帶妻子和兩個兒子來到摩押地寄居,十年后,家中三個男子竟意外地全部死去。婆婆拿俄米希望遣散兩個兒媳,獨身返回故居伯利恒,但小兒媳路得堅決追隨婆婆回到丈夫的故鄉。在撿拾麥穗時,路得遇見了地主波阿斯,在婆婆的支持下,路得向波阿斯表示了自己以身相許的心愿,波阿斯也因為路得的賢德而對其充滿尊重和喜愛,最終兩個人根據當時寡婦內嫁制的風俗,結為夫妻,并生下了一個兒子。雖然《路得記》表面只是現世中一個很普通的異族女子的婚姻故事,但是行為充滿了詩意和美感,也有深刻的內涵。在生態視野下,本文立足于《路得記》文本,通過對豐收意象、兩性關系和場景描寫的研究,探索文本中所蘊含的生態中心理念,如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關系,男性和女性和諧的關系,以及人在世界中詩意的棲居,從而通過解讀文本的生態書寫來展現古希伯來人積極樸素的生態思想,以啟發世人更好地欣賞《圣經》中的生態美,汲取其中積極的生態思想,更好地愛護我們的家園。
一、對人與大地的書寫
《創世紀》中,上帝創造出天與地,自然萬物,但是在“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人類把自然當作是為自己服務的工具和奴仆,對自然肆意妄為,而人類對自然的侵略和掠奪的表現之一就是對大地母親的忽視和過度汲取。人類改造、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但是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大地母親失去了以往的生機和繁榮,慢慢淪為艾略特筆下的“荒原”——枯萎、貧瘠,絕望和死亡。隨著生態危機日益加重,思想家們開始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特別是人與大地母親之間的關系。美國哲學家利奧波德提出了“大地倫理”的思想,提出了人和土地之間的倫理關系,人類與大地不是一種占有和利用的關系,而是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的關系。在“大地共同體”理論下,人類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大地(自然界)共同體中的一個。人類只有尊重共同體中的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熱愛并保護生養我們的大地,人類才能依托于自然,立足于世界。人類休養生息于大地母親之上,與大地母親共生共榮的關系在《路得記》中彰顯無疑。
在《路得記》的故事背景中,土地的貧瘠,伯利恒的饑荒使得拿俄米一家背井離鄉,家中的三個男性也最終難逃死亡之劫。當拿俄米得知伯利恒土肥地豐——“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3](P254)——就決定返回故里,小兒媳路得堅決地跟隨婆婆回到家鄉,故事由此開始。《路得記》前后的對比進一步烘托了人與土地生死相依,休戚與共的關系。
當路得跟隨婆婆回到家鄉伯利恒的時候正式“動手割大麥”的時候,大地母親呈現出一片豐收的景象,“收獲”的意象也貫穿故事始終。收獲的季節,人們心中充滿了感恩和喜悅。在豐收的田野上,路得邂逅了波阿斯,并與之產生樸素的感情,最終收獲了一份婚姻和一個兒子。在《路得記》問世之后的兩千多年,教徒們每年都會在猶太人的三大節日之一的“五旬節”朗讀它。“五旬節”又稱“收獲節”,也就是收割麥子的季節,來感謝上帝賜與的收獲,同時也紀念路得這位異族女子的美德和仁愛。而“收獲”恰好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象征和表現,是大地對人類的一種給予和回饋,而這也是人類自足之基和生存之本。古希伯來人的風俗體現了生態美學中所講到的“共生性”,“意指人與自然生態相互促進,共生共榮,共同健康,共同旺盛”。[4]《路得記》中所描繪的那一片豐收的景象和收獲的意象已經成為一種文學意象,帶給人以希望和美好。豐收和收獲的意象正是人依托于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個象征和結果。
《路得記》通過對豐收和收獲的書寫,展現了古希伯來人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期盼和贊美,書寫了一種樸素的生態觀。
二、打破二元對立的兩性關系
在《創世紀》中,上帝從亞當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創造了夏娃,由此開始了女性從屬于男性的被動地位。在父權社會中,亞當和夏娃的關系成為男女關系的范式。無論從被造的順序還是目的,女性劣于男性。“女性劣于男性、自然劣于人的二元對立思想是基督教思想中,甚至是整個西方文化中輕視女性、忽視自然世界的根源”[5](P13)。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男性與女性的關系,自然與文明的關系被割裂開來。盡管如此,在《路得記》中,我們卻解讀到了一種不同的兩性關系。在這里,沒有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對立,有的卻是理解和關懷;在這里沒有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有的卻是尊敬和愛護。路得和波阿斯之間的愛情故事雖然樸實、平淡,卻十分感人,詮釋了兩性之間的和諧與美好。
當路得來到田間撿拾麥穗時遇到了地主波阿斯,出于對路得遭遇的同情和對路得品行的贊賞,波阿斯按照希伯來的傳統讓路得在他的田間撿拾麥穗并吩咐仆人“從捆中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她拾取……”[3](P255),并為路得提供水和食物。波阿斯的善良和體貼也贏得了路得的愛戴和尊敬,一段美好的感情發展起來。在善良的婆婆的幫助下,路得來到了打麥場,按照希伯來求婚的習俗,躺臥在波阿斯的腳下,表明自己以身相許的決心。波阿斯感動于路得的坦誠,說:“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行”[3](P256),但是為了保持路得“賢德”的名聲,波阿斯必須按照古希伯來的風俗,請了本城的長老,與路得的另外一位至親的親屬進行協商。按照“寡婦內嫁制”的風俗,那位至親如果買下路得家的地,就要迎娶路得,所生下的后代卻要歸于路得先夫的名下。但是那位至親擔心這樣于自己的產業有礙,就脫鞋為證,放棄了對路得家土地的贖買,同樣也放棄娶路得為妻。這樣,路得名正言順地嫁給了波阿斯。在路得與波阿斯的故事中,我們看到的男女之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愛慕,最終克服困難,創造幸福生活的過程。
雖然,根據古希伯來的傳統觀點,男性的地位要高于女性,但是波阿斯卻沒有對路得有絲毫的輕視和不敬,而是盡其所能幫助她、愛護她,這顛覆了女性和男性之間二元對立的傳統,體現了一種和諧的兩性關系。由于“在基督教傳統中,男人是理性、靈魂、精神的象征和承載物,他們和上帝更為接近;而女人則是肉體和物質世界的象征,是墮落和欲望的載體,她們和自然更為接近。這種觀念造成了文化與自然、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巨大鴻溝”[6](P179)。由此,路得和波阿斯和諧的關系也喻示了他們分別象征的物質與精神、自然和文明之間的和諧和統一,由此打破了傳統觀念中女人與男人、自然與文明之間的對立關系。
三、“場所”中所喻含的“家園意識”
《路得記》篇章簡潔,全文由幾個主要“場景”構成,這些場景被置于古希伯來人日常生活的各種“場所”背景下。通過對這些“場所”的描寫,體現了古希伯來人濃厚的家園意識。
“家園意識”是海德格爾最早提出的美學概念之一,是探討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內涵。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家園意識’不僅包含著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而且蘊含著更為深刻的、本真的人之詩意地棲居的存在真意”。[7](P325)而一向被贊揚為“牧歌體”的《路得記》因為所描寫的詩意場景、令人陶醉的田園氣息和和諧的人際關系而散發著濃郁的“家園意識”,而這種宏大的人之存在的本源性意識通過一個個具體“場所”的描寫體現出來。
在《路得記》中,作者通過幾個“場所”的描寫書寫了一個充滿了詩意的空間。在海德格爾看來,“場所意識”就是與人具體的生存環境及其感受息息相關。而“空間化為人的安家和棲居帶來自由和敞開之境”。[8](P482)在麥田中,路得在撿拾麥穗的一幕已經成為經典的詩性敘述,一段美好的愛情也在這豐收的大地上收獲,自然的豐碩和人棲居于自然的美好給人帶來希望和寄托;在打麥場,路得依偎為波阿斯的腳下,兩個人之間相互的尊重、理解和愛慕,帶給人愉悅而甜蜜的感動;在城門口,波阿斯和路得至親之間的脫鞋為證,有情有義,有理有據,讓路得名正言順地嫁進自己的家門;而在街頭巷尾,拿俄米和街坊鄰居之間的互相關愛和肯定,也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友愛。
阿諾德·伯林特對“場所”做了更加具體的闡釋,“這是我們熟悉的地方……它們很容易被識別,能帶給人愉悅的體驗,人們對它的記憶中充滿了情感。如果我們的臨近地區獲得同一性并讓我們感到具有個性的溫馨,它就成為了我們歸屬其中的場所,并讓我們感到自在和愜意”。[9](P135)在《路得記》中,作者所描寫的這些“場所”——麥田、打麥場、城門口和街頭巷尾恰恰正是古希伯來人日常生活中最為熟悉的地方。“鄉土,是人類最初情感與最深刻理性集合成的一種文化形態,人類賴以詩意地棲居的精神家園”,[10]然而通過對這些具有鄉土氣息的場景的描寫,表現了古希伯來人在自己所存在空間棲居的自在、和諧、愜意而溫馨,而且在這平凡而詩意的棲息中孕育著希望和美好。當路得為拿俄米生下兒子俄備得時,這位老婦人也最終由邊緣位置回歸到自己民族的倫理體系之中,而路得,一個異族女子,最終成為以色列民族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衛王的曾祖母,由此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征,突破了猶太民族狹隘的民族意識,促進了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聯系與交往。
《路得記》通過對場景的書寫,不僅展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還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關愛、理解與尊重,展現了一個和諧美滿的理想家園,實現了人本真的存在,詩意的棲居。
四、結語
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里提出了生態整體主義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有助于維持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事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11](P224-225)“和諧、穩定和美麗”成為我們看待世界的一種原則。本文以《路得記》為例探討了《圣經》中的生態書寫。通過對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書寫,對男女和諧關系的書寫,對人詩意棲居的書寫,讓我們看到了古希伯來人和諧樂居的場景,看到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托與眷顧,看到了人如何“詩意的棲居”于世界之中。132這也是為什么歷經歲月的遷徙,《路得記》所傳達的那種質樸和美好溫暖了人們的心,也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這樣讓我們進一步更好地認識《圣經》以及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生態思想,啟迪當代人更好地愛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
[1]王諾.歐美生態批評[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2]吳佩君.生態美學的身體維度研究[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
[3]中國基督教協會.圣經[M].南京: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2011.
[4]曾繁仁.試論生態審美教育[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5]南宮梅芳,朱紅梅,武田田.生態女性主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6]Rosemary Ruether.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 Healing[M].San Francisco:Harperone,1992.
[7]曾繁仁.生態美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8]〔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9]〔美〕阿諾德·伯林特.環境美學[M].張敏,周雨,譯.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10]黎維麗.集體記憶與家園意識[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
[11]Leopold Aldo.A Sand County Almanac[M].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