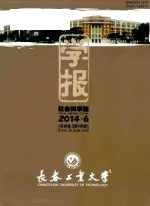論“馬歇爾計劃”的非冷戰因素
成 林
(湖北財稅職業學院 圖書科研處,湖北 武漢430064)
1947年馬歇爾提出“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該計劃提供總價值為131.5億美元的援助,以幫助西歐經濟走出戰爭陰霾。“馬歇爾計劃”的出臺有著不可否認的冷戰政治因素,然而筆者認為,冷戰只是主要誘因之一,即使沒有戰后國際政治兩大敵對陣營的分野,美國從其稱霸全球的戰略角度考慮,為維護本土的經濟安全和增長,最終也將對歐洲進行援助。
一、稱霸全球戰略是美國援助西歐的根本出發點
(一)特殊使命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思想根源
“美國外交事務的出發點是這樣一種信仰,即美國在外部世界關系中享有一種任何其他國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1](P18)這種特殊使命感和對國際事務的責任感,根植于早期美國移民中的清教傳統,形成了特殊的美國精神并延續下來。美國學者斯特林·約翰遜在談到美國使命觀時指出,“從歷史上講,美國人擁有這種信念,即美國過去是,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他們認為,美國信念的理想過去是,現在還是不僅對美國是正確的,而且對其他國家也是正確的。”這種傾向可以說始終存在于美國對外政策之中。[1](P48-49)對世界事務的主宰被美國人普遍認為是他們的天然職責。
(二)稱霸世界是歷任美國總統的施政目標
19世紀90年代,美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大國,經濟的極度膨脹,使美國自然走上了海外擴張的道路,之后歷屆美國總統都把稱霸世界作為施政的主要目標。對西班牙戰爭的勝利,使美國品嘗到了作為殖民帝國的好處。西奧多·羅斯福的“大棒政策”確立了美國在加勒比海的霸主地位,實現了將加勒比海變成“美國內湖”的計劃,他喚醒了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的夢想;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交替使用,控制了拉丁美洲;“門戶開放”政策使美國順利進入老牌帝國主義的勢力范圍;“門羅主義”令美國確立了“美洲霸主”地位。
(三)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稱霸全球戰略的助推器
兩次世界大戰使美國集聚了實力,逐步登上霸權舞臺。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作為戰爭物資的主要供應國,從戰前的債務國轉變成戰后擁有100億美元的債權國。美國總統威爾遜宣稱:“金融領導地位將屬于我們,工業地位將屬于我們,貿易優勢將屬于我們,世界上其他國家將期待我們給予領導和指引”。[2](P102)自威爾遜后的總統,都把稱霸全球作為自己的施政綱領和制定外交政策的圭臬。二戰的全面勝利,美國選擇在各個領域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機制。1945年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宣布:“勝利已使美國人民有經常而迫切的必要來領導世界”。[2](P18)到1948年,美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產量的53.7%,黃金儲備的74.5%,經濟實力的劇增為美國稱霸全球的夢想作了有力的支撐。
(四)希、土危機使美國順利完成世界霸權的交接
1947年希臘和土耳其的危機為美國接過英帝國主義的霸權地位創造了良好契機。1947年2月,英國向美國提交了涉及希臘和土耳其的兩份照會,這表明“英國此刻已將領導世界這一任務,連同其全部負擔和光榮,一起交給了美國”。[3](P54)毋庸置疑,希臘和土耳其戰略位置之重要,自然令美國接起了保衛東地中海的重擔。5月22日,杜魯門簽署了“援助希臘、土耳其法令”,將希、土兩國納入美國全球戰略體系,在東地中海建立了美國的前沿陣地。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在和海軍及陸軍部長討論希、土問題時提出:希、土僅是歐洲問題的一部分,整個歐洲援助問題急需考慮,“一個受華盛頓密切監視、統一的援助計劃將能獲得和平與繁榮,即恢復經濟,穩定政治,削弱共產黨,有助于多邊的世界貿易以及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安全。”[4](P207)
二、歐洲是美國稱霸全球戰略的關鍵
(一)歐洲是美國政治體制和宗教文化的重要來源地
從美國的宗教、文化、人種等因素來看,與歐洲唇齒相依。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主流階層仍然是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從人種上看,美國是歐洲和其他洲的大雜燴,但主流階層與歐洲,尤其是西歐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從宗教上看,英國的清教徒、蘇格蘭的長老會教徒、荷蘭的宗教改革者、德國的路德派教徒、法國的胡格諾教徒、歐洲的天主教徒都在英國匯集。19世紀美國著名的政治家丹尼爾·韋伯斯特認為“英國給美國帶去了自由;而西班牙則帶去了權力”。弗雷德里克·金特爾斯的一項研究結論是“美國多數政治傳統是英國經歷的結果”。[1](P18)美國的許多政治文化傳統仍舊保持了其母國英國的風范。加上18世紀歐洲“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滲透,對美國的政體創建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歐洲是美國戰后貿易的重要輸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歐各國至少占美國出口貿易的40%,同時在美國的資本輸出中這些國家占第二位。[5](P29)到1947年,美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1/3,達140億美元,一些關鍵性的工業產品,如汽車、大型機械設備、鋼材、農業機械等都依賴出口,主要銷往西歐。戰后初期,美國對西歐等國片面的“多出少進”的貿易政策,使得西歐各國無力組織強勢出口以換回外匯來支付美國商品,引發了“美元荒”,成為美國發展貿易擴張的一個嚴重障礙。美國出超的大幅度下降將對美國的商務活動和就業產生抑制性作用。為維持美國持續穩定的發展,支持高出口額,就必須對歐洲予以援助,幫助他們恢復購買實力。
(三)歐洲殖民地是美國壟斷資本的延伸地
西歐有著美國夢寐的財富和廣袤的殖民地。二戰期間,華爾街眼前的主要目標就是在西半球上消除所有其他帝國主義對手,獨享太平洋上的支配權,并在遠東大部分地區獲得支配地位。[6](P155)美國稱霸全球的野心使它必然需要謀求控制世界市場和資源作為依托。一戰后,德、意、日被踢出拉丁美洲,其產業在美國金融資本的控制下進行了改組,增加了美國對南美洲的控制;同樣,較弱的“同盟國”法國在二次戰爭中的削弱,對拉丁美洲投資驟減;更不用說英國,為了換取驅逐艦和軍火,被迫放棄了加勒比海及沿加拿大海岸的重要軍事基地,還讓出了它在美國及拉丁美洲的投資。至二戰結束,加拿大成了美國軍隊的訓練場,油田和鐵礦砂資源都自動轉到美國壟斷資本手中;在中東,美國從英國手中收購了阿拉伯的軍事和經濟據點。借助對西歐的經濟援助,就可以利用老牌帝國打下的基礎讓美國的壟斷資本滲透到世界各地。
(四)西歐是美國戰后制衡蘇聯的緩沖地
歐洲有著妨礙美國稱霸全球的巨大障礙—蘇聯,控制整個歐洲是美國稱霸全球的關鍵。隨著二戰后美蘇共同敵人的消失,昔日的朋友變成對手,蘇聯成為橫亙于美國霸權之路上的巨大障礙,此時西歐對于美國而言戰略地位更是顯著。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控制夾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中間地帶”,戰略意義可見一斑。與“馬歇爾計劃”同時運作的“北大西洋軍事同盟”使美國跨越了大西洋這片巨大水域,取得了在歐洲駐兵的權利,更便于美國對歐洲局勢的掌控。
三、援助西歐是美國稱霸全球戰略的利益所在
(一)經濟援助歐洲是美國戰后稱霸世界政治目標的重要部分
蘇聯在二戰后將保持邊界疆域穩定及周邊國家的安全作為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在德國東側也即蘇聯自己一邊的緩沖地帶上大力扶持東歐各國政府,確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法國和意大利的局勢更不容樂觀,政府的支持率正在下降,而在反法西斯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的支持率正在上升。[7](P47)毫無疑問,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局勢是美國戰后制定援助計劃的巨大誘因。再加上戰后西歐經濟局勢惡化,工人階級組織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美國擔心這將給共產主義以可乘之機。此時援助虛弱不堪的歐洲,對穩定戰后的局勢,加強美國對西歐的控制是大有裨益的。
(二)對受援國家附加“奴役性”條款是美國霸權外交的天性
戰后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就是要通過進一步發展經濟和保持充分就業來實現“領導”世界的目標。而戰爭結束導致軍事生產減少使工業產量急劇下降,失業人口增多,西歐此時無力與美國展開正常的貿易。此時如果不展開經濟援助,無異于關閉了美國的金融和貿易大門。但援助不是無償和純道義的,“馬歇爾計劃”規定,接受“美援”的國家必須與美國簽訂雙邊協定,這有利于美國針對不同國家提出不同的附加條款。“美援”以美國提供貨物的方式進行;受援國出售這些貨物所得款項,須經美國同意后才能動用;受援國必須開放本國及殖民地市場;須保障美國公民的權利和向美國提供有關經濟情報等。
(三)“馬歇爾計劃”成功轉嫁了二戰后美國內第一次經濟危機
1947年5月27日提交的一份備忘錄中,美國副國務卿克萊頓寫道“沒有美國的更為迅速的大量援助,經濟社會和政治解決將遍及歐洲……除了世界未來和平與安全產生嚴重影響外,對我國國內經濟的影響也是極為嚴重的,將失去我國剩余產品的銷售市場”。[8](P114-115)可見,對西歐援助的出發點仍然是美國的經濟利益。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美國爆發了戰后第一次國內經濟危機。1949年,美國對西歐的全部出口中,有62.7%是靠“馬歇爾計劃”資金實現的,1950年這一比例更增至73.2%。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成功轉嫁了這次經濟危機。
(四)“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加強了美國資本的歐洲滲透
通過與受援國簽訂雙邊協議,美國獲得在受援國自由投資的權力,大量美資涌入西歐,擴大了資本的海外市場,加強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1951年“馬歇爾計劃”結束,歐洲經濟基本得以恢復,美國私人資本在歐洲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1996年6月11日,《亞洲華爾街日報》刊文指出,這種援助以“隱蔽的形式使美國企業共同繁榮”,“使許多美國企業家富起來,有些歐洲工業卻遭到劫掠”。[9](P237)
(五)“馬歇爾計劃”使美國成為世界貨幣體系的霸主
按照羅斯福總統“世界藍圖”建立起來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以美元為核心構造的國際金融舞臺,為美國撈取鑄幣利差,轉嫁國內通貨膨脹創造了基礎。“馬歇爾計劃”促成歐洲支付同盟的建立,對布雷頓森林體系起到了支撐作用,彌補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需求,避免了國際貨幣體系和貿易體系的崩潰,使得美元成為西歐市場的主要結算貨幣,打開了西歐多邊支付的格局,化解了西歐對美國商品的束縛。美元的結算體制,削弱了歐洲金融,使美元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的“中心貨幣”。
[1]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2]吳于廑,等.世界史現代史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方連慶,等.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Price,H..TheMarshallPlanandItsMeaning[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5.
[5]〔蘇〕A.基爾薩諾夫.美國與西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經濟關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6]〔美〕維克托·佩洛.美國帝國主義[M].北京:世界知識社,1955.
[7]〔英〕托因比.歐洲的重組(上)[M].勞景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8]王在幫.霸權穩定論批判——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歷史考察[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9]江紅.為石油而戰——美國石油霸權的歷史透視[M].上海:東方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