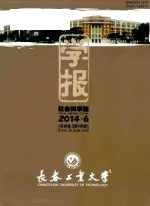封閉與融定的詩(shī)意結(jié)合——徽州古民居內(nèi)部設(shè)計(jì)之空間結(jié)構(gòu)分析與審美研究
馬榕君
(江蘇師范大學(xué) 美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徐州221116)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徽州古民居在建筑史上獨(dú)具地域特性,其內(nèi)部空間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也有著個(gè)性獨(dú)特的結(jié)構(gòu)秩序,并且顯溢著封閉與融定的詩(shī)意審美特質(zhì)。
建筑空間是建筑由物理存在而創(chuàng)造出的建筑場(chǎng)所,不僅具有使用價(jià)值,而且具有精神價(jià)值,體現(xiàn)一定的文化審美傾向。其空間結(jié)構(gòu)尤其是內(nèi)部空間結(jié)構(gòu)的合理設(shè)計(jì)與布局構(gòu)成了這種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
一、內(nèi)部空間結(jié)構(gòu)分析
結(jié)構(gòu)主義(Structuralism)的代表人物、瑞士心理學(xué)家皮亞杰在數(shù)學(xué)結(jié)構(gòu)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三種數(shù)學(xué)“母結(jié)構(gòu)”,即代數(shù)結(jié)構(gòu),原型為“群”;次序結(jié)構(gòu),原型為“網(wǎng)”;拓?fù)湫再|(zhì)的結(jié)構(gòu),原型為“拓?fù)洹薄榇耍覀兘栌眠@三種結(jié)構(gòu)的思想方法,并將其運(yùn)用到建筑空間結(jié)構(gòu)分析中,將代數(shù)結(jié)構(gòu)演變成并列結(jié)構(gòu),即各結(jié)構(gòu)之間不分主次、先后,同時(shí)存在,具有相容與不相容特點(diǎn),包括連接、接觸、集中式、串聯(lián)式、放射式、群集式、網(wǎng)格式。次序結(jié)構(gòu),各結(jié)構(gòu)單元之間有主次、先后關(guān)系,形成等級(jí)式、序列式結(jié)構(gòu)空間體系,包括重疊、包容、序列式、等級(jí)式。拓?fù)浣Y(jié)構(gòu),各結(jié)構(gòu)單元的關(guān)系為鄰接、連續(xù)和界限關(guān)系,以點(diǎn)、線(xiàn)、面的方式組合空間結(jié)構(gòu),并構(gòu)成空間結(jié)構(gòu)的分析方法。[1](P93-101)
徽州古民居整體結(jié)構(gòu)為次序結(jié)構(gòu)的包容式。一個(gè)大庭院包容著眾多的小單元房間,即中國(guó)式庭院結(jié)構(gòu)。其具體特點(diǎn)是以四周高大而封閉的圍墻包容著眾多的單元房間。為了防火,兩側(cè)均為高過(guò)屋脊頂?shù)鸟R頭墻。其內(nèi)部則為天井式結(jié)構(gòu),即并列結(jié)構(gòu)的集中式。以天井為中心構(gòu)成三合院或四合院,屋型一般為兩層或三層樓房,外部圍墻為磚石,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為木質(zhì)。三合院稱(chēng)為“一明兩暗”,堂屋明,兩廂暗,屬對(duì)稱(chēng)并列連接結(jié)構(gòu);堂屋稱(chēng)“明三間”,中間廳堂,兩側(cè)為客廳或臥房,也為對(duì)稱(chēng)并列連接式結(jié)構(gòu)。四合院的構(gòu)成,是在堂屋的對(duì)面,即天井的另一邊安排一個(gè)倒座房。天井與廳堂空間連成一片,在節(jié)日或重大活動(dòng)之時(shí),成為一個(gè)整體空間為活動(dòng)提供場(chǎng)所,其結(jié)構(gòu)又具有次序結(jié)構(gòu)的重疊式。平時(shí)廳堂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待客之用;天井用于散步、納涼、曬太陽(yáng)之用;有大型活動(dòng)則兩者共用。若想將整個(gè)庭院的單元繼續(xù)增加,即在廳堂的后墻即太師壁的后面,再增加一個(gè)倒座房,然后如前院一樣安排天井明三間,就構(gòu)成了后院?jiǎn)卧皬d堂與后院倒座房共用一墻,這種結(jié)構(gòu)稱(chēng)為“一脊翻兩堂”。前后院廳堂處于同一中軸線(xiàn)上。若想繼續(xù)增加則以此類(lèi)推,繼續(xù)由前向后擴(kuò)展疊加,也可橫向擴(kuò)展疊加。這種縱橫擴(kuò)展方法也符合拓?fù)渚W(wǎng)格法,即以太師壁這堵墻作為界限,也作為聯(lián)系的線(xiàn),以堂屋兩頭墻角的點(diǎn)為節(jié),將整個(gè)四合或三合院集合為面,采取鄰接與連續(xù)的手法,在這種不改變拓?fù)湫再|(zhì)的條件下,將原始網(wǎng)格——前院,經(jīng)拓樸變換轉(zhuǎn)變?yōu)樾碌木W(wǎng)格——后院。當(dāng)然,這種拓?fù)湟?guī)則網(wǎng)格式結(jié)構(gòu),也是一種串聯(lián)式結(jié)構(gòu),即前后各庭院?jiǎn)卧磸那跋蚝蟮姆绞脚帕羞B接。然而,從大的庭院范圍來(lái)看,整體庭院也符合序列式結(jié)構(gòu)。以四合院為例,其順序是:進(jìn)入大門(mén),見(jiàn)一小門(mén)廳,有屏風(fēng)門(mén),然后是廚房及儲(chǔ)藏間,向前是中部的天井,接著是一明兩暗,然后是明三間的一廳堂加兩臥,太師壁的祖先牌位處為建筑中心,若繼續(xù)向后拓展,則按前低后高的順序依次向后拓展。在一些大戶(hù)人家,其內(nèi)部空間結(jié)構(gòu),也有著嚴(yán)格的等級(jí)式區(qū)分。以宏村承志堂為例,在中軸線(xiàn)院落兩側(cè)增加了別院或偏房,其廊間和偏房則為傭人或轎夫居,中軸前廳為議事處,后廳堂為長(zhǎng)輩居住,這就是“前公后私”、“前下后上”,是等級(jí)式空間劃分。
徽州民居初建于南宋,現(xiàn)保存下來(lái)者大多為明清建筑,其建筑結(jié)構(gòu)已跨越初級(jí)階段的形象化而走向文化上更為成熟的象征化。風(fēng)水理論在建筑中處處體現(xiàn)著重要作用。陰陽(yáng)、五行、八卦及氣等理論結(jié)合著日照、風(fēng)向、氣候、景觀等運(yùn)用得十分考究,如天井的四方形處為四合院中央,即為“四水歸堂”,既考慮聚財(cái),又有通風(fēng)、聚氣、日照的作用。進(jìn)門(mén)的屏風(fēng)門(mén)即為擋煞氣作用,前后廳堂“前低后高”即為“前低后高,子孫英豪”等。
建筑空間的設(shè)計(jì)與建造,必須要考慮人的行為,人的空間行為又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密不可分。為此,空間的使用方式在空間行為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個(gè)人空間、公共性、私密性構(gòu)成了空間使用的主要內(nèi)容。當(dāng)代美國(guó)人類(lèi)學(xué)家霍爾提出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個(gè)人空間”,在建筑空間同樣適用。與此同時(shí),“私密性”空間也在空間理論中浮上水面。奧斯蒙德(Osmend)提出社會(huì)向心空間與社會(huì)離心空間,在空間理論上有著重要貢獻(xiàn)。社會(huì)向心空間具有公共性而缺乏私密性,社會(huì)離心空間則具有私密性而缺乏公共性。[1](P172)以此運(yùn)用到建筑空間上,徽州民居的廳堂為議事處,與天井連成一片,其空間結(jié)構(gòu)則構(gòu)成了公共性空間,所以在空間設(shè)計(jì)上呈開(kāi)敞式處理。廳堂兩側(cè)為臥室,屬個(gè)人空間,具有夫妻生活的私密性,所以封閉較嚴(yán),其門(mén)口又安排一“角廂”,角廂一側(cè)安排兩扇看似樘板壁的板門(mén),使得臥室更具私密性。二樓一般為小姐閨房,隔離著高高的距離,又為柱檐及門(mén)窗隔柵所擋,其私密性更強(qiáng)。而整個(gè)庭院高大的圍墻及窄小的門(mén)窗,又使得整個(gè)家庭的私密性得到強(qiáng)有力的保證。其內(nèi)部廳堂則屬于整體家族私密性中局部的公共性場(chǎng)所。
徽州民居成熟之時(shí),正處南宋理學(xué)興盛時(shí)期,因而,儒家思想文化在室內(nèi)空間結(jié)構(gòu)上和場(chǎng)所精神上,總是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以廳堂為例,太師壁上的祖宗牌位以及匾牌、兩邊大量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條屏、柱聯(lián),處處散發(fā)著三綱五常、忠孝禮義廉恥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廳堂與天井連為一體,在空間關(guān)系上,仰首為天,俯首為地,是天地的象征,大自然的陰晴雨雪,總是通過(guò)此空間與人們息息相關(guān),融為一體,其場(chǎng)所精神昭顯著強(qiáng)烈的天人合一思想,人與自然于此融通會(huì)合。
立體派的運(yùn)動(dòng)空間理論在徽州民居同樣存在,只是徽州民居呈現(xiàn)的是運(yùn)動(dòng)與封閉相混合的空間效應(yīng):廳堂與天井即為兩種空間相互運(yùn)動(dòng)滲透的場(chǎng)所;由門(mén)入天井、廳堂、各廂房、樓上、回廊、花園及各前后內(nèi)外院,是一條生生不息的運(yùn)動(dòng)鏈條;而各臥房的私密性、等級(jí)次序性及圍墻的圈護(hù),又形成了封閉性的一面,其空間的張弛有度都體現(xiàn)著深層的文化內(nèi)因。
二、詩(shī)意的棲居與審美
建筑的審美體現(xiàn)著建筑由物理使用價(jià)值向精神文化價(jià)值的升華,體現(xiàn)著人的情感與文化修養(yǎng)的介入,體現(xiàn)著主觀藝術(shù)創(chuàng)造。根據(jù)格式塔心理學(xué)理論,人的心理存在的心理場(chǎng)與外界客觀物質(zhì)存在的物理場(chǎng)一一對(duì)應(yīng),人的心理對(duì)外界的物理知覺(jué)感受稱(chēng)之為心物場(chǎng)。從建筑審美角度來(lái)看,人的心理對(duì)建筑空間物理的審美活動(dòng)即心物場(chǎng)的活動(dòng),只是這種活動(dòng)滲透著文化的體驗(yàn)與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并攜帶著詩(shī)意的萌動(dòng)。
古徽州地處江南丘陵之中,山川秀美,氣候濕潤(rùn),自古就有桃花源里畫(huà)里鄉(xiāng)村之稱(chēng),坐落在秀美山川環(huán)抱之中的徽州古民居,白墻黛瓦,清雅俊秀,詩(shī)意盎然。攜山川之靈氣,積文化之底蘊(yùn),韻味十足地應(yīng)現(xiàn)了海德格爾所夢(mèng)寐以求的“人詩(shī)意地棲居”的理想境界。
徽州民居的建筑意境是詩(shī)意的,對(duì)徽州民居內(nèi)部空間的審美體驗(yàn),同樣是詩(shī)意的。
(一)空間形式表現(xiàn)的審美萌動(dòng)
徽州民居的整體空間結(jié)構(gòu)為方形的分割與組合結(jié)構(gòu),給人以方正規(guī)矩嚴(yán)整之感,序列井然。在大的宅群里,各大方塊空間又以回廊過(guò)道相連接,如一盤(pán)流動(dòng)的棋局,點(diǎn)線(xiàn)面的布局,大小比例的對(duì)比,十分和諧。這也是中國(guó)文化審美注重方正秩序等級(jí)的顯現(xiàn)。各方塊空間又分出:私密性——靜的區(qū)域,如臥房、廂房;公共性——?jiǎng)拥膮^(qū)域,如天井、廳堂、廊道、花園等。整個(gè)院墻的圍合,又以整體的靜態(tài)為主導(dǎo),從而產(chǎn)生動(dòng)靜結(jié)合,靜中有動(dòng),動(dòng)中有靜的氣與力的波動(dòng)韻律。各部空間比例的大小不同,結(jié)構(gòu)的復(fù)雜變化,便產(chǎn)生了不同力量的對(duì)比節(jié)奏,而整體上則又在院墻方塊的圍合下達(dá)到均衡效果。自明代以來(lái),民居便演變成樓上低而樓下高,這便形成了樓下為主,樓上為次;樓下實(shí),樓上虛的效果。因?yàn)榧彝ブ饕顒?dòng)多集中在樓下,所以在尺度比例上,樓下高度突出,便不會(huì)產(chǎn)生壓抑感。尤其是廳堂連通天井,往往給人以心靈升騰飛越之感,在規(guī)矩井嚴(yán)四面圍合之中,便擺脫了束縛,釋放了性情。為了解決通風(fēng)透氣問(wèn)題,民居的窗門(mén)都采用了隔柵雕花手法,使得內(nèi)外空間得以勾連,在花園圍墻壁上嵌以透雕磚窗,又可借景入畫(huà)。引水圳之活水入院建養(yǎng)魚(yú)池及布置花壇安排花園,室內(nèi)空間便和自然融為一體,煥發(fā)出生趣盎然的萌動(dòng)活力,這便是徽州民居的空間形式審美妙處之所在。
(二)空間的審美文化心理與視覺(jué)情感體驗(yàn)
封閉與融定,是徽州民居內(nèi)部空間審美最為突出的體驗(yàn)。這一特征來(lái)自于一個(gè)移民群落心理內(nèi)部的深層憂(yōu)患。人的居住帶有一定的領(lǐng)域性,阿爾托曼將領(lǐng)域性定義為:個(gè)人或群體為了滿(mǎn)足某種需要,擁有或占用一個(gè)場(chǎng)所或一個(gè)區(qū)域,并對(duì)其加以人格化和防衛(wèi)的行為模式。人的領(lǐng)域性不僅包含著生物性的一面,也包含著社會(huì)性的一面。[1](P176)徽州居民大多是自秦漢至北宋以來(lái),社會(huì)大動(dòng)亂所造成的四次人口大遷移的移民,經(jīng)歷太多的恐懼與災(zāi)難之后,當(dāng)他們開(kāi)始重建家園時(shí),其強(qiáng)烈的移民憂(yōu)患意識(shí)便注定了他們?cè)谛藿ň铀鶗r(shí),不得不強(qiáng)調(diào)其強(qiáng)有力的防衛(wèi)措施。所以,其民居無(wú)一例外地建以高大厚實(shí)的圍墻作院墻,圈定了個(gè)體或家族的領(lǐng)域性,形成了整體的封閉空間。走進(jìn)了防備心十足的庭院,人頓時(shí)有一種安全和安定的感覺(jué),望著高高的圍墻,人的感覺(jué)不是被圈禁,而是一枚飄零的落葉終于回歸到了屬于自己的根,一個(gè)游子終于找到了家的歸宿。當(dāng)然,這是移民者的心態(tài)。然而,對(duì)于長(zhǎng)期生活安定的后輩子孫來(lái)說(shuō),為了清除高墻圍圈的閉塞感,就要在內(nèi)部空間設(shè)計(jì)上加大透氣感,于是天井與廳堂的敞開(kāi)式處理便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wèn)題。
對(duì)于中小戶(hù)家庭,廳堂天井不僅是議事待客處,更是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場(chǎng)所。一家老小祖孫幾代,冬曬陽(yáng)夏納涼,團(tuán)聚一起吃飯聊天,盡享天倫之樂(lè),歡樂(lè)融融,安定而富足。這便是徽州尋常百姓的審美精神境界。老子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lè)其俗”,[2](P61)安居融定,正是此意。
簾卷西風(fēng),寂寞心頭。徽州的男人,大多在外常年經(jīng)商,而女人則留在家里,照看老幼,操持家務(wù),加上封建禮教的束縛,徽州女人大多常年待在家里,在高高的圍墻的圈禁下,獨(dú)自寂寞地打發(fā)時(shí)光。尤其是夜靜更深,女人唯有以綿綿不絕的思念、流淌的淚水,寄托對(duì)遠(yuǎn)方親人的相思,排遣漫漫長(zhǎng)夜,封閉的空間,狹窄的臥室,便是她們賴(lài)以生存的空間。“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wú)計(jì)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3](P79)此情此景,寂寞與哀愁,便是審美的全部?jī)?nèi)容,而幽閉的居室空間,以及馬頭墻上的一輪殘?jiān)拢┰S寒星,便是承載審美的形式,此時(shí)的空間審美,唯獨(dú)對(duì)女人是無(wú)情與殘酷的。個(gè)體的心靈裂變經(jīng)歷,不是偶爾的風(fēng)花雪月,而是漫長(zhǎng)的幾十年,一代又一代,漫漫幾百年。與成年已婚女人有類(lèi)似經(jīng)歷的,便是樓上小姐閨房的少女。在封建禮教占主導(dǎo)地位的年代,男女有別,少女們的行走范圍,常常止步于樓梯口。所謂“大門(mén)不出,二門(mén)不邁”,青春歲月便在如此狹小封閉的空間里寂然度過(guò)。婺源理坑小姐樓小姐,甚至一輩子住在樓上。青春的萌動(dòng),情感的波瀾,世俗的壓力以及空間的封鎖,便是少女的生活全部。此時(shí)的空間審美,便是少女禁錮的煩惱與淡淡的哀愁。“佳節(jié)又重陽(yáng),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fēng),人比黃花瘦。”[3](P80)如此境地,誰(shuí)能猜透徽州少女的空間哀愁?
勤儉與虛閑的映現(xiàn)。上述的愁怨,只是針對(duì)徽州女性的愛(ài)情生活。然而,對(duì)于大多數(shù)徽州居民的大部分時(shí)光來(lái)說(shuō),他們是殷實(shí)而幸福的。勤勞樸實(shí)的作風(fēng),堆滿(mǎn)家院的勞作場(chǎng)景,以及雨季時(shí)光的虛閑,都寫(xiě)滿(mǎn)了這幽幽的空間,陶公的詩(shī)句:“戶(hù)庭無(wú)塵染,虛室有余閑”,就是對(duì)徽州民居空間說(shuō)的。
古淳肅雅之風(fēng)韻。黑格爾歷史決定論認(rèn)為:歷史中的任何片斷都可以鉤沉出其整體存在的樣子。作為徽州民居成熟時(shí)期空前勃興的理學(xué),深刻影響著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在建筑內(nèi)部空間上,留下了濃重的歷史文化痕跡。走進(jìn)民居,映入眼簾的便是遍布四周,以忠孝節(jié)義廉恥故事為素材精美三雕;四周廊柱的對(duì)聯(lián)、匾牌、中堂、條屏也常是儒家修身養(yǎng)性、讀書(shū)致仕求功名的言論,如“敦孝弟此樂(lè)何極,嚼詩(shī)書(shū)其味無(wú)窮”,“淡泊明志,清白傳家”,“作六州之保障,植萬(wàn)古之綱常。”每當(dāng)人駐身此景,儒家文化之遺風(fēng),便在這廳堂廊廂的空間之中撲面而來(lái)。儒文化向來(lái)追求“溫文爾雅”的審美氣質(zhì),這在徽州人的修身養(yǎng)性、家居空間布置方面,都有顯著的體現(xiàn):大量木質(zhì)建筑材料的選用及本色處理,加上精細(xì)的雕刻,懸掛四壁的國(guó)畫(huà)書(shū)法作品,青磚青石鋪就的地面,精致古香的條基、八仙桌、靠背椅等中式古典家俱及各種裝飾等,集合在一起作為這有限空間的表述,便演化出一種高古、清淳、整肅、文雅之意境,和天井處的“天人合一”之境,合在一起,悠然飄逸,彌散虛空。
幽邃冥想之化境。由于在四周筑以高墻,雖然開(kāi)天井采光,但是,徽州民居內(nèi)部光線(xiàn)仍然較暗。兩廂、倒座房及廊間最暗,臥房雖屬明間,但由于四周木板墻面的封閉,同樣很暗。尤其在陰雨時(shí)節(jié),室內(nèi)空間便呈現(xiàn)著一種幽邃朦朧的意境。光線(xiàn)幽幽,景象影影綽綽,如一層紗幔遮住天空,也如月明之夜,水乳般的月光皎然灑下,人處其中,在層層板墻的反復(fù)圍護(hù)之中,便有一種安全無(wú)憂(yōu)、悠閑舒適、超游物外、冥想空靈之感;悠悠然脫骨換胎,心空神游,漸入虛無(wú)之境。此時(shí),審美的主體與客體——建筑空間,便發(fā)生了交融互動(dòng),猶如水乳交融一般。主體不覺(jué)主體存在,客體也非居室空間,主客體打成一片,成為一體。這便是道家的虛無(wú)三境,亦或莊周夢(mèng)蝶之境,佛家的物我兩忘,身心俱空之境界,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境。事實(shí)上,徽州居民,尤其是歸隱田園的文人雅士,在此空間待久了,便會(huì)萌生遁世入道的意愿,諸如:“靜者心多妙,飄然思不群。有花方酌酒,無(wú)月不登樓”,“花能解語(yǔ)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登樓望月正是靜者所悟之妙境,人與石的和諧相處,亦即心與物的兩相交融。而“屋小僅能容膝,樓高卻可摘月”,所傳達(dá)的意境即是徽州民居內(nèi)部空間固然狹小,然而,在封閉圍墻的保護(hù)之中,在這種幽邃冥想的空間里人便可消解最初移民的恐懼心理,人與物——空間、自然,兩者便“相看兩不厭”,共融共通。心,便能融定安閑自在,獲得精神的自由,漸入審美之佳境,登樓摘月,遨游天外。
[1]詹和平.空間[M].南京: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6.
[2]寧志新.道教十三經(jīng)[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3]胡云翼,等.詞曲薈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