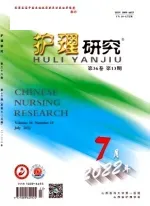護理領域評判性思維相關研究進展
陳靜雅,左鳳林,向燕卿,鄧 輝,汪芝碧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間信息的快速交流、我國社會的飛速發展及人們健康需求的不斷提高都對我國護理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新形勢下,護理人員既要注重實踐能力又要有創新意識,這就要求護理人員面對復雜的環境時要有較強的應對能力并做出相應的決策。評判性思維的培養正是提高護理人員以上這些能力的關鍵之一。我國護理領域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評判性思維進行研究,如今評判性思維已成為我國護理領域的研究熱點。本研究簡要介紹了評判性思維的起源、概念等基本情況,并對近年來我國護理領域評判性思維的相關研究進行分析。
1 評判性思維概述
1.1 評判性思維的起源 評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CT),也可譯為批判性思維。“評判性(critical)”一詞源自字根skeri和希臘字kritikos:前者意為切割、分離、分析;后者意為洞察力、判斷力[1]。CT的起源大體有兩種說法:有學者認為1933年美國教育家杜威出版的《How we think》一書中所提出的解決問題困難的5個歷程是探討CT的開始;也有學者認為CT這一概念起源于哲學,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提出,并將其作為一種教學思維模式和教育價值觀引入教育界,也就是“教育批判意識”,其本質是教育主體的解放,即教育者的批判意識[2]。
1.2 評判性思維的概念 自1964年Watson和Glaser兩位學者最早提出關于CT的定義以來[2],國外許多學者從心理、教育、哲學等不同角度對CT提出相應的定義,至今尚不統一。目前,為大多數學者接受的定義是20世紀90年代由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APA)提出的,是指有目的的自我調節的判斷過程,是個體對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做出判斷的互動的反映性推理過程,包括認知技能和情感傾向兩個方面。認知技能包括闡述、分析、評價、自我調節等思維活動的技能;情感傾向包括探索、自信、公正、靈活等多方面人格特征。
1.3 評判性思維的測評方法 現今,國際上常用的CT的評價量表包括加利福尼亞評判性思維意向問卷(CCTDI)、Watson Glaser評判性思維評價表(WGCTA)和加利福尼亞評判性思維技能測試表(CCTST)等。其中,CCTDI量表多用來測試受試者CT的意識情感傾向,而WGCTA和CCTST兩種量表多用來測試受試者CT的認知技能水平[3]。
1.4 評判性思維引入護理領域的時間 20世紀60年代,西方教育界興起研究CT的熱潮。提倡在教育中開設有關CT的課程。20世紀80年代后,英、美等許多國家將CT作為高等教育的目標之一。同期,CT被西方學者逐步引入護理領域。1986年,美國高等護理教育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AACN)將CT定為護理專業本科畢業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之一。1999年,國際醫學教育組織(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IIMF)制定的本科醫學教育的“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中包括7個宏觀教育領域,“評判性思維和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足見國際醫學界對CT的重視程度。20世紀90年代,CT被引入我國護理領域,我國護理學者開始對其進行探索性研究。
2 評判性思維在我國護理領域的發展回顧
2.1 起步階段 20世紀90年代,我國護理領域開始對CT進行研究。1996年,國內護理領域首次出現的關于CT的文章是由葉旭春[4]摘譯的一段大約三百字左右的國外文獻,從而拉開了我國護理CT研究的序幕。1997年,陳保紅等[5]較詳細地介紹了評判性思維的概念、結構、評價方法等,并對CT于護理教育的意義和培養學生CT能力的策略進行了探討,使國內護理學者對CT有了大體上的了解。此后直至2001年,我國護理學者在國內各類護理刊物上發表了十幾篇CT的相關文章。此期的文章主題多為介紹CT的理論結構、探討培養方法、護理教育中培養CT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分析等。較有影響的是陳保紅等[6]對CT的定義進行了系統的闡述,指出適合我國國情的護理學科的CT概念是關于護理決策有目的、有意義的自我調控的判斷過程和反思推理過程。可見,此期我國護理CT的研究多以理論性研究為主,是我國護理領域CT研究的起步階段。
2.2 過渡階段 2002年起,關于護理CT的文章逐漸增多。2002年—2005年,每年均有十幾篇關于護理CT的文章發表在各類護理刊物上。護理學者在不斷加深CT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上,逐漸開始了對護理CT的實踐性研究。學者們分析了我國護理教育的不足之處,提出相應的CT培養措施,如改變舊的教學觀念,積極提高護生的學習自主性,采用新的教學方法,制定全面的教學評價體系等都有助于提高我國護理人員的CT能力,同時也為護理CT的實踐性研究指明了方向。由此,國內學者開始在護理實踐中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試用國外先進的教學方法,并對其教學結果及護理人員的CT能力進行評價,對影響護生CT能力的因素加以分析。在分析評價的過程中,我國護理學者逐漸發現,由于各國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用國外的CT評價工具對我國護理人員進行測評時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彭美慈等[7]對CCTDI量表進行改編,修訂了CCTDI的中文版量表,即CTDI-CV。此量表用來測量CT的情感傾向,包括尋找真相、開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統化能力、CT的自信心、求知欲、認知成熟度7個方面特質。CTDI-CV量表符合我國文化,適應我國國情,即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又為我國護理人員CT能力的測評等實踐性研究提供了依據,對我國護理CT研究起到了推進作用。同期,我國學者不僅對我國護理CT的現狀進行分析,而且開始關注我國與其他國家護理CT的差異。如李小妹等[8]用CCTDI量表對中國與日本護理本科生的CT能力進行了比較性研究,得出總體上兩個國家學生的CT能力為中等水平,但各子條目得分有差異,可能與兩國不同的教育體制及文化背景有關的結論。這些研究都表明我國護理CT的研究已經逐漸從理論性研究過渡到實踐性研究,護理CT的研究已經引起我國護理學者的廣泛關注。
2.3 發展階段 2005年后,國內護理CT研究迅速發展起來。2006年—2007年,每年有近40篇的相關文章發表。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都逐漸細化,并注重國外相關研究的進展。如李秋萍等[9]對近年西方較普遍的CT教學方式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包括概念圖示法(concept mapping)、以病例為基礎的學習方式(case-study learning)、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方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以網絡為基礎的學習方式(web-based learning)、反思日記寫作(reflective journal writing)、循證模式(evidencebased model)、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等多種教學方式。每種教學方式都有其獨到的優點,如概念圖示法可以使學生較容易地了解各個概念之間的相關性,對加深CT的理解有重要作用[10];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方式較傳統的教師課堂講授方式更易使學生提高CT的情感傾向[11],其中尋找真相和開放思想這兩種情感傾向提高的最為明顯[12];以網絡為基礎的學習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收集到大量的前沿相關資料、書籍、最新技術信息等[3],有利于學生收集信息能力的培養。上述教學方法在國內雖也有試行,如蔣運蘭等[13]研究證實,開展循證護理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評判性思維能力,但由于文化背景、教育模式等條件的不同,西方教學模式并不完全適合我國護理教育。因此,國內學者正不斷研究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方式,如王維利等[14]對CT教學實踐的研究表明,采用討論式課堂教學、社會活動及臨床實踐三者相結合的教學方式,對提高學生的CT傾向是有效可行的。從近兩年發表的文章中可見,CT研究無論是研究內容的細化,還是研究方法的創新都表明我國護理CT研究已經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階段。
3 我國評判性思維研究的限制
3.1 理論研究較片面 CT包括情感傾向與認知技能,兩者相輔相成。近年來,我國護理領域的CT研究多注重情感傾向方面,對認知技能方面的研究較少。但具有較高的情感傾向并不一定有較強的認知技能,單純對于CT情感傾向的評價不能代表評判性思維認真技能的高低。研究表明,85%的學生具有情感傾向,而具有認知技能的學生只有38%。自CTDI-CV中文版量表修定成功以來,我國學者用此量表對CT情感傾向的研究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5]。大多數研究表明我國護理人員的CT情感傾向為中等水平,低于西方。但在未測評CT認知技能的前提下,部分學者即認為我國護理人員的CT能力也為中等水平是否恰當,是否比較片面,仍值得商榷。兩者的不同應在護理專業CT的課程設計、教學方式、評價方法等方面都應清楚表明[16]。護理教育者應同時重視學生情感傾向和認知技能兩方面的培養,尤其在臨床實踐中培養學生的認知技能十分重要。因此,必須全面了解CT的內容、影響因素,并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才能真正提高護理專業人員的CT的能力。
3.2 研究對象過于集中 近年來,我國護理CT研究對象多為在校學生或臨床護士,而對護理教育人員及護理管理人員研究較少。教育者及管理者在培養CT的過程中起到指導、監督、幫助、組織等關鍵作用,尤其是教師,在校教師及臨床帶教老師都是培養學生CT能力的重要環節,如國外有研究表明,當帶教教師的分析能力及尋找真相這兩種CT能力較強時,所教過的學生這兩種能力同樣突出[17]。我國護理教育者中對CT是否了解及自身CT能力高低都有待研究,這直接影響到護理CT的教育質量。因此,應拓展護理CT的研究對象,應涵蓋在校學生、臨床工作者、教育者、管理者等所有護理相關人士,重視其CT能力的培養;研究內容應涉及護理教育、護理管理、臨床實踐等諸多方面。
3.3 評價方法較單一 我國護理CT研究的迅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眾多新方法、新成果的試用和產生,這就要求建立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CT評價體系。CT能力的培養受專業價值觀、人格傾向等多方面因素影響。要想全面且有效的評價受試者的CT能力,評價的內容不僅要包括技能考核,還要關注受試者的情感、人格、價值觀等多個方面。同時,評價方式要多元化,除了各種量表的測評外,還可進行質性測評,如教師對學生的評價、學生間的相互點評、臨床實習成果等都可以評價學生CT的綜合運用能力。這些都是今后護理CT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4 學校教育與護理實際工作的銜接問題
4.1 課堂教育 目前,我國的護理院校教育主要是全日制教育模式,學生的知識主要是從書本及教師的講解中獲得。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給予學生正確的指導,幫助他們培養良好的思維習慣。要培養學生全面審視問題、獨立思考、得出結論的能力,并在教師的指導下對自己得出的結論進行反思并判斷其可行性,從而通過課堂教學達到提高學生CT能力的目的。當然,這就要求教師有較高的CT的能力。但課堂教育受時間限制,并非所有的學生都能提出自己的觀點,教師的反饋性建議只能針對個別學生,班級較大、學生較多時,教師不能面面俱到[18]。所以,并非所有學生都能得到鍛煉,并且,課堂教育缺乏實踐性,學生對個案分析仍停留在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如果想全面的提高CT的能力就必須結合臨床實習。
4.2 臨床實習 臨床實習是課堂教育與實際工作的中間環節。護理專業學生CT的能力在臨床實習中能真正地得到強化和鞏固。在臨床實習中,護理程序的任何一個環節,護理評估、護理診斷、護理計劃的實施及評價等,都離不開CT的指導。課堂教學只是基礎,真正的臨床實踐才能將學生的CT轉化成能力[19]。而學生CT能力的提高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及應用護理程序,從而為臨床實際工作做好準備。
4.3 護理臨床實踐 臨床護理畢竟是實踐性較強的工作,即使學生在校期間有過臨床實習,培養了較好的CT基礎,真正到了工作崗位上是否能有效地運用CT能力還未可知。臨床護理工作大多情況緊急、工作量大,這就要求護理工作者必須在短時間內分析問題并做出正確的判斷。學生走出校門進入臨床實際工作后,必定要適應一段時間,只有將學校教育培養的CT基礎與實際工作中不斷積累的臨床經驗相結合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護理工作者。醫院可以結合各科室特點,為臨床護理人員創造實踐CT能力的臨床護理氛圍,同時采用理論講解、組織討論、自我反思、工作記錄等方式繼續培養護理人員的CT能力[20]。CT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課堂教育、臨床實習及實際工作等都是CT培養的不同階段,只有各個階段銜接緊密才能真正提高臨床護理工作的質量,促進我國護理事業的發展。
綜上所述,我國護理人士對CT的相關研究還應繼續努力。培養護理人員的CT能力要從護理教育、護理管理、實際工作等多方面入手。在不斷深入了解CT的同時,要將其更好地應用到臨床護理工作中,使其指導臨床實踐,提高護理服務質量,為全面發展我國護理事業作出貢獻。
[1]王斌全,孟艷君.護理評判性思維的發展[J].護理研究,2007,21(4C):1127.
[2]劉義蘭,王桂蘭,趙紅光.現代護理教育[M].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257-276.
[3]Walsh CM,Seldomridge LA.Critical thinking:Back to square two[J].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2006,45(6):212-219.
[4]葉旭春.護理教師和護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的比較[J].解放軍護理雜志,1996,13(1):18.
[5]陳保紅,李樹貞,姜安麗.批判性思維與護理教育[J].國外醫學:護理學分冊,1997,16(13):113-115.
[6]陳保紅,姜安麗,李樹貞.在高等護理教學中培養批判性思維的若干問題探討[J].中國高等醫學教育,1998(1):7-8.
[7]彭美慈,汪國成.批判性思維能力測量表的信效度測試研究[J].中華護理雜志,2004,39(9):644-647.
[8]李小妹,Petrini MA,Kawashima A,等.中國與日本護理本科生評判性思維能力的比較[J].中華護理雜志,2005,40(10):730-733.
[9]李秋萍,王惠峰.國外護理教育中批判性思維教學策略實踐研究進展[J].中國護理管理,2006,6(9):26-28.
[10]Fonteyn M.Concept mapping:An easy teaching strategy that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and may improve critical thinking[J].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2007,46(5):199-200.
[11]Tiwari A,Lai P.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lectur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J].Medical Education,2006,40:547-554.
[12]Ozturk C,Muslu GK,Dicle A.A comparison of problem-based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on nursing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J].Nurse Education Today,2007,10:1-6.
[13]蔣運蘭,余陽燊.循證護理教學法對護理本科生評判性思維能力的影響[J].護理學雜志,2006,21(21):1-3.
[14]王維利,陳元鯤.評判性思維教學實踐及效果評價[J].中華護理雜志,2006,41(9):834-836.
[15]Profetto-McGrath J.The relationship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3,43(6):569-577.
[16]趙海平,于春妮.護理本科生批判性思維認知技能和態度傾向性的相關性調查[J].護理研究,2007,21(5B):1158-1162.
[17]Raymond CL,Profetto-McGrath J.Nurse educators’critical thinking:Reflection and measurement[J].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2005,5:209-217.
[18]Shin K,Jung DY.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nd skills of senior nursing students in associate,baccalaureate,and RN-to-BSN programs[J].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2006,45(6):233-237.
[19]Zygmont DM,Schaefer KM.Assessing th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faculty:What do the findings mean for nursing education?[J].Nursing Education Perspectives,2006,27(5):260-268.
[20]王芳.培養ICU護士評判性思維的實踐與體會[J].護理管理雜志,2006,6(4):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