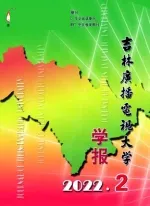法律夢想照進現實——讀《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兼評《我國基層司法的階段性思考》
劉鳳濤
(曲阜師范大學,山東 日照 276826)
法律的發展不是向誰看齊,向誰發展,而是應當屬于地區本身。
一、司法的地方性擴張的正當性
首先我贊同主報告人關于司法的地方性擴張論的提法,但并不同意主報告人認為“送法下鄉與政治權力的擴張相聯系,正體現了我國基礎司法的主要弊病”的說法。首先我也認為司法應當是在地方進行擴張,這樣做不僅有助于提高國家權力的運作,也有助于法律觀念的普及,在福柯看來“任何一種權力的考察,應當是從微觀層面,應當在權力運作的末梢,在一種權力與另一種權力交界的地方。”蘇力也提出“在考察當代中國國家權力時,我們不應當停留于法律文字的規定,或從‘共產主義國家’的概念中推演,更不應僅僅看行使權力的人是否有‘國家干部’的身份,或是否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國家相聯系,而應當看普通人如何同這些代表國家的人打交道,以及代表國家的人又以何種方式同國家權力意圖治理的對象打交道。”由于中國廣大的基層社會人群在知識和視野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對于司法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送法下鄉正是切合了這種實際情況,讓法律知識和法治觀念能夠深入到基層社會的各個群體中。所以說,強調司法的地方性擴張,是有利于了解國家權力邊緣地帶的相關事實和情況,也有利于依法治國的推進。
主報告人所謂的主要弊病是從司法中立方面來談的,認為送法下鄉所采用的“炕上開庭”是有違司法中立的原則,而我認為主報告人這種說法是牽強的,文中的案例清楚的指出“1996年,在地區和縣政府有關部們要求加強“依法收貸”的促動下,信用社向該縣法院派駐該鄉的人民法庭提出訴訟請求。”所以說這個案例中是符合“不告不理”的原則的,并非違背司法中立的要求,而且在法官的調解下,糾紛也得到了解決,也消除了“民間流傳”的錯誤信息,從而維護了各方的正當權利,筆者認為這是一起符合司法中立原則的案例。
二、村長“地方性知識的載體”的合理性
對于案例中村長的角色問題,主報告人可能認為他是妨礙司法中立的一個因素,但我卻贊同蘇力“地方性知識的載體”的評價,在基層社會中,我認為村長的存在是有利于糾紛解決的重要因素,現代法治是建立在陌生人社會或者個體主義社會之上的,而作為中國廣大的基層社會,卻是徹徹底底的熟人社會,根據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他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依法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主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用著這些設備。更進一步說,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而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已先發生了。”所以說,為了防止法律過于剛性和強硬的進入到基層社會的普通熟人生活中,村長從中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他不僅維護了司法的推行在思想改變村民傳統的非法治觀念,而且從側面也加強了自身的權威,從而促進社會結構的改革,使法治能夠在基層社會中順利前進。
三、司法技巧運用的實在性
對于主報告人關于“司法過程夾雜著軍事謀略就是在司法中加入了權力爭奪的內容”的看法是持否定態度的,我認為司法就應該要有謀略,實地的解決問題才是基層司法要做的事情,是解決基層社會糾紛的要求,我認為也應當是司法公正要追求的目標。案子判的再好再漂亮,不能執行于實踐,那就和一紙空文和空頭支票毫無差別,把餅畫的再漂亮而你卻不能吃,那我還要這個畫餅有什么用?而且執行難的問題現在也不可謂不嚴重,為什么?我認為這和一些人天天宣揚的嚴格依法判決和強調法官的絕對中立不無關系,而且所謂軍事謀略,并不是權力的爭奪,而是切實的解決了矛盾和糾紛,完全不應與權力爭奪的軍事謀略相提并論,顯然這里主報告人存在概念混同的問題。
四、基層法官不應失其專業性
主報告人第二部分中提出“基層法官不應失其專業性”這一點我完全贊同,但是對于基層法官的專業性的因素分析上,主報告人把司法判決還要動用其他因素來促成,看做為我國法律如此孱弱的主要原因這一說法我并不贊同。
我認為作為法院的法官,依法判案是首要的,但不應當只是完全的按照法律進行審判,如果那樣就和判決機器沒有區別了。不管法律的制定還是案件的判決,都應當是受到社會利益所影響的,而不單單只是為了法官的專業化而機械的專業化。卡多佐認為法院的標準必須是一套客觀的標準,在這些問題上,真正作數的并不是那些我認為是正確的東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認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會合乎情理地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由此可以看出,法院判案要考慮廣大人民的認可度和信任度,而不單單機械的依照法律。所以說,社會福利是法律的終極原因。
其次在判決的執行方面,借助其他因素更是必然的,如果單靠法院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那么就會變得相當有困難,法院的力量不管是在人力財力上還是在權力上都是達不到的。所以說這種依靠其他手段來輔助解決問題并非法官角色的“偏離”,而是逐步走上正軌的必須。
五、探尋法律的本質
最后:主報告人提出,“多種解決問題的式樣可能會逐漸模糊法律的本質但又概括的慣用司法之名。所以面對鄉土社會的熔爐,法律應該具有體現其本質的堅定性,這也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必然要求。”這一觀點更是引發了我的深思。
首先,我并不認為多種解決問題的式樣是會逐步模糊法律的本質,談到法律的移植的本土化界限問題,我認為解決問題的多樣化并不會模糊法律的本質,反而會提高法律的認知度和更好的本土化,為人民所接受,法律移植是法律發展的一種方法和手段,但是移植并非簡單的“拿來主義”,要根據本地的實際需要和具體情況進行選擇和變通,法律是流變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實驗,而作為西方的一些法律規則原則和精神,對我們可能并不完全適用,所以說適當正確變通,也就是上文中所說的“基層司法實踐中產生了多種式樣的應變解決機制”,我認為這恰恰就是反對拿來主義,根據中國具體實際進行變通的有力體現。
其次,法律的本質是什么?司法的本質又是什么?張文顯的《法理學》認為:(一)非馬克思主義法學關于法的本質的學說:法的本質是法的根本性質,是指法這一事物自身組成要素之間相對穩定的內在聯系,是由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構成的。(二)馬克思主義法學關于法的本質的學說:法的本質所揭示的并不是某個唯一的、終極的要素,而是法內在的一種矛盾關系。
第一,我不認為一個東西的本質是特定的、不移的。第二,我認為能夠合理的解決糾紛并為公共利益所服務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作為實用主義者的蘇力老師所貫徹的。“鄧小平曾經說過,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著耗子就是好貓”,這一句話雖然放在這里有些突兀,但是作為中國如此龐大的領土和復雜的民族,一味去強調法律的條條框框的客觀性和冷酷性,才會使法律失去本身的價值和作用。你被動司法,你一味的追求形式,結果只會導致人們不認識法律,不信任法官了,如果變成一個與人民毫無關系的東西,那么恭喜:最后也就沒有司法了。
在這里我還要談另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法律的本質的模糊,什么是法律的本質?西方有西方的定義和內涵,而這并不能成為限制中國法律發展障礙,我認為中國社會存在一個這樣普遍且正在普及的現象,就是外國的東西就是好東西,一味的追求和研究外國的這好那好,你好他好,把外國的東西奉為神圣,認為他們既是民主又是法治什么的,我想各國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發展都是不一樣的,你難以評定一個制度對于一個國家好就適用于全世界,我想說的是,在你走向“神”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
[2]費孝通.鄉土中國[M].人民出版社,2008,(10).
[3]本杰明·卡多佐[美].司法過程的性質[M].商務印書館,1998,(11).
[4]張文顯.法理學(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
[5]Michel Foucan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ed.by C.Gordon,Pantheon,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