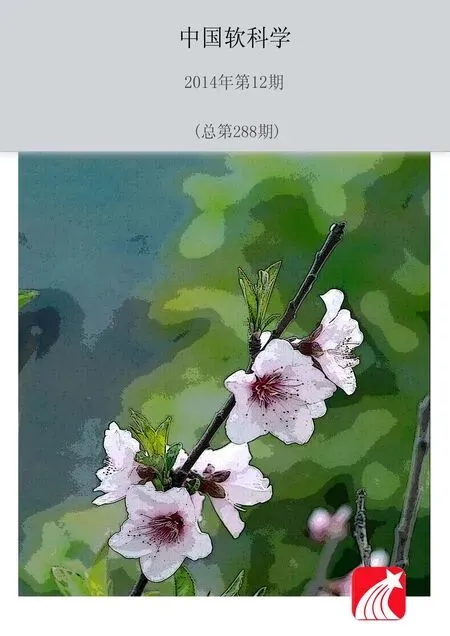基于威客模式的眾包參與行為影響因素研究
孟 韜,張 媛,董大海
(1.東北財經大學 薩里國際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2.大連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一、引言
伴隨著網絡通訊技術和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消費者獲取知識更加便捷,消費者具備了參與企業價值創造活動的能力。尤其是在Web2.0的時代背景下,企業更注重通過網絡與消費者進行交互作用,消費者不再是產品和信息的被動接收者而是創造者,企業的傳統創新方式也在向開放式、平臺式、協作式的創新模式轉變。由此,一種新型的企業與消費者的關系和企業商業模式、創新模式——眾包隨之產生。眾包(crowdsourcing)意指把傳統上由內部員工或外部承包商所做的工作外包給一個大型的、沒有清晰界限的群體去做[1]。
企業實施眾包的目的是利用企業外部的人力資源,即利用企業外部大眾所具有的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2],兼有降低成本、宣傳企業之效。因此,企業要想實施眾包必須了解眾包的參與者為什么愿意參與眾包項目,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的參與行為,企業可以從哪些方面入手激勵大眾積極參與眾包。只有吸引了大眾的參與才有可能進一步地激發大眾集體智慧作用的發揮,實施眾包也才有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眾包有多種類型,本文選取已有研究較少的威客模式為研究對象,對大眾參與眾包的行為進行解析,分析影響眾包參與行為的多種因素,試圖對企業如何激勵大眾積極參與眾包活動并提高其參與效果產生促進作用。
二、眾包研究綜述
眾包具有多種類型,包括:以Linux為代表的開源模式、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維基模式,以及威客模式等[1]。Afuanh和Tucci(2012)將眾包分為競標式和合作式兩種,多個個體接受企業或組織的發包并競爭取勝的威客模式屬于競標式,多個個體一起工作來解決問題的開源模式和維基模式都屬于合作式[3]。目前對開源模式和維基模式已經有了較多研究,對威客模式的研究較少。“威客”(Witkey)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指大眾出售智力產品獲取收益的互聯網交易模式;二是指通過互聯網出售自己的智力成果而獲取收益的人[4]。在威客網站上,任務的發包者或提問者在威客網站上提出具體的任務,感興趣的“威客”通過提交解決方案獲得報酬,威客平臺網站則可以獲得客戶提供的產品標價的一部分作為的收益來源或通過獲得廣告收入等其他方式盈利。知名的威客網站如InnoCentive、任務中國、豬八戒等。許多世界知名公司也都開設了專門的網站來邀請消費者和其他外部人員為公司提供產品創新思路和設計,如星巴克的My Starbucks Idea網站,戴爾公司的Ideastorm,寶潔公司的Connect+Develop;Iphone4的用戶也可以編寫游戲等應用軟件上傳到蘋果公司網站供廣大用戶下載。目前全球共有威客網站過千家,注冊會員超過1億人,交易額超過百億美元。
雖然眾包是一個較新的概念,但是關于眾包的一些研究已經遍及營銷、創新和組織等研究領域,和眾包相關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3類。第一類研究關注于參與眾包的大眾在眾包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大眾發揮的作用,消費者角色的轉換。第二類研究從企業的創新角度出發,認為企業不僅要利用內部的創意,更要整合外部創意,企業可以通過用戶創新、顧客參與、開放式創新來實現對大眾創新的吸收、整合和利用。第三類研究從生產和組織模式的角度,研究了眾包所形成的群體組織的性質,認為這種模式不同于企業,也不同于市場。
關于眾包參與者角色轉變的研究中,Kleemann和Günter認為消費者已經積極的、直接的參與到了企業產品和服務的整個提供過程中了[5]。他們指出眾包模式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消費者類型,即“工作的消費者”(Working Consumer),并進一步指出消費者的角色出現了轉變的趨勢,消費者現在變得更像是與企業一起創造價值的合作者(Co-Workers),消費者承擔了生產過程的一部分職能,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5]。托夫勒(2006)提出了“產消合一經濟”(Prosuming Economy)這一概念,并指出“產消合一”的重點將是企業將內部的部分工作轉嫁給消費者[6]。而到了Web2.0時代出現了“用戶生成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簡稱UGC)這一概念。用戶可以自己創造互聯網平臺上的信息和內容,用戶成為了“內容創造者”(Content Creator)。Prahalad和Ramaswamy(2005)指出消費者參與企業創新的模式正在挑戰公司傳統的價值創造模式,用戶通過互聯網,借助網絡的互動性、快捷、個性化和開放性等優勢,使得自身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參與度大大提升,并且這一影響正在蔓延到企業的整個價值鏈[7]。消費者的角色已經出現了轉換的趨勢,消費者從過去純粹的消費者向價值共同創造者轉變;消費者從產品、服務以及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向主動的參與者轉變;企業與消費者的關系也發生了轉變,由過去的企業提供產品和服務,消費者純粹消費和被動接受產品和服務轉變為企業和消費者合作開發產品、生產產品甚至銷售產品,消費者是企業價值創造活動的合作者。而這所有的轉變都為眾包的實現提供了可能,眾包中的大眾也正是具備這些新特點的新型消費者群體。
從企業創新的角度來看,眾包實質是用戶創新、顧客參與、開放式創新的新的表現形式。Hippel(1976)提出了“用戶是創新者”的觀點[8]。用戶創新理論強調不僅生產者可以進行創新,用戶也能夠進行創新,提倡關注用戶創新。在企業的眾包實踐中,相當一部分企業正是利用企業的用戶在進行產品和服務的改進、設計、以及提供。因此,眾包和用戶創新是密切相關的,而且眾包還有其獨特的優勢所在。眾包可以實現一個較大群體的互動,因此可以更好的獲取一個較大群體的顧客的隱性需求信息,而這對于企業開發產品和服務非常的有幫助。國外營銷學界對顧客參與(Customer Participant)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9],其研究歷程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從企業的視角研究顧客參與,該階段主要從經濟原理的角度,關注顧客參與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二是從顧客的視角研究顧客參與,主要探討顧客參與對顧客本身的影響,特別是對顧客感知質量和顧客滿意的影響;三是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來審視顧客參與,強調鼓勵顧客參與到價值創造過程,成為共同創造者將是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Chesbrough提出了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創新范式,他指出當企業在發展新技術的時候,應同時將企業內部和外部的所有有價值的創意結合起來[10]。眾包可以看作開放式創新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開放式創新的研究側重于組織之間的合作,而眾包比開放式創新更加關注于企業與大眾間的合作。
從生產模式和組織模式角度開展的一些研究更加深化了眾包的研究。互聯網為大眾合作生產提供了一個大規模合作(masses collaboration)的生產平臺,使得大眾進行生產成為了可能[11]。眾包之所以能夠創造價值,在于眾包利用了全球互聯網形成的網絡,而網絡節點上蘊含了賦有多樣化和個性化特征的資源[12]。Benkler將這種現象稱為是“基于共同性的大眾生產”(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認為這種模式不依賴于市場或清晰的組織層級,大眾是自發進行互動和協作的[13]。常靜等人認為大眾生產中大眾是自愿參與的,大眾與企業之間不存在雇傭和管理的關系[14]。開源運動領導者之一的Raymond在其《大教堂與集市》一文中使用“集市”(bazzar)一詞來比喻包括眾包社區在內的網絡社區的組織特征,以區別于大教堂似的企業組織[15]。傳統的生產方式是一種組織層級分明的,自上而下的類似于大教堂模式的組織,而眾包的生產方式則正是類似于集市的、自由的、松散的模式。Demil 和Lecocq提出了“集市治理”的概念,他們通過集市治理與市場、層級和網絡的比較分析認為集市治理具有三個特點:以開放許可作為特殊的合同關系、雙邊交易受到開源社群的影響、激勵與約束機制較弱[16]。雖然集市治理的激勵和約束力度都很弱,不確定性大,但是它能夠降低交易和生產成本、具有數量龐大的潛在參與者、形成了持續的互惠效應,因而集群治理有獨立存在的邏輯。
三、研究假設與模型
現有的針對大眾參與眾包的行為的實證研究多集中于從參與者的動機進行微觀層面的研究,從宏觀層面對眾包參與行為進行解析的研究較少。本文為了能更好地解釋大眾參與眾包這一行為,在較為宏觀的層面,引入在技術接受模型(TAM模型)[17]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技術接受整合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模型)[18],擬對哪些因素影響了大眾的參與行為以及如何影響進行研究。本文基于UTAUT模型構建了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在UTAUT模型中,社群影響是自變量之一,然而本文研究的威客模式是競標式眾包,單一參與者直接以在線方式向發包方遞交任務結果,具有競爭關系的參與者之間并未有或少有互動行為,顯然社群影響在本研究范疇中不適用。另一方面,本文認為眾包具有參與主體的三方關系(triadic relationship)、契約關系的松散型與短暫性等特點,這增加了作為交易行為的眾包的復雜性。因此眾包交易的完成依賴于三方關系的建立和延伸,直至信任關系產生,進而減少不確定性并防范機會主義[19]。本文認為參與者對發包方以及第三方威客網絡平臺的信任程度對眾包行為有重要影響,因而用信任替代社群影響作為一項自變量。其他自變量仍為參與眾包的預期收益、預期努力和促進條件,大眾參與的意愿為中介變量,參與行為作為因變量,以此模型檢驗自變量對大眾參與行為的影響情況,同時檢驗參與意愿的中介作用。

圖1 研究模型與假設
(一)預期收益對大眾參與意愿和參與行為的影響
Yang等人對“任務中國”上的威客進行的研究表明,威客對獲取報酬的預期是激勵和吸引他們參與的重要因素[20]。Lakhani等人對InnoCentive.com社區中獲勝大眾的研究表明大眾對貨幣獎勵獲取的預期是吸引他們參與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時還包括解決問題獲得的滿足感等其他影響因素[21]。Brabham對圖片網站iStockphoto眾包社區中的用戶調查顯示獲得金錢,提高個人技能,獲得樂趣是參與者加入社區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22]。Leimeister等人在對威客網站SAPiens的研究中指出大眾對學習知識或技能的提高,對報酬的獲得,對人際關系的建立和獲得職業機會的預期是影響其參與到社區中的重要因素[23]。這些研究表明吸引和激勵大眾參與到眾包活動中來是因為參與眾包活動能夠為參與者自身帶來某些利益,滿足他們的一些需要,有的學者將這些因素概括為內在動因和外在動因[24],也有的學者分為個人動因和社會動因[25]。無論何種分類,歸納這些因素有:經濟報酬、樂趣、知識獲得、職業發展、尋找新工作、技能提升、交友、成就感等。本文也由此來形成題項并衡量預期收益。本文認為參與者預期的眾包給參與者帶來的利益水平將會影響其參與意愿,進而影響參與行為。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大眾參與眾包的預期收益對其參與意愿有正向影響。
(二)預期努力對大眾參與意愿和參與行為的影響
大眾是否參與眾包活動,除了會考慮自己能得到哪些收益,同樣也可能會考慮如果他們參與眾包的容易程度或付出努力的程度。目前,參與眾包的大眾大多是利用閑暇時間來參與眾包的,因此大眾參與眾包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雖然參與眾包會為大眾帶來諸如收入、樂趣、滿足感等各種收益,但是如果參與眾包活動比較困難,需要付出過多的時間和精力等,那么大眾根本就無法支出如此多的閑暇時間。Lakhani等人的研究指出參與者有充足的業余時間也是促使參與者參與眾包的主要原因[21]。Sun等人在對國內眾包平臺網站“任務中國”中參與IT設計相關任務的威客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收益與成本比對參與者的滿意度有著顯著的影響,進而會影響威客的參與行為[26]。雖然,Sun等人沒有直接研究大眾的預期努力對其參與行為的影響,但收益與成本比可以間接表明參與者對付出的努力的預期可能會影響其參與行為。本文借用UATUT模型中預期努力的定義,用預期參與的容易程度來衡量努力預期。因而,大眾預期的參與眾包活動的容易程度會影響其參與眾包活動的意愿,進而影響其參與行為,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大眾對參與眾包的的努力期望對其參與意愿有正向影響。
(三)信任對大眾參與意愿和參與行為的影響
在眾包中,大眾與發包方以及眾包平臺之間進行了價值的交換,在這種交換的過程中就涉及三方之間的信任問題。史新和鄒一秀(2009)指出威客平臺中的作弊問題是阻礙用戶忠誠度提高的最大障礙[27]。同時,在智力成果的支付方面,通常是發包方將報酬支付給眾包平臺,然后眾包平臺扣除一些相關的服務費用后再支付給大眾,大眾通常是在方案提交后才能獲得收益,因此大眾可能面臨無法獲得收益的風險,在這一過程中眾包平臺網站的信用非常重要。因此,本文試圖對信任是否對大眾的參與行為存在顯著影響進行實證的研究。關于信任的定義并沒有形成統一的界定,信任的主要來源在于被信任者的能力、仁慈與正直這三種特征[28]。而且在實證研究中,學者們對信任概念的界定多集中于認為信任是信任方對被信任方的善意、誠實和能力的信心。因此,本文將信任定義為大眾對于眾包平臺和發包方在善意、誠實和能力方面所持有的信心,并將從誠實、能力、善意三個維度的變量來測量大眾的信任態度。因而大眾對眾包其他參與主體和眾包平臺的信任影響其參與眾包活動的意愿,進而影響其參與行為,假設3如下:
H3:大眾對于發包方和眾包平臺的信任對其參與意愿有正向影響。
(四)促進條件對大眾參與行為的影響
促進條件指使用者認為組織與技術設施支持信息系統使用的程度,分為感知行為控制、促進因素和兼容性3個子因素[18]。促進條件在本研究情景下,將促進條件定義為大眾認為參與眾包活動的過程中可以獲得的來自于其他組織或個人以及眾包平臺技術設施等方面支持的程度。根據本文的研究情景,在本文中促進條件只包括感知行為控制和促進條件這兩個子因素。其中感知行為控制反映了大眾所感受到的參與眾包活動過程中存在的自身知識與能力和外部環境的約束因素。促進因素指能夠使大眾完成眾包任務更加容易的客觀環境因素,包括來自眾包平臺、發包方,其他眾包參與者以及參與者的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當大眾產生參與眾包的動機之后,是否能獲得一些來自發包方以及眾包平臺網站等參與主體的幫助和支持也可能會影響其參與的積極性。目前,眾包平臺網站、發包方對眾包參與大眾提供的幫助較少,任務很多時候基本由大眾獨立完成,這可能會降低其參與的的積極性。史新和鄒一秀認為威客平臺存在著信息服務能力不足[27]。眾包平臺網站與大眾間的溝通渠道不足,大眾無法順暢的反饋所遇到的問題;發包方不能及時的回答威客的問題,對任務的輔助支持較少。而這些將不利于眾包任務的完成,也會影響大眾參與的積極性和信心。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假設4:
H4:促進條件對大眾參與眾包的行為有正向影響。
(五)參與意愿對參與行為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參與意愿是指個體企圖參與到眾包活動中的行為的主觀幾率,是其參與眾包的行為的意愿強度。參與行為是指大眾參與眾包活動所進行的所有活動,包括瀏覽任務、參與任務、提交方案等行為。Davis指出行為意愿是參與行為的最有力的預測指標,行為意向和參與行為之間存在著極強的正相關關系[17]。大量的學者將UTAUT模型應用于各種實證研究,實證結果大部分驗證了行為意向對參與行為有顯著影響。本研究認為眾包活動參與者參與的意愿程度越高,參與者參與的頻率也會相對較高,參與者提交任務的次數也會有所增加,相應的中標等其他行為也會較多,即大眾參與眾包的行為意愿與參與行為之間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5:大眾對眾包活動的參與意愿對其參與行為有著正向影響。
H6:參與意愿在眾包影響因素與參與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H6a:大眾對眾包活動的參與意愿在其預期收益對參與行為的影響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H6b:大眾對眾包活動的參與意愿在其預期努力對參與行為的影響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H6c:大眾對眾包活動的參與意愿在其對發包方和眾包平臺的信任對參與行為的影響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四、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數據,選擇 “豬八戒網”中的參與眾包活動的威客為問卷發放對象。“豬八戒網”是目前國內知名的威客網,個人通過該網站平臺參與和完成企業有償委托的包含創意設計、網站建設、營銷推廣、文案策劃、建筑裝修等上百種服務任務。目前平臺已擁有1000萬個人和企業參與者,完成了240萬次任務。“豬八戒”平臺運行比較成熟,注冊威客數目眾多,交易量大,具有典型性。同時,調查問卷的發放也要借助網絡進行,在“豬八戒網”上有威客的人才庫,在這些人才庫中可以找到威客的聯系方式,如郵箱,騰訊QQ賬號,甚至某些威客的電話號碼;而且在人才庫中可以進入威客的個人空間,在其個人空間里可以發站內信與威客取得聯系。本研究通過這些聯系方式,經詢問并得到威客的同意后,進行問卷的發放,提高問卷的回收率。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30份,回收206份,扣除存在回答前后矛盾、填寫不完整、回答有錯誤等問題的35份問卷,有效問卷數為171份。
為確保測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本文盡量采用國內外現有文獻已使用過的量表,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修改,如表1所示。具體問卷設計方面,本文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進行設計。同時,為了提高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在問卷正式定稿及調查之前,選取了30名“豬八戒網”社區參與者進行了問卷的預測試和深入訪談,對問卷中的相關題項進行了調整。
五、研究結果
(一)量表信效度檢驗
如表2所示,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結構變量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7,因此本研究的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所有題項均保留。本研究利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轉,提取了7個因子,并且各個分題項的因子最大載荷值均大于0.5,說明本研究中所用到的量表的效度較好。
(二)數據分析與解釋
本研究通過SPSS18.0采用逐步回歸分析的方法來驗證本文提出的相關假設。在回歸分析之前,對數據的多重共線性進行了檢測,容忍度(Tolerance)在0.576和0.836之間,并未接近于0;方差膨脹因子(VIF)在1.197和1.736之間,數值不大,因而均顯示不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可以進行多元回歸。
1.自變量對參與意愿的回歸
將預期收益、努力期望和信任作為自變量,參與意愿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可以看出總體回歸效果顯著,假設檢驗的情況如下:
① H1通過驗證。預期收益的t值為3.731,其值大于2,Sig.值0.000<0.05,預期收益對大眾參與眾包活動的參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這表明預期收益能顯著影響大眾參與眾包活動的意愿,參與眾包所能獲得的樂趣、額外收入、職業發展機會、新的工作機會,以及能力的提升等收益會吸引大眾參與眾包。
② H2不成立。預期努力沒有進入回歸方程,對大眾參與眾包的參與意愿影響不顯著。H2沒有通過驗證表明威客預計自己參與眾包活動的容易程度對其參與眾包活動的意愿沒有顯著影響,進而H6b也不成立。究其原因,首先,參與眾包之前用戶并不能很好的衡量參與的容易程度,大眾更在意收益的獲得,缺乏對其將要付出的成本的考慮與評估。其次,對于某些用戶而言,任務的困難和挑戰反而能夠為其帶來解決問題的樂趣和成就感,因此并不降低他們參與眾包活動的意愿程度。

表1 各變量量表 單位:百萬美元,現價

表2 信度與效度檢驗

表3 自變量對參與意愿的回歸結果
③ H3通過驗證。信任的t值為5.826,其值大于2,Sig.值0.000<0.05。信任對大眾參與眾包活動的參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2.自變量對參與行為的回歸
將預期收益、預期努力、信任、促進條件作為自變量,參與行為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從數據中可以看出,預期收益、努力期望、信任對參與行為有正向影響。由于這幾個因素與參與行為的關系并不是本文理論模型中的研究假設,因而不進行詳細分析和數據展示。而促進條件沒有進入回歸方程,對大眾參與眾包的行為沒有顯著影響,H4未通過驗證。究其原因,在威客模式中通常由威客自己獨立完成某項任務,而很少能夠獲得來自于發包方、威客平臺和朋友等其他群體的支持。由于一貫缺乏外界其他群體的支持和幫助,使其在參與過程中不太關注這方面的因素。
3.參與意愿對參與行為的回歸
將參與意愿作為自變量,參與行為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如表4所示,總體回歸效果良好,參與意愿的t值為5.417,其值大于2,Sig.值0.000<0.05,說明大眾參與眾包的意愿對其參與行為有正向影響。
4.參與意愿的中介效應分析
由表5結果可知,在模型1中,預期收益和信任對參與行為有顯著影響。在模型2加入參與意愿后預期收益和信任仍然顯著。因此,參與意愿在預期收益和信任對參與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H6部分成立,H6a和H6c成立。

表4 參與意愿對參與行為的回歸結果

表5 中介效應回歸分析結果
六、結論與建議
互聯網平臺加速了企業創新模式的演化,促進了顧客以及社會大眾參與價值創造與創新的興起。從長期來看,由于Web2.0時代為多主體間的便捷、即時、移動化的信息互動開創了難以想象的空間,因而這種依托互聯網的大眾參與創新的模式的發展也才剛剛開始。眾包模式應用的重點在于利用大眾的集體智慧,將企業內外部的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彌補內部資源的不足,獲得企業創新的新動力。眾包的參與者成為與企業共同創造價值的合作者,他們不再是純粹的消費者,他們是兼具生產者、創造者和消費者等身份的統一體,這是一種新型的消費者-企業關系和創新模式。
企業如果擬采用眾包模式,必須要吸引大眾的參與,必須要了解哪些因素會影響大眾的眾包行為。本項實證研究證明,參與眾包的預期收益和對眾包平臺和發包方的信任會給參與眾包的意愿和行為的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根據前文論述和實證研究結果,本文提出以下管理建議:
第一,企業需重視應用眾包模式。企業通過采用眾包這一新型商業模式、創新模式可以利用企業外部的人力資源,利用顧客和大眾的知識與技能來開發產品和服務,并能提升顧客體驗和滿意,從新的途徑來加強顧客與企業的關系。因而并不是資源缺乏的小企業才適合使用眾包模式,大企業也需應用眾包,這一點已被諸多國外知名大企業成功應用眾包的實例所證明。和國外相比,國內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在眾包模式應用方面還比較滯后。是自建網站,還是利用第三方眾包平臺?采取競標式,還是合作式?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應著手探索適合企業自身發展的眾包應用方式。
第二,建立完善的信任機制。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了大眾對眾包平臺和發包方的信任不論對其參與意愿還是參與行為都有顯著影響,因此威客平臺要建立完善的信任機制,提升大眾對眾包平臺和發包方的信任。一方面,眾包平臺應該信守對參與大眾的承諾,積極提升服務水平,樹立良好的眾包平臺的品牌。另一方面,眾包平臺應該審核發包方的資質,建立發包方的信用記錄,并將發包方的信用記錄對大眾公布。
第三,建立合理的定價機制,提高大眾預期收益。目前的眾包類型中,雖然有些活動大眾是無償參與的,但是越來越多的眾包活動給參與者提供了貨幣性報酬。而大眾預期收益中往往對貨幣性報酬的預期是主要因素,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一點在國內更為顯著。尤其是在威客模式這種眾包類型的活動中。因此威客網站應當建立合理的定價機制,網站管理者可以對發包方的定價制定統一的標準,對定價進行指導、評估和管理,促使發包方制定合理的眾包任務價格,確保大眾參與眾包活動能獲得應得的報酬,從而提高大眾參與積極性。
第四,從多途徑提升大眾參與眾包的預期收益。在眾包平臺上參與任務的大眾多是具備相關技能的大眾,同時眾包平臺上有很多雇主,因此眾包網站可以給參與的大眾建立一個人才庫,這樣不僅有利于用人企業獲得所需人才更能增加大眾的就業機會,提高大眾參與眾包活動的預期收益。除此之外,在預期收益中,成就感也是大眾看重的一個方面。眾包平臺網站可以根據投標次數、中標次數、雇主滿意度等等方面的指標來對大眾進行評級,并在其標志中顯示其級別。眾包網站可以對高級別威客或一些“明星威客”在網站中進行宣傳、或組織見面活動、或給予物質獎勵,一方面滿足其成就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勵其他威客。
第五,提高眾包平臺的服務水平,降低大眾參與難度,提供更多促進條件。在實踐中,促進條件與努力預期還是能夠影響大眾的參與意愿,眾包平臺需要在這兩方面進行改善。首先,建立任務描述標準,并進行嚴格審核,使大眾明確任務要求,使其參與更加容易。這樣既可以減少大眾判斷任務完成要求所要付出的努力,也可以使大眾更好的選擇參加與自身能力更匹配的任務,使大眾參與容易程度提高。其次,眾包平臺應該和參與大眾之間建立順暢的溝通渠道,建立充分有效的反饋機制,盡可能的為大眾提供幫助;提供完善和直觀的大眾參與教程;精簡的任務操作流程;建立大眾交流社區;發包方應該積極、快速解決參與大眾對眾包任務提出的疑問。
七、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以下研究局限。首先,本文對眾包模式類型的選擇是有限的。本文只選擇了威客這種形式的眾包模式,并沒有對開源模式、UGC模式(用戶創造內容模式)等其他眾包模式進行實證研究。而且威客平臺屬于第三方平臺,在眾包模式中企業可以自建眾包平臺,本文沒有研究這類企業自建平臺的眾包模式。不同類型的眾包模式的大眾參與行為影響因素會有所不同。其次,沒有對預期收益進行進一步分析。預期收益可分為內部收益、外部收益,或者經濟收益、社會收益,本文沒有設定預期收益的二級指標,沒有進一步考察不同收益類型對參與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再者,預期努力對參與意愿的影響和促進條件對參與行為的影響在本實證研究中并未得到驗證。這只能說明本研究采集的數據不支持這兩個假設,并不說明理論是錯誤的。如果樣本量再擴大一些,或者采取實驗法,也許會得出更接近實際的結果。眾包在發達國家已經大量進入商業應用階段,在中國卻還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隨著Web2.0應用工具的發展,以及參與、共享、協作、創新的文化理念的普及,未來中國企業的眾包以及威客模式的應用將快速增長。對此的理論研究也急需發展。上文研究局限中提及了需進一步研究眾包其他類型的影響因素、不同預期收益類型的分析、兩個未證明假設的驗證。除此之外,未來該領域的研究還可以在以下方向開展。
第一,研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網絡機制。在現有的威客模式下,參與者通常是單獨完成任務的,但是在開源模式、維基模式等其他眾包類型中,每個參與者僅完成一部分的任務,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很頻繁,參與者形成的網絡成為企業網絡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網絡中,企業和大眾,大眾之間如何互動?以及不同的互動方式和互動程度對這一網絡的發展、眾包的成功、企業的創新將會產生何種影響?這些都是需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研究不同類型的參與者、不同類型的眾包任務的影響因素。可以對不同參與度的大眾參與行為影響因素進行比較研究,如核心參與者與邊緣參與者的比較;對參與不同眾包任務類型的大眾參與行為影響因素進行比較研究。
第三,研究參與動機、行為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眾包已成為顧客和大眾參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途徑,因而需考察顧客和大眾參與動機和參與行為對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以及顧客和大眾的知識如何向企業內部轉移,與企業內部研發和知識管理體系如何融合。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如何化解這些負面影響[32]。這方面研究所得出的管理建議將有助于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
參考文獻:
[1]HOWE J.Crowdsourcing: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M].New York: Crown Business Press, 2008: 23-25.
[2]BROWN P, LAUDER H.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C]//BARON S,FIELD J,SCHULLER T.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226-242.
[3]AFUAH A, TUCCI C L.Crowdsourcing as a solution to distant 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2, 37(3):355-375.
[4]LIU Feng, ZHANG Linlin, GU Jifa.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witkey mode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and Syestems Sciences, 2007, 4(4):341-352.
[5]KLEEMANN F, GüNTER G, RIEDER K.Unpaid innovators: The commercial utilization of consumer work through crowdsourcing[J].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 Studies, 2008, 4(2): 5-26.
[6]TOFFLER A.Revolutionary wealth[M].New York: Knopf Press, 2006:137-139.
[7]PRAHALAD C, Ramaswamy V.The future of competition co-creating unique value with customers[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5:8-13.
[8]HIPPEL E V.The dominant role of users in the scientific instrument innovation process[J].Research Policy, 1976(3): 212-239.
[9]SILPAKIT P,FISK R P.“Participatizing”The service encount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C]//BLOCK T M,UPAH G D,ZEITHAML V A.Service marketing in a changing environement.Chicago, IL: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85:117-121.
[10]CHESBROUGH H.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2-6.
[11]TAPSCOTT D, WILLIAMS A.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M].London: Portfolio, 2006: 6-11.
[12]鐘耕深,朱雅杰.基于眾包的商業模式優化[C]//第五屆(2010)中國管理學年會——組織與戰略分會場論文集.2010.
[13]BENKLER Y.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and virtu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 14:394-402.
[14]常靜,楊建梅,歐瑞秋.大眾生產者的參與動機研究述評[J].科技管理研究,2009(5):423-425.
[15]RAYMOND E S.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Musings on linux and open source by an accidental revolutionary[M].Sebastopol,CA: O’Reilly, 1999:23-36.
[16]DEMIL B, LECOCQ X.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or network:The emergence of bazaar governance[J].Organization Studies,2006, 27: 1447-1466.
[17]DAVIS F D.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MIS Quarterly, 1989, 13(3): 319-340.
[18]VENKATESH V, Morris M, Davis G B,et al.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J].MIS Quarterly, 2003, 27(3): 430-450.
[19]LUHUMAN N.Trust and Power[M].New York: Wiley, 1979.
[20]YANG J, Adamic L, Ackerman M.Crowdsourc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Strategic user behavior on task[C]//Pro-ceedings of the 9th ACM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commerce.2008.
[21]LAKHANI K, JEPPESEN L, LOHSE P.The value of openness in scientific problem solving[Z].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7.
[22]BRABHAM D.Moving the crowd at iStockpho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rowd and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a crowdsourcing application[J].First Monday, 2008, 13(6): 84-95.
[23]LEIMEISTER J,Huber M,BRETSCHNEIDER U.Leveraging crowdsourcing: activation supporting components for IT-based ideas competi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9, 26: 197-224.
[24]HARS A., OU S.Working for free? Motiva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open source project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2, 6 (3): 25-39.
[25]CIFFOLILLI A.Phantom authority, self-selectiv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members in virtu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Wikipedia [J].First Monday, 2003,8(12): 57-72.
[26]SUN Y, WANG N, PENG Z.Working for one penny: Understanding why people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tasks with low payment[J].Computers in Human Bahavior, 2011, 27(1):1039-1049.
[27]史 新,鄒一秀.威客模式研究述評[J].圖書與情報,2009(1):71-72.
[28]MAYER R, DAVIS J.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 709-734.
[29]RYAN R, DECI E.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ic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25:54-67.
[30]MCKNIGHT D, CHERVANY N.What trust means in e-commerce customer telationships-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ual typ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2, 6: 35-59.
[31]THOMPSON R, HIGGINS C, HOWELL J.Personal computing: Toward a conceptual model of utilization[J].MIS Quarterly, 1991, 15(1):124-143.
[32]CHAN K W, YIM C K, LAM S.Is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value creation a double- edged sword? Evidence from profess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Across Cultures[J].Journal of Marketing, 2010, 74 (2): 4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