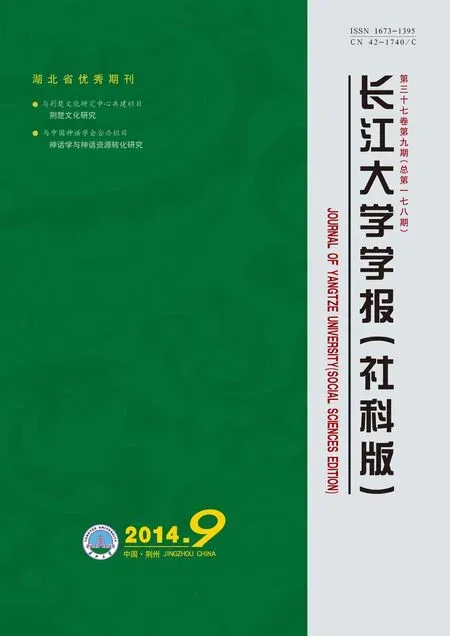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移民、難民與經濟
李芳
(長江大學 文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0 )
陜甘寧邊區建于1937年,位于陜北、隴東、寧夏東南交界處,以陜北為主,總面積最大時為12、9萬平方公里(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國民黨軍隊的侵占,減至9、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為200萬。1941年邊區總人口1342634人,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綏德分區總人口544552人,人口密度為49.5人/每平方公里,占邊區總人口的40.57%;人口最少、人口密度最小的三邊分區總人口67687人,人口密度為2.6人/每平方公里,占邊區總人口的5%。[1](P36) 邊區人口分布不均的狀況由此可見一斑。造成這種分布狀況的原因與陜甘寧邊區的黃土高原地形地貌相關。黃土丘陵高山、溝壑綿延,難以形成較大的聚居區,只有較為平坦的高原地帶才會有大片的人口聚集。
陜甘寧邊區地處我國西北干旱少雨的黃土高原地區,溝壑縱橫,干旱少雨,不利于農業種植。農業生產技術落后,工具簡單,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業的開發是以擴大耕地為主的粗放型的開發。同時農村副業以及工商業的發展都極其有限。“抗戰時期,由于受戰爭的破壞,僅有耕地8.431萬畝。副業如植棉、紡織等大都停頓。畜牧業只有牛、驢等大牲畜10萬多頭,羊40多萬只。工商業衰落,食鹽運銷停頓,公營工業僅有200多人的軍械所和被服廠兩處。”[2](P61)從陜甘寧邊區當時的經濟狀況來看,可耕種土地稀缺,農業生產不足,工商業極不發達,無法拉動經濟增長。
全面抗戰爆發后,移民、難民的涌入,一方面為邊區的生產、抗日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另一方面對邊區的生態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問題。
一、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移民、難民的成因、數量和安置
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府正面戰場的失利,大批移民、難民紛紛涌向陜甘寧邊區,邊區政府采取適當措施進行了安置和救濟。
(一)陜甘寧邊區移民、難民形成的原因
首先,國民黨政府正面戰場的失利是陜甘寧邊區移民、難民潮形成的主要的原因。“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步步加深,無數的中國人民在敵人炮火之中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數以萬計的淪陷區人民為躲避戰火,紛紛背井離鄉而淪為移難民,其中一部分輾轉進入邊區”。[3](P56)其次,國民黨政府鼓勵移民的政策對其有一定的推動。抗戰爆發后,在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往重慶的同時,也將中東部、沿海地區工業、高校陸續內遷,為繼續抗戰提供經濟保障和人才支持。數以萬計的淪陷區人民遷往西部邊區,其中一部分來到了陜甘寧邊區。第三,自然災害。1942年河南大旱災引起的中原大饑荒就使豫籍災民入陜者先后達到80萬人。1943年河南又遭水蝗災,不僅重創了河南等中原地區,由此也產生了數量極為龐大的難民。第四,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出臺了一些獎勵移民的政策和實施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移民、難民來到邊區。
(二)移民、難民的數量
邊區的移難民主要包括邊區外移入的難民、向往共產黨的領導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和工人、來到邊區做生意的商人以及邊區內部人口的遷移。據統計,抗戰期間,邊區移難民達到了266619人。1944年3月民政廳統計的邊區人口總數為1424786人。因此,邊區移難民占當時邊區總人口的18.7%,移民數量是相當驚人的。

表1 邊區1937—1945年移民難民人口流動數量統計表[4]( P400)
邊區內部人口遷移。在邊區的移民運動中,邊區內部人口的遷移也是其主要的內容之一。由于邊區人口分布不均衡,綏德分區人口最為稠密,而三邊分區人口最為稀少。陜甘寧邊區成立后,組織邊區內部人口遷移。“1941年內移民8527戶,27744人,其中移居延安縣的人口11684人”。[1](P38)1942年,邊區政府繼續實施內部移民。“1943年,從綏德分區移出的1836戶,4961人,其中全勞力與半勞力約占總數的55.75%”。[1](P38)這其中也包括進入邊區的移難民的遷移。由于實行了有效的內部移民措施,使邊區的勞動力資源得以合理的調劑。
(三)移民、難民的救濟與安置
陜甘寧邊區的移難民經歷了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1937—1940年間移難民運動基本處于無序狀態。1940年以后邊區政府出臺了第一個優待移難民的條例,1943年以后走上了正軌。“邊區政府為了妥善安置如此眾多的難民,制定了一系列條例、制度,采取了諸多有利措施使難民救濟工作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5](P88)
首先,自愿原則。1940年3月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優待外來難民和貧民之決定》。《決定》規定:凡淪陷區域,非淪陷區域之難民貧民,如自愿遷入陜甘寧邊區居住,從事勞動生活者,均準許自行遷入。
其次,對移難民實行救濟。1941年5月27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發出了《關于賑濟災難民的指示信》,要求各縣應將已撥之糧款,迅速發放,并強調:放賑只是個消極的方法,積極的辦法是以工代賑,改進生產工具,擴大生產以及動員廣大人民互相調節救濟。
再次,妥善安置移難民。邊區政府設立了移民接待站,對于進入邊區的移難民由各縣區政府進行登記,把移難民調劑到各個移民的開墾區,移難民在居住、墾荒、貸款、醫療方面都有一定的優惠政策。據不完全統計,僅1942、1943年兩年內,邊區政府就發放救濟糧4000余石,調劑窯洞6240孔,調劑熟地8、67萬畝,農具9100件,耕牛1388頭,種籽180多石。[6](P598)
此外,邊區政府對移民墾荒進行獎勵,在政治上也規定移民、難民和邊區人民享有同等的權力,使得大批移民、難民來到陜甘寧邊區能夠安居樂業,恢復和發展生產。
二、移民、難民對陜甘寧邊區的作用
(一)移難民推動了陜甘寧邊區經濟的發展
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移民、難民對經濟發展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增加了陜甘寧邊區的勞動力。陜甘寧邊區地廣人稀,再加上連年戰亂和自然災害,勞動力資源短缺。移難民絕大多數為農民,遷往邊區正好為邊區增添了勞動力。根據1944年西北局調查組對關中分區的新寧、赤水、淳化和同宜耀四個縣的調查統計,農民占全部移民總數的93.6%,手工業者占5%。這兩項就占了移民總數的98.6%,還有商人、學生等,當然也有少數農民兼營商業。[7](P647)1942年、1943年兩年,移民中勞動力的比例分別是46%和60%。[7](P640)大量移民勞動力的投入,使邊區的農業生產獲得急缺的勞動力。
推動了邊區農業的發展。移民進入邊區以后,邊區政府組織他們廣泛墾荒,開展大生產運動。據1943年2月統計,邊區5年擴大耕地面積240萬畝,其中200萬畝是移民開荒增加的。1943年增產細糧8萬石,60%是移民完成的。[4](P424)移民推動了邊區的農業生產,也解決了邊區的軍民糧食問題,為抗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推動了邊區工業的發展與繁榮。陜甘寧邊區在抗戰之前基本上沒有工業。原有的可以算作現代工業的油礦在內戰時期被破壞掉了,保留下來的基本上都屬于作坊式的手工業和家庭紡織業。要抗戰,要發展經濟,邊區面臨著巨大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技術和人員問題。移民中有一些知識分子,如“抗日大學第五期共有學員13390人,其中外來知識青年有10403人”[8](P40)在抗大其他期、延大等學校中也有一些外來的高素質移民。他們對邊區的教育、人口素質的提高以及工業的發展都起了推動作用。如在機械工業和軍事工業上,來自浙江的沈鴻不僅帶來了11部機器,還帶了7名技術工人,后任邊區軍工一廠廠長,奠定了邊區機械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著名的有機化學家錢志道1938年來到邊區后,也使邊區的化學工業建立并發展起來。此外邊區還設立了移難民工廠,其中的移難民在技術革新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較高素質的移難民在工業發展中基本上都擔任了指導性職務,他們在培養邊區工業發展急需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邊區商業的發展也起到一定作用。邊區商業蕭條,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后,國民黨對邊區實行了封鎖,邊區的商業貿易發展極其困難。移民在邊區商業的發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據1944年西北局調查組對新寧、赤水、淳化、同宜耀四縣的統計,商人占移民總數的1%,此外還有為數不多的農民兼營商業者。他們活躍了商業貿易,例如,“在延安市,1941年邊區以外的商戶占了2/3,其中戰爭爆發后遷到邊區的10大家占了延安市全部商業資本的1/2以上”。[9](P20)
總之,移難民的遷入對當時陜甘寧邊區經濟的發展有著很顯著的影響。毛澤東同志就曾說過:“移民是發展農業的條件之一。”“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積擴大了,也發展了牧畜,繁榮了商業”。[10](P756)
(二)移民、難民對陜甘寧邊區的負面影響
抗戰時期移民、難民對陜甘寧邊區也有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人口壓力之下的經濟開發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破壞。
移民、難民涌入陜甘寧邊區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也增加了邊區軍民糧食的負擔。因此,邊區選擇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發展道路。而邊區農業的開發,屬于粗放型的開發模式,大量燒荒,開荒,濫墾濫伐,甚至在不構成耕地條件的坡地也開荒。1937年邊區的耕地面積為862、2萬畝,1945年抗戰結束時為1425.6萬畝[9](P85-86),八年的時間增長了560多萬畝,每年差不多增長70萬畝。雖大大擴大了耕地面積,解決了邊區軍民生存問題;但同時也破壞了邊區的生態環境,造成水土流失加重、水旱災害頻繁。1940年《陜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團報告書》明確指出:“在洛河流域、延河流域、葫蘆河流域以及沮水、汾川、清澗河等地,因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進行著掃蕩的砍伐呢!”[9](P123)
林業、工業的開發也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林業中大量的砍伐,工業中馬蘭紙的制造,都導致水土流失嚴重。
因此,“盡管邊區農業開發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總體上來說開發水平不高,大量的開荒、濫墾濫伐,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破壞”[11](P21)。這種不計后果的開發方式是當時特定情況下產生的結果。隨著戰爭結束,我們理應重視生態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牛昉,康喜平.陜甘寧邊區人口概述[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3).
[2]張杰,王省安.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人口發展[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4).
[3]張志紅.初探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移難民的源流[J].殷都學刊,2002(1).
[4]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9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
[5]高冬梅.陜甘寧邊區難民救濟問題初探[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3).
[6]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3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
[7]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2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
[8]李志民.革命熔爐[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
[9]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4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澤東選集[M].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
[11]王沛,郭風平.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農業開發研究[J].農業考古,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