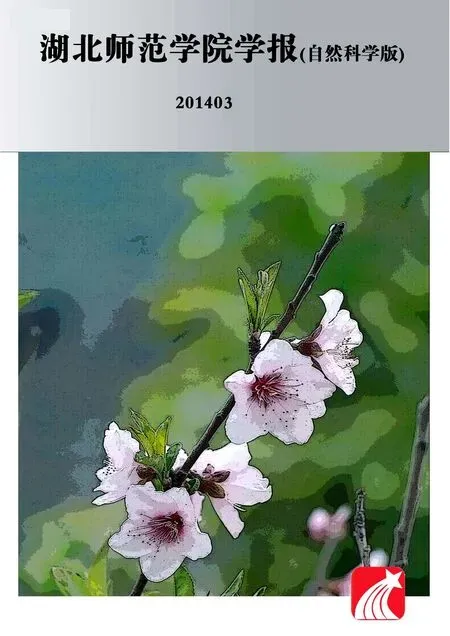偏側化預備電位研究述評
郭志平 ,李安民 ,李正中
(1.上海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學院,上海 200438;2.湖北師范學院 體育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偏側化預備電位研究述評
郭志平1,2,李安民1,李正中2
(1.上海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學院,上海 200438;2.湖北師范學院 體育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偏側化預備電位(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LRP)是與運動準備相關的一個腦電成分,基于運動肢體對側大腦皮層的預備電位波幅高于同側的特點而獲得。LRP作為反應準備的在線測量方法,獲得并準確檢測其出現是關鍵,而了解其特點及影響因素是恰當運用該方法的保證。未來研究應著力于提高LRP的效度,將LRP與其它測量方法相結合。
偏側化預備電位;認知;運動準備;抑制控制;運動表象
人類需要進行各種運動以應對內外環境的變化,但是有關外顯運動出現前大腦認知系統是如何加工和組織運動信息的,對此,我們無法通過直接觀察獲得。心理生理學測量,特別是事件相關電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s,ERP),作為心理事件和生理事件的標志,成為了解人類思想和大腦的一個窗口[1]。而與運動動作的準備和執行密切相關的一個ERP成分,偏側化預備電位(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s,LRP),則為我們了解外顯運動開始前大腦對運動的加工和組織過程打開了一扇窗。
LRP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揭示潛在的認知加工的時間特性,特別是在有關運動準備與反應選擇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因此,自LRP被發現以來,已經在主流認知心理學的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的研究和應用。研究者通過設置一些實驗條件,利用LRP的時程、波幅以及極性等參數,能清楚地了解心理加工階段和時程特點。系統地梳理有關LRP本身的研究,對我們充分了解LRP并恰當地運用LRP來揭示運動相關加工過程以及整個大腦活動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 獲得與出現檢測方法
人們普遍認為,LRP提供了反應準備或反應激活的在線測量方法。但是,由于腦電圖描記器(electroencephalograph,EEG)信號的低信噪比,要準確獲得LRP并確定LRP的出現(onset)很困難[4]。
傳統的LRP獲得方法是采用平均法從EEG信號中提取[1],但是該方法受到EEG信噪比的影響較大,因此,研究者們嘗試采用其它方法來獲得LRP。如果能夠為LRP提供一個single-trial波模型,將有助于獲得更真實的LRP。Mordkoff和 Gianaros[3]采用了single-trial LRP的人工模型(如方波和正玄波),但是他們的主要興趣在于評價記錄LRP出現潛伏期的不同方法,并沒有正式評價模擬的LRP與真實LRP的擬合度。2010年,Stahl等人[5]首次采用 方程進行single-trial的 LRP建模,發現所建模型對刺激鎖時和反應鎖時平均都能產生真實的平均波。該結果或許使得通過trial-by-trial波來提取LRP成為可能。除了用數學方程為single-trial波建模,最近有研究者基于功能數據分析技術來提取LRP[6]。該方法將EEG數據作為功能數據,把每個trial的縱向信息(時間序列數據)與某個固定時間點的所有trials的橫向信息(橫向數據)結合在一起來獲取LRP。結果發現基于功能數據分析的LRP比傳統的基于平均的LRP要更接近真實的LRP,而且在trials減少的情況下更穩健。此外,在不同LRP出現檢測方法中,基于功能數據分析的LRP出現要比基于平均的LRP更精確。
為了準確地檢測LRP的出現,研究者設計了各種方法,其中應用較廣的主要有3類:基于特定標準的方法、基線偏差方法和基于回歸的方法[7]。對于這些方法能否準確地檢測LRP的出現,確定出現標準的計算方法是關鍵。1998年,Miller等人[4]首次檢驗了jackknife-based方法在評估LRP出現潛伏期上的差異。他們發現,盡管該方法在不同被試潛伏期不同時會導致平均LRP出現偏差,但是當所有潛伏期偏差大致相同時,不同條件下的統計比較不受該偏差的影響。研究者認為jackknife-based方法提供了多數實驗條件下LRP出現潛伏期變異的精確評估,可同時用于S-LRP和LRP-R分析。而對各種方法的比較研究表明,基于回歸的方法在分析S-LRP和LRP-R數據時是最準確和可靠的[3]。
2 影響因素
獲得LRP的經典實驗范式是S1-S2-R范式。因此,預備信號的內容及有效性、預備信號與命令信號的時間間隔以及反應特征等都可能是LRP的潛在影響因素。Masaki等人[8]提出,LRP開始于反應手的選擇后和動作編程開始以前。反應選擇階段的參數只影響S-LRP間隔;運動學參數在動作編程階段具體化,對LRP的持續時間和振幅均起作用。
研究表明,預備信號的內容及有效性影響LRP的波幅、出現時間和極性。Ulrich等人探討了預備信號攜帶的信息維度(反應力量和運動方向)對LRP波幅的影響。實驗要求被試用兩種不同水平的力完成一個左手或右手食指的伸屈動作。在命令信號呈現之前給被試提供四種不同的前置線索信息:手、手+動作方向、手+力的大小以及手+方向+力的大小,即動作參數的信息從部分到全部。結果發現,任何部分線索信息均不能提高LRP的波幅,只有在所有線索信息都呈現的情景下LRP波幅才會有明顯的增加。隨后有研究者考察了反應力量和運動方向預備信號對LRP出現時間的影響,發現有預備信號比無預備信號的S-LRP間隔要小得多,但是LRP-R間隔不受反應力量預備信號的影響[9]。此外,預備信號的有效性會影響LRP的極性。當預備信號有效時,LRP顯示出預備階段正確反應的啟動(負波);當預備信號無效時,被試啟動了錯誤反應(正波);在中性條件下,沒有啟動。這些變化說明預備信號的有效性對LRP的極性產生了影響[10]。
1995年,Steven等人探討了預備信號與命令信號的時間間隔對LRP的影響。他們運用go/no-go實驗范式,采取了0ms、100ms、300ms和1400ms四種時間間隔。結果發現,長時間間隔的LRP波幅大于短時間間隔的LRP波幅,而且前者的LRP出現時間比后者早。
關于反應特征對LRP的影響研究主要探討了反應復雜性、速度-準確性要求的影響。復雜運動的LRP波幅比簡單運動的大,時間壓力上升時LRP波幅提高,速度任務比準確性任務有更大的LRP,力量變化速度越大,LRP的波幅也越大[11]。此外,反應的力量變化速度影響LRP的反應潛伏期[8]。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LRP波幅存在一個“Gratton's Rule”,即不管反應速度、準確率、數據窗口以及實驗條件如何,LRP的波幅在外顯反應開始的時刻(肌電出現)是不變的[12]。這種不變性表明中央運動命令只有在兩手的中央激活水平差異達到一定水平或閾限時才會發出。LRP的該特性可被很好地用于區分運動認知加工階段。
3 未來研究展望
LRP作為反應準備或反應激活的一種在線測量方法[1],其效度對研究結果的準確性至關重要。自發現LRP以來的四十多年中,研究者們嘗試了從各個方面來驗證和提高其效度,并獲得了一定的突破。

傳統的LRP提取方法是從EEG信號中采用平均方法獲得[1],因此,LRP不可避免地受到EEG信號低信噪比缺陷的影響。不難發現,提高EEG信號的信噪比能夠提高LRP的效度,但是該方法受到目前科學技術水平和實驗條件的極大限制。在現有的條件下,能否另辟蹊徑,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呢?研究者們嘗試了采用校正EEG信號提取LRP[13]、用Γ方程為single-trial的LRP波建模[5]以及運用基于功能數據分析技術提取LRP[6]。但是,上述三種方法都是新的嘗試,還沒有獲得足夠的效度證據支持。因此,未來研究需要加強此方面的研究,不僅僅是為已有研究提供證據,也需要進一步開發新的更有效的LRP提取方法。
在使用LRP進行研究時,準確檢測LRP的出現是一大難題。目前,對于LRP出現的檢測,主要有基于特定標準的方法、基線偏差方法和基于回歸的方法[7]。面對這些方法,我們如何進行選擇呢?到目前為止,只有一項研究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3]。研究者指出,如果要分析S-LRP數據,采用基于回歸的方法較好;如果要分析LRP-R數據,推薦使用基于回歸的方法結合JK50%的技術;如果要評估刺激或反應鎖時效應的大小,或者需要在單一條件下識別LRP的出現,則使用單被試1DF技術來分析刺激鎖時數據,使用JK1DF技術來分析反應鎖時數據;如果研究者需要所有類型分析的建議,則建議使用單被試1DF技術。盡管該研究為我們的選擇提供了參考,但是對于這些建議的正確性,有待進一步研究的檢驗。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外,對LRP本身特點的驗證和探討無疑有助于提高其有效性。首先,對LRP-R的分析大多是基于LRP波幅的“Gratton's Rule”,即LRP波幅在外顯反應出現時是固定的。盡管大多研究者都支持“Gratton's Rule”,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并非如此[14〗。因此,未來研究需要考慮解決此爭議,為合理地解釋LRP-R數據提供有力地支持。其次,已有研究探討了反應力量和運動方向提示線索、預備信號與命令信號的時間間隔、反應復雜性、速度-準確性要求、反應的力量變化速度等因素對LRP波幅、極性以及潛伏期等方面的影響,但是,研究結論并不統一。因此,未來研究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探討各因素對LRP本身的影響,以期得出更為一致的結論,另一方面需要探討其它可能影響LRP波的因素,例如刺激呈現方式、任務類型等,以獲得對LRP更全面的了解。
總之,當我們對腦電測量與大腦功能的關系更清楚時,我們便能更準確地推斷認知任務中的大腦加工過程。反過來,正如生理心理學家所言的那樣,這對認知神經科學將是一大貢獻。因為心理生理學在心理學和生理學中的位置,它將在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中起到關鍵的作用[1]。而LRP作為一種心理生理學測量方法,為我們深入理解人類大腦和行為的關系開啟了一扇門!因此,我們今后努力的可能方向是,進入這扇門并綜合運用其它科學技術手段和測量方法,進一步揭示人類大腦和行為的奧秘。
[1]Coles M G.Modern mind-brain reading: Psychophysiology, Physiology, and Cognition[J]. Psychophysiology,1989,26(3):251~269.
[2]Brunia C H M,Damcn E J P.Distribution of slow brain potentials related to motor preparation and stimulus anticipation in a time estimation task[J].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1988,69: 234~243.
[3]Mordkoff J T.Gianaros P J.Detecting the onset of the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A comparison of available methods and procedures[J]. Psychophysiology, 2000,37:347~360.
[4]Eimer M.The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as an on-line measure of central response activation processe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1998, 30(1): 146~156.
[5]Stahl J,Gibbons H,Miller J.Modeling single-trial LRP waveforms using gamma functions[J]. Psychophysiology, 2010,47(1):43~56.
[6]Zhao Y B,Tao J,Shi N Z,Zhang M,et al. The extraction of LRP via functional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J]. J Neurosci Methods,2012,206(1):94~101.
[7]陳立翰.單側化準備電位的含義和應用[J].心理科學進展,2008,16(5):712~720.
[8]Masaki H,Wild-Wall N, Sangals J, et al. The functional locus of the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J]. Psychophysiology, 2004,41(2):220~230.
[9]Gethmann H M,Rinkenauer G,Stahl J,et al.Preparation of response force and movement direction: onset effects on the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J]. Psychophysiology,2000, 37:507~514.
[10]Gratton G,Coles M G H,Sirevaag E J,et al.Pre- and post stimulus activation of response channels: A psychophysiolog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1988,14(3):331~344.
[11]Sangals J, Sommer W,Leuthold H. Influences of presentation mode and time pressure on the utilisation of advance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preparation[J]. Acta Psychologica,2002,109(1):1~24.
[12]Mordkoff J T,Grosjean M.The later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and response kinetics in response-time tasks[J]. Psychophysiology,2001, 38:777~789.
[13]Hohlefeld F U,Nikulin V V,Curio G.Visual stimuli evoke rapid activation (120ms) of sensorimotor cortex for overt but not for covert movements[J]. Brain Res,2011,1368:185~195.
Keywords: LRP; cognition; movement preparation; inhibition control; movement imagery
Areviewonlateralizedreadinesspotential
GUO Zhi-ping1,2,LI An-ming1,LI Zheng-zhong2
(1.School of Sport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LRP) refers to negative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which occurs to the cerebral cortex contra-lateral to the response effectors. The crux of LRP analysis is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onset" time and the guarantee of using LRP in appropriate way is to understand its character and affect factors.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are also addressed, and future areas of inquiry are suggested.
2013—10—12
上海體育學院一流學科建設(心理學)開放基金項目(XL2012007)
郭志平(1979— ),湖北恩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運動人體科學.
G804.3
A
1009-2714(2014)03- 0016- 04
10.3969/j.issn.1009-2714.2014.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