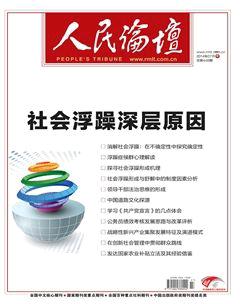陜北黃土地的藝術形象與精神表達
郭鵬 楊雨佳
【摘要】陜北黃土地的藝術形象塑造從一開始就具有象征意義,這一形象是一種糅合了現實歷史元素和紀實性的藝術創造,它的核心元素就是中國革命運動,因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所承載和表達的宏大熱烈的政治品格。繪畫作品中的黃土山梁溝壑、勞動人民、勞動場景等都隱含有深刻的政治傾向,無不是宣揚激昂的民族革命精神,或鼓舞士氣。
【關鍵詞】陜北黃土地 藝術形象 精神表達
【中圖分類號】J2 【文獻標識碼】A
曾幾何時,蒼涼的陜北黃土地成為畫家寫生和藝術創作的基地,陜北的一切都成為他們獲取藝術靈感的源泉。畫家們以一種浪漫的情懷和主流文化的意念創造了一個響徹大江南北的“陜北”與“陜北人”的形象范式。陜北的黃土地、陜北的民俗、陜北人民以及陜北人民的生活都被賦予了深刻的內涵和積極的精神意義。陜北黃土地的藝術形象塑造從一開始就具有象征意義,這一形象是一種糅合了現實歷史元素和紀實性的藝術創造,它的核心元素就是中國革命運動,因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所承載和表達的宏大熱烈的政治品格。繪畫作品中的黃土山梁溝壑、勞動人民、勞動場景等都隱含有深刻的政治傾向,無不是宣揚激昂的民族革命精神,或鼓舞士氣。
黃土地以其質樸、雄渾、蒼涼的自然美形成了黃土地的“精神基質”,以民風的質樸和勞動人民的熱情以及民俗文化的古老、獨特,形成了黃土地特殊的整體文化“意象”,而它們與表現中國的革命精神意象和人民艱苦奮斗建設家園情懷的特殊使命完美結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陜北黃土地的形象范式和情感表達寄托,成為中國繪畫創作歷史的典范。至此,承載紅色革命精神和老黃牛精神,反映陽剛豪放、雄渾大氣、勃勃向上的理想現實主義繪畫風格轟轟烈烈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繪畫趣味與社會政治的互動關系,也就是陜北黃土地成為革命搖籃這一特殊的歷史際遇為陜北黃土地提供了廣闊的歷史展現舞臺和鑄造了崇高的形象地位。在革命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它象征著國家正氣和中華民族的脊梁,展現出民族沸騰的熱情和奔騰的熱血。以它為背景的繪畫作品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思想和題材先行,形式和內容相一致的藝術創作思想指導下,形成了中國的經典革命圣地圖式以及質樸的人民形象典型。誠然,以黃土地作為繪畫表現的對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國革命發展歷史境遇選擇陜北,使得陜北成為紅色搖籃而具有特殊的地位,成為繪畫表現的對象;另一方面,黃土地的“物性”和品質所承載的表現能力正好與其作為革命精神的媒介所需要表達的獨特性相一致,也就是它的地理風貌和人文質地的純粹性正好匹配于革命精神的標準,從而成為畫家關注的對象。從這一點上講,陜北黃土地確實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陜北黃土地地理“物性”是表現革命精神繪畫的最佳載體
某種角度上說,在黃土地生活的人們的處境同革命時期革命志士的處境是十分一致的。二者的生存環境有相當的同質部分,因此也筑成了他們共同的人格品質—在惡劣的環境中艱苦生活,卻意志堅定、斗志昂揚、積極樂觀。革命志士在荒涼的、漫無邊際的黃土溝溝壑中感受到的不是絕望,反而涌現無盡的激昂情緒和博大胸懷,亦有無窮的抗爭力量。這些品質共同筑成了黃土地的精神內涵,而這一內涵正是畫家們要表現的。這種特殊的表現主題是國家特殊的歷史時空境遇需要賦予的—國家抗戰特殊時期為意識統一所進行的思想建設和精神動員。
抗戰時期,國體的凝聚、國魂的召喚、國格的塑造成為美術創作的時代最強音,在大多數人看來,人們需要的美術作品要有力的情緒,有鐵的精神,有慷慨悲嗆的奮發音調,有沖鋒陷陣的戰斗聲勢,只有這樣才能敘述民族過去光榮史跡以激發民族上進的志氣,來描寫國家當前的艱難情狀以激發民族的革命情緒。因而,革命需要成為當時繪畫表達的唯一思想資源。
這種創作的精神歸宿不再是儒家哲學和道家理念本質的,而是對實現民族集體事業的禮贊—國家危難時刻的革命活動和精神的頌揚。這一時期的繪畫作品也確實承載起這一歷史使命,從圖像上完成了中華民族革命精神的構建,為塑造國民堅固的向心力和強大的戰斗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如畫家石魯的作品《轉戰陜北》就是典型。它描繪的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個大氣磅礴的空間,把觀眾帶到了一個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在畫面上,毛澤東立于陜北高原,憑高遠視,指揮若定,雖不見千軍萬馬,但似千軍萬馬隱藏于大山大壑間。近景山體巍峨雄壯,用了紀念碑式的構圖方式,再加上筆墨凝練厚重,給人以高邁偉大之感,充分塑造出毛澤東高韜遠略的偉人形象,亦顯現出偉大的中國氣魄。在新時期的繪畫作品中,陜北黃土地的蒼涼、空闊、雄渾都被轉化為人格化了的蒼勁剛毅、氣魄雄健、豪放灑脫、積極樂觀的民族精神品質,發揮出強大的正能量,讓觀者強烈感受到一個處于苦難中的民族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生存能量。
陜北黃土地人民品質是表現新中國群眾精神繪畫的最好代表
新中國建立后,轟轟烈烈的建設運動又將陜北黃土地推向作為繪畫對象的高峰。新政權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也是為人民服務的,藝術亦然。人民需要表現人民和人民生活以及新時代人民精神風貌的藝術。在這種歷史社會背景下,傳統文人畫、宮廷畫等題材受到社會的批判而被萎縮,而描寫廣大群眾勞動、豐收、國家建設的題材卻成為主流,也產生了諸如畫“白菜”的齊白石,畫陜北農民的劉文西等人民藝術家。這一時期的人民大眾在生活上是比較艱苦的,但是在精神上卻是積極樂觀、干勁十足、滿懷希望的。不論是在農家庭院里,廣闊的田野里,還是在繁忙的工廠地,到處都煥發著新中國社會特有的“精神氣質”,處處呈現著熱烈的氣氛、喜悅的心情,以及激烈勞動場面和累累碩果。這一切都讓畫家十分感動和震撼,他們紛紛投入到表現這類題材的創作活動中。而基于這一使命,陜北黃土地亦顯露出它的特殊性來,成為畫家們表現的對象。
陜北勞動人民純樸、勤勞、熱情、樂觀的品質正是新中國全體勞動人民在建設新家園這一時刻所體現出的品質,陜北勞動人民的精神風貌成為全國勞動人民精神風貌的寫照和代表,加之陜北在革命過程中的地位以及中國人民對陜北的特殊情感,使得它再次出現在表現新中國新建設和社會風貌繪畫舞臺的前沿。當時傅抱石、黎雄才、錢松、李可染等知名畫家都曾來陜北黃土地體驗生活和創作以黃土地為主題的繪畫,留下了一批經典的畫作。而以黃土地為創作對象最為典型畫家則是劉文西。劉文西從陜北的黃土地中發現了自己的繪畫創作內容,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歸宿。他在這片熱土中挖掘到了的極其豐富的人民生活、生產素材,獲取了綿綿不斷的藝術創作靈感。他的《祖孫四代》、《溝里人》、《黃土情》、《虎娃》以及《毛主席與牧羊人》等表現黃土地和黃土地上的生靈的作品,奠定了他一生的創作道路和藝術成就,且將宣揚黃土地精神的“運動”推向高峰。
劉文西無疑是秉承毛澤東《講話》精神且最忠實的踐行者,在他的旗幟影響下,70~80年代中國的西部出現了一支活躍在黃土地的山山水水和溝溝壑壑的畫家群體—黃土畫派。他們以黃土文化為背景,以黃土為基地,以黃土地以及黃土地上生活的勞動者為藝術對象,以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表現、贊美、謳歌這塊黃土地以及生活在這塊黃土地上的生靈。黃土畫派的畫家們踏著前人的足跡,延續以積極的現實主義色彩和革命浪漫主義詩情,表現中華民族艱苦卓絕、救亡圖存的史實以及人民和領袖同甘共苦、戰勝苦難創造的歷史奇跡的作品之余,更多地利用手中之筆為黃土地的崛起和黃土地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黃土地豐厚的人文風情而揮灑激情。這種繪就黃土地,歌頌勤勞質樸的勞動人民以及燦爛民族歷史文化繪畫主題,更加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民族文化意志,大大擴展了傳統黃土地精神的內涵和外延,也極大地豐富了表現黃土地精神的繪畫題材和意象。在一思潮下,繪畫作品更多關注于時代,題材更多地來源于人民日常生活,并呈現出最為積極、感人、鼓舞人心的一面,也由此誕生了楊曉陽、王有政、王勝利等新生代畫家以及《黃河的歌》、《悄悄話》、《延安新市場》等優秀繪畫作品,這些畫家和作品成為增補中國藝術史極為重要的內容。
陜北黃土地題材繪畫的藝術特色
“陜北黃土地”和“陜北人民”繪畫范式的藝術創造,使得黃土地成為中國繪畫中一個永恒的藝術圖騰,它不僅深深影響了20世紀后的一批批畫家,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中國繪畫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審美走向。對山川和人民的表現體現出符合政治的需要,繪畫作品做到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畫家們以深刻的主題思想和崇高的志趣,提煉出概括性的藝術形象,使語言藝術與題材達到完美結合。從一般山水和人物向特定山水和人物,即“革命圣地山水”和“勞動大眾”轉移,表現出一種與革命圣地相吻合的莊嚴、崇高的鮮明風格和反映國家新的主人—人民大眾的堅強、純樸、樂觀、勤勞的高貴品質。畫家的筆墨游離于浪漫與真實之間,以宏大的空間、熱烈的色彩、粗狂的筆觸和象征性的人物形象等元素塑造出極具視覺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的繪畫作品。這種特定意境以及新時代內容使得繪畫形式實現了視覺語言、文化結構、審美趣味與時代題材的有機融合,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和象征,成了一個民族永遠抹不去的文化寫意符號以及繪畫史上璀璨的明珠。
(作者單位:陜西省榆林市榆林學院藝術學院;本文系2012年榆林市科技局產學研合作項目成果之一)
責編/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