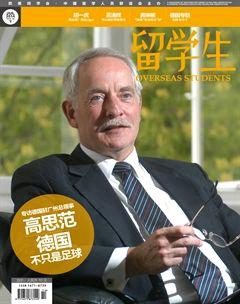專訪胡一虎:我是誰?我是tiger胡一虎
張曉雅
胡一虎,鳳凰衛視主持人。以他名字打造的《一虎一席談》以其獨特風格獨樹一幟,節目選取每周在社會、文化等方面發生的重大事件、焦點或熱門話題,請來當事人、各界學者、名人擔任嘉賓發表意見或精辟見解
幾年前我與胡一虎曾有過一面之緣。當時我為香港書展某位作家做助理,胡一虎則是那場作家講座的主持人,講座開始之前,我要交給他一些資料。在約定的會場里,我等在一條走廊盡頭,此時胡一虎戴著墨鏡出現了,從走廊另一頭的黑暗處慢慢走過來,步伐很穩,那一瞬間像極了黑幫電影里的鏡頭,他顯得很酷,好似大有來頭。
及至幾周前我作為《留學生》記者打電話向他約采訪,聽到的仍然是那個非常有活力的聲音,簡直聲如洪鐘。這聲音透著臺灣人特有的禮貌與謙和,他答應了采訪,并解釋自己需要定期在北京與香港之間飛來飛去,見縫插針的面訪都稍有困難,因此選擇了電話采訪。
對于胡一虎40年的經歷,我們可以這樣概括:在臺灣長大,在美國念書,在香港的電視臺工作,卻做著關于大陸的節目。而在胡一虎自己撰寫的自傳中寫道:我是一名在高雄出生的孩子,平民之子,文科胚子,教養與情義兼修;我是一名從紐約出發的戰士,不與人同,保持激情,打人性牌,做實力派。
胡一虎1967年生于臺灣高雄眷村,1989年畢業于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兩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華視新聞。在華視,他最重要的經歷是與崔慈芬及莊開文輪流主持《華視新聞雜志》,而因其出色的表現,獲得了華視100萬元新臺幣的撥款,得以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進修。
2001年,從美國歸國的胡一虎做出了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個決定:離開華視,加盟鳳凰臺。關于這點,他說:“如果沒有飛入鳳凰,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能如此幸運與豐富。如果沒有離開臺灣到香港,我不會有今天的思維與說話方式。”
在加入鳳凰衛視后,胡一虎先后主持《媒體大拼盤》、《縱橫中國》、《鳳凰全球連線》等節目。他認為,主持《縱橫中國》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正是這個節目,讓他得以行遍中國的各省各市與自治區,“飄蕩在華人世界的不同角落,對中國有了全新的認識”。
然而,真正讓胡一虎這個名字著名的是《一虎一席談》——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周末黃金檔節目。
而在這個節目中,胡一虎幾乎展現了所有他作為一個主持人的特點:機敏、博識、反應迅疾、把控力強。每一期節目現場都顯得很緊張,甚至劍拔弩張,選題尖銳,嘉賓間針鋒相對,辯論激烈,“唇槍舌劍之間你不知道會激出怎樣的火花甚至火焰”。
《留學生》記者在采訪中問胡一虎:“tiger,你覺得主持《一虎一席談》最難的一點是什么?”他這樣回答:“把握節目的節奏。主持這個節目的每一秒,我都繃緊了全身的神經,不敢絲毫的大意與放松。”這一點,他確實做到了,并充分地展現了一個更為真實的胡一虎。如他自己所說:“我比主持其他節目更為接近‘本我的狀態。”毫無疑問,觀眾們喜歡那個更為真實的主持。
胡一虎用了一個很別致的詞來形容他與節目的關系——“甜蜜點”。記者初聽時覺得太過臺灣人的小清新了,但在與他交談的過程中,發現他對工作有自內而外,深沉的熱情,他才能在工作中捕捉“甜蜜點”。
開播9年來,這個節目在國內幾乎無人不知,連續5年都是鳳凰臺收視率前5名,并獲得了盡可能的好評與贊許。國內一份著名刊物曾在對《一虎一席談》的頒獎詞里這樣評價:它首度將選秀的PK精神和板磚引入電視節目,演繹問題的多重視角,并展現社會多元的現實圖景。
而生活中的胡一虎呢?
胡一虎說他喜歡慢跑,尤其喜歡看海。但是他說:“我太忙了,沒太多時間做這么奢侈的事。”事實上,由于要錄制多檔節目,他必須在香港與北京之間穿梭。事業上的忙碌,胡一虎甚至對于家庭有一定的愧疚感。他在自己的自傳中寫道:為人子,無暇與父親共同走過他生命中的最后歲月;為人父,女兒一出生我就離開臺灣,幾乎錯失她的成長……很多時候,我從主播臺上回歸現實生活,都發現拼湊不齊自己完整的人生版圖。
當然,如他所說,人生總有得失,不甚完整。
對于未來,胡一虎卻用了臺灣人特有的,帶有一定詩意的回答:命運的走向是全無章法的,我不知道未來如何,我們只能盡全力地做好自己,“謹守分寸,Be yourself”。
尋找“甜蜜點”
留學生:最開始你對內地的事務并不是那么熟悉。為什么有膽量做這樣一檔與內地事務息息相關的節目?
胡一虎: 2003年到2005年我做了鳳凰中國,三年內走遍中國各個地方,為我對內地了解打了很好的底色。現在做《一虎一席談》,現場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師。節目中我會尋找“甜蜜點”,讓我特別感動的是武村正義,這個前官房長官他說了一句話,就是說至少在他那個年代那個歷史,他說安倍,他的確有很多看法跟安倍是不一樣的。他說不能只看一個人對歷史不道歉,其實日本的老百姓也在反思。然后這個時候我記得有一個將軍跳出來了,那個將軍正好跟武村正義是一樣大,下個禮拜的,一時忘記了。他就講說在他的腦海里記憶,日本人是怎么樣對待我們中國,就講,講講講。他講完我記得我那時候也是馬上想到奇怪了,我就跟武村正義說:官房長官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現在全場當中這么多人只有他的年歲跟你一樣大,他所記憶的歷史跟你所記憶的歷史是共同那個時代的東西,但是你們有不同角度的記憶,而我們這些后輩根本不知道,沒有參與那些情況。我就問他說:那你覺得這個差別點是在哪里,你會不會希望中國下一代的記憶跟它是不一樣的。這些東西就是在,我覺得做這些話題是很沉重的國際議題的時候,我一直努力去找那種,你剛才講的你的平衡點在哪里,平衡點就是連接點,平衡點就是將心比心的那一點,平衡點就是設身處地的那一點。
留學生:你主持的這檔節目大多數時候與內地話題相關,怎樣才能去平衡各方不同觀點?為什么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來處理這些問題呢?
胡一虎:我家里的背景就是沖突性比較大,我父親從大陸到臺灣,母親是閩南人,本身就有沖突點,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了解到適應沖突就像適應一個陌生的地方,到一座新的城市適應它的文化。我覺得需要幾個本領,第一就是百變的適應力,這是在生活中磨礪出來的;第二就是將心比心。比如說既要體會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帶來的震撼,也要習慣這座城市百年來積淀的塵埃,才能真正對這座城市心生崇敬。在不同文化轉換的過程中,這點幫助我非常多,因為《一虎一席談》這檔節目里沖突太多,文化背景差異太大。讓對方闡釋背后的東西,這很重要。因為我們之所以看不起,或看不慣對方的語言表達,往往是不懂他身處的文化語境積淀出來的東西,而這個平臺就是去搭臺。
留學生:你的性格里面有容易質疑的部分嗎?
胡一虎:很多上節目的觀眾事后會被大家罵:“那種觀眾怎么也讓他講。”我覺得這是誤讀,因為通過對熱門話題的充分討論,會看到眾生相的縮影。過去很多嘉賓會說如果有觀眾我就不參加。他可能覺得觀眾跟他身處不同層次,對事實上理解會不同。可是我們一直在強調有話大家談。那“大家”指的是社會各個不同利益團體的縮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一虎一席談》中很強調這點,這里面有精英知識分子的觀點,也有草根最樸素的表達。你可以責怪草根講某些沒道理的話,但別忘了他的情緒背后的原因。讓最基層的人能夠跟知識精英對接,其實我們就在打造這個平臺,它是一定有沖突的。在沖突當中你怎么去強調,怎么去起承轉合,這也是我喜歡的原因。
留學生:《一虎一席談》開播有9年,會不會感到疲憊?
胡一虎:我的狀態還一直保持著,怎么看我的狀態呢?看我的說話速度就知道了。我做這檔節目永遠像是在坐過山車,你根本不知道誰會冒出什么話,感覺很爽,但也很傷。談話性節目最重要的是擲地有聲,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內地對一個事件的看法,想了解為什么北京人口才這么好,看這一檔節目就學到了。觀眾卻是讓我感覺很傷的部分,這檔節目實際上每次大概錄80分鐘,中間沒有停頓,我需要全神貫注控場,高度關注觀眾的反應,因為你不知道觀眾會冒出什么火花,每次主持完就會掉很多頭發。一次討論“廢除偽科學”時,臺下有清華和北大的學生,但居然因激烈言辭顯些變成武斗。另外甚至還有重量級的外國嘉賓自費來到現場,近期就有原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武村正義先生。
留學生:自費來參加節目的嘉賓有很多嗎?
胡一虎:有關烏克蘭事件的節目,我們請到烏克蘭公使、俄羅斯人,還有美國人都來到現場,這樣的組合就會有不一樣的聲音。我們請更貼近核心利益的人很難得,因為經費根本就不夠,鳳凰是有名的沒錢。很有趣的是,俄羅斯公使還有秘書幫忙開車來,烏克蘭公使自己開車來,開到一半的時候還出車禍,我們致歉,但他說沒有關系,至少他把聲音發出來了。
留學生:雖然真理是越辯越明,但也有上過節目的嘉賓曾說激發辯論是電視臺追求收視率的做法。你怎么看?如何平衡?
胡一虎:PK本身就富有戲劇性,初來乍到希望用戲劇性強一點來做沖突,早期的確會有遺憾,強調收視率,這個我們該檢討,這幾年也在修正。早期有的嘉賓會習慣扮演某個角色,我會打斷他,告訴他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捍衛這個觀點跟價值。我們發現很多議題根本不存在天然對立,反而是透過PK的形式慢慢延伸出不同角度,它提供看問題的多元角度。
收視率?收思率!
留學生:《一虎一席談》這些年的收視率怎樣?
胡一虎:這檔節目開播9年到現在,收視率一直是鳳凰的前5位。非常幸運的是擁有這個團隊,我們默契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幕前跟幕后我們都有共同點。鳳凰不是拿廣告費來支付節目經費,我們人少錢也少,在這樣的環境下,能不能壯大自己的品牌是需要考慮的。我的團隊里有拼命三郎和拼命三娘,每一個都可以是all in one。如果沒有這個團隊,說實話我也不會做這么久。
留學生:除了收視率之外,什么是你希望影響公眾的?
胡一虎:任何一檔節目能夠長久持續的原因都不是收視率,而是收思率。我每次看完節目后會總結,哪幾段內容刺激了我的思考。電視版《一虎一席談》是第一個階段,它更大的影響力是在網絡上炸成鍋,其他人的持續辯論。社會在不斷思考,尤其公共議題就會更有價值。有時節目又會演變為一堂文化課、美學課。也有人會反應說為什么我們要用惡毒的話來攻擊,外國嘉賓講話又為什么彬彬有禮。謙恭的態度也是一種學習。
留學生:審選題是怎樣的節奏?
胡一虎:我每隔一周飛一次北京,一周之后再回香港。人在香港就做《鳳凰全球連線》,在這期間,團隊在北京開會碰題目,往往是一飛過去全都推翻了,有時是嘉賓找不到,或者沒有更好的組合,只能撤換。更多是新聞熱度的突然轉變,或者是選題沒有新的火花就寧愿不要,這樣做很冒險,甚至有時前一天晚上才找嘉賓。
留學生:選取話題最注重哪些方面?
胡一虎:以前坦白講,選話題就是熱度,但熱度其實沒有這么簡單,因為人人都能做。如果來總結選擇話題的組合,第一叫滾燙的水,最熱的話題一定要選。像朝鮮局勢經常是突然爆發,那就把其他國際話題通通拿掉,嘉賓通通撤掉。第二種叫炒冷飯,文化議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比如京劇該不該走進課堂?我記得當期收視率好得不得了,意料之外。所以那時外界說內地不重視中華文化,簡直是鬼扯的,看收視率就知道。怎么重新喚醒內心對文化的眷戀,重新包裝,重新來談,這些東西潤物于無聲。
留學生:作為《一虎一席談》這類論爭類節目的主持人,你希望達到什么目的?
胡一虎:一個節目最重要不僅是它所傳達的訊息,而是它的態度。好多人希望從我嘴里聽出來,我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大部分人習慣主持人這樣。我做新聞至今,認為節目主持人不能這樣。我每次的結論傾向于什么,其實可以聽得出弦外之意,促使大家都體會正反方背后的思考,這才是我的目的。其實我曾經快要動搖了,最明顯就是“范跑跑”那一集。我當然有我的立場,但我絕對不能在這個平臺上說,我這么一說了之后,因為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了嘛。
留學生:節目中嘉賓會進行激烈辯論,你怎么掌握“度”的問題?這是否很重要?
胡一虎:是的。這里頭“度”的把握最痛苦,比如專家與場下觀眾PK時,兩人的知識層次或許不在同一個平臺,你要讓場下觀眾尊重專家表達的完整,讓專家包容場下的無的放矢。讓大家放下預存立場,放下偏見,來聽聽看。還有一次任志強一個人足足講了十幾分鐘,我必須要打斷他,當時他剛從美國飛回來,直接來到節目現場,如果生硬打斷,他可能掉頭就走,任志強問“你干嘛打斷我,那請我過來干嘛。”當時有點尷尬,那我就說“任大炮,體諒你剛從美國回北京,我讓你先喘口氣。”然后立刻問與他PK人的意見。“度”的把握有時是時間的掌握。電視是永不完美的,受限于時間空間,受限于手上腳上所戴的東西,還受限于嘉賓,很多元素觀眾沒辦法體會,但沒有關系,有心人會體會到,無心的人慢慢解釋就好。
留學生:印象最深刻的嘉賓有哪些?
胡一虎:坦白講這里有幾個嘉賓非常優秀,比如羅援將軍他的強硬態度、語言能力、對歷史的嫻熟度,以及對數據的掌握;你可以不欣賞任志強說話的高聲,“大炮”的氣勢,但你永遠沒法反駁他在節目中帶來的完整邏輯;你可能討厭范跑跑在最關鍵的時刻說了不該說的話,但是他所表達出來的真實也讓你反思。我所有的結束語幾乎都是現場編出來,因為我必須要聽到嘉賓的表達。所以我之前說過山車的快感也就在這兒。假設我們的節目是錄制的話,我也許會松懈,說錯重新再來,但我們一直都是現場。
游刃有余?NO,要保持緊張
留學生:近幾年有沒有受到自媒體、新媒體和網絡媒體的沖擊呢?
胡一虎:坦白講是勢必的。但我一直覺得不管是自媒體也好,傳統媒體也罷,我堅信“內容為王,形式為后”。這兩者都要兼顧,到哪里去看都是看內容,形式上,我們怎么在技術上與新媒體結合,那是最好的。我也希望能夠走出去,但是要有先決條件。
留學生:你如何看待新聞記者到底應該是專,還是應該是萬精油。
胡一虎:現在新聞學都強調輔系,能夠彌補知識結構。傳統新聞系的優勢越來越少,在哥倫比亞大學游學三個月對我影響很大,你要學完政治、經濟、科學,人文。我個人覺得實踐才是真道理,永遠是實踐才是真道理。
留學生:你現在做得到游刃有余嗎?
胡一虎:這個平臺讓我知道當一個藝術家是不容易的事。它讓你發現新聞是一門藝術。我做到現在也一直沒有辦法做到游刃有余。如果游刃有余,我就不會永遠保持著緊張。因為緊張,我就會見證恐懼,我才會做準備。我希望保持這樣的狀態。一到游刃有余的時候,我就要開始做退休的打算了。
留學生:與團隊合作最重要的一點是什么?
胡一虎:這個團隊就是信任和默契。剛開始我會問剪輯師為什么把我的話都剪了,他們會回答說“你的話最多”。后來慢慢意識到,我的話多不多根本一點都不重要,重點是嘉賓能充分地說出在其他頻道不會說的話,而且是他的真心話,還有你激出了他跟其他人的碰撞。
留學生:作為一名主持人,你如何去看待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胡一虎:永遠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誰。做新聞已經花了你太多時間,如果私生活不再過得平淡一點,工作是不會做好的。
留學生:一檔節目總會經歷高低起落,你的節目有沒有采取一些新的發展模式?
胡一虎:有新的發展模式,我就要拜托首先換布景,但現在經費不夠。另外想換新的棚,但鳳凰國際大樓望眼欲穿還沒蓋好,聽說明年可以進駐,希望有嶄新的形象。電視節目要讓觀眾思考之際,至少要讓人家賞心悅目。我印象中人家批評《一虎一席談》最多的就是說布景像鄉村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