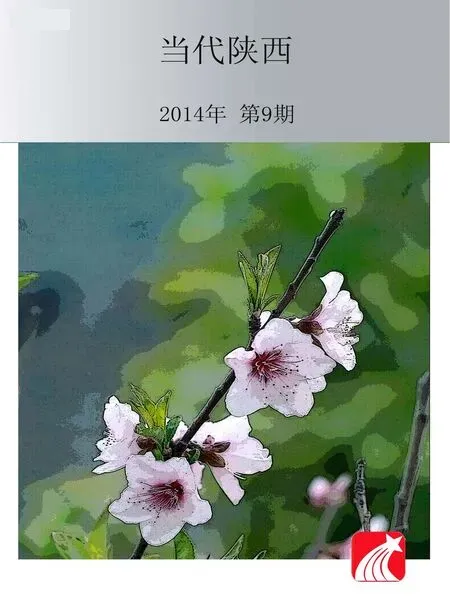羅蒙:情牽“天邊的阿里”
文/梁芝芳 周 明(本刊記者)
羅蒙:情牽“天邊的阿里”
文/梁芝芳 周 明(本刊記者)
在阿里援藏回到漢中一年多了,羅蒙仍保留著在阿里的手機號,每天與在阿里的“學生們”通電話;向別人介紹阿里的時候,會習慣性地脫口而出“我們阿里”……
8月25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全國對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電視電話會議上,個頭不高、說話靦腆的漢中市人民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羅蒙受到表彰。作為陜西省第六批援藏干部,羅蒙是我省2名受到表彰的全國援藏先進個人之一;他也是全國6名受到表彰的援藏技術干部之一。
去北京之前,羅蒙又一次遞交了調往西藏工作申請,他希望能夠再回到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地方——阿里。那里,有他的“學生們”在殷殷地等待,也有藏族同胞的熱切期盼……
打著手電筒搶救生命
2010年7月,羅蒙主動請纓援藏。
晚上值夜班時,他給父親打了個電話:“別人都可以去援藏,我應該也沒什么問題。”電話那頭,身為老產科醫生的父親沉寂了片刻說:“去吧,我們不拖你后腿。”妻子也寬慰他:“放心,我會照顧好咱們這個家的。”
初到阿里,嚴重的高原反應一度讓羅蒙產生了恐懼心理:“會不會出現肺水腫?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盡管之前有心理準備,但當羅蒙走進阿里地區人民醫院時,仍然讓他瞠目:細數醫院婦產科的家底,5名醫生中3人沒有行醫執照;整個婦產科室,沒有一名助產士。
羅蒙還聽說,由于電壓不穩,手術中時常停電,被當地醫生形象地稱為“鬼吹燈”。不過這種情況大多發生在晚上,上午停電的幾率不大。
上班第一天,羅蒙的第一例剖宮產手術就遭遇了這個“小概率事件”。手術進行到一半,嬰兒的臍帶剛剛剪斷,突然停電,手術室一片漆黑,羅蒙只好靠著手電筒和手機發出的微弱亮光,剝離胎盤、縫合……在內地只需30多分鐘的手術,卻出動了婦產科所有的醫護人員,持續了近兩個小時。
由于能源等問題,年均氣溫零下2℃的阿里地區,建筑內沒有供暖設施。冬天從頭年9月一直延續到第二年5月,最低氣溫達零下38度。在那些長風呼嘯、暴雪紛飛的夜里,羅蒙裹著厚厚的軍大衣鉆進被窩還常常被凍醒。顧不上做飯,羅蒙一次蒸一大鍋米飯,之后就著榨菜吃好幾天。
與生活上的困難相比,艱苦的工作環境更讓羅蒙印象深刻:醫院總共25張床位,沒有專用被褥,住院病人只能自帶。病人及家屬基本都是舉家搬遷到病房,有的帶煤氣灶和鍋碗瓢盆,有的帶來干牛糞在醫院準備的藏式灶臺上料理一日三餐(醫院沒有食堂)。
這樣的條件下,治療方案只能“將就”著來。給病人開藥,也只能開最便宜最基礎的藥——當然,首先還得考慮醫院是不是有這種藥品。
“上了手術臺,才知道手術器械跟陜西沒法比,落后的不是幾年。”羅蒙說,好比開慣了飛機,忽然讓你開一輛破舊的拖拉機,哪里都不順手,特別“擰巴”。不具備全麻技術、沒有機械吻合器,只能人工縫合。在內地很簡單的手術,在阿里常常要做好幾個小時。有時,羅蒙從黃昏一直站到凌晨兩三點,做完手術,渾身像散了架一樣,癱倒在椅子上,半晌起不來。
“無奈,我只能用這兩個字來概括。”羅蒙在日志里如此嘆息,可生活在這里的藏族同胞以頑強的生命力與惡劣的環境和死神在執著地抗爭。
“在高原上創造生命奇跡”
“援藏干部可能缺氧,但絕不缺乏戰勝困難的決心和勇氣,我們要在高原上創造生命的奇跡。”他在QQ日志中對未來心懷憧憬:“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每個人必須腳踏實地地干好分內的每一件事,相信一批批一代代做下去,時間會改變這一切。”
一次,在救治改則縣一名子宮破裂的產婦時,患者腹腔大量積血,處于休克狀態,急需輸血。但阿里地區沒有血庫,緊急調血已經來不及。眼看死亡一步步逼近,羅蒙顧不上手術疲勞和高原反應,果斷獻出了400毫升血液。
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這樣的獻血量無異于在“跟死神叫板”,可羅蒙沒時間多想,立刻又投入緊張的搶救工作中。直到產婦脫離危險,羅蒙已累得說不出話了。
沒有助產師,婦產科大夫還要兼助產師的工作。“一臺手術三個人,有時從上午10點鐘忙到晚上10點,樓上樓下地跑。”一次,羅蒙因跑得太急,喘不上氣,臉憋成了醬紫色,護士趕緊拿過病人的氧氣袋讓他吸了幾口,這才緩過勁兒來。
羅蒙剛到醫院時,當地醫生做接生手術從沒用過產鉗,這增大了嬰兒的死亡概率。后來,羅蒙在醫院倉庫找到了大量產鉗。“全是新的,還有很多先進設備沒拆封放在那里,我真覺得可惜。”羅蒙說,“各方的援助很多,我們不缺先進設備,而是缺懂技術的人員”。
為了幫助當地醫生提高職業技能,羅蒙從日常的病歷書寫、查體到手術基本操作,手把手地教,定期組織人員培訓……
當時婦產科惟一一臺比較先進的設備就是腹腔鏡,但閑置多年,是羅蒙完成了這臺設備的組裝和調試。2012年6月,地區醫院婦產科首次成功開展了腹腔鏡微創手術,填補了阿里地區醫療技術上的空白。“現在婦科一般卵巢腫瘤、子宮肌瘤、宮外孕都可以做微創手術了。”

羅蒙(左一)在為病人手術
羅蒙還幫助地區醫院建立起自己的產科手術團隊:一個麻醉師,兩個主刀醫生,還有兩名護士。在一例例手術鍛煉下,他們學到了技術,也建立起了信心。“我離開阿里時,醫院的藏族醫生基本都能承擔普通的手術了。”這讓他倍感欣慰。
羅蒙說,阿里地處偏遠、條件艱苦、缺醫少藥,每一次生病對患者來說幾乎都是生死考驗。但令他感到無奈的是,由于缺乏醫療常識,很多藏族同胞對疾病不夠重視。
入藏不久,有位患有絨癌的藏民來醫院看病,由于地區醫院不具備化療的條件,羅蒙建議她去拉薩做化療,可以治愈。但病人并沒在意,等到全身大出血家人才把她送到醫院。“失血過多,人薄得就像一張紙。”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羅蒙自責不已:“要是能早點治療,人也不至于死啊!”
后來,羅蒙每次下鄉都會為牧民建健康檔案,定期回訪,給他們免費義診。“他們看病太辛苦了,要走上百公里。”到結束援藏工作的時候,羅蒙已經為當地群眾建了上千份健康檔案。
“我的心在阿里”
2013年7月,援藏工作結束將要離開之際,羅蒙站在自己住過的阿里地區醫院宿舍環顧了一圈,房間里的東西仍舊像往常一樣擺放著,“我一定要再回到這里。”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臨離開阿里前,羅蒙一連寫了9封援藏申請書,希望能夠爭得西藏和陜西兩地組織上的同意,讓自己再干一屆,或者永遠留在那個“天邊的阿里”。
“在阿里,幾乎沒有醫患糾紛。”藏族醫生告訴羅蒙,在藏民心中,醫生的地位僅次于“神”。這種淳樸的信任,讓羅蒙感動。
羅蒙永遠忘不了那位78歲的藏族老阿媽。一次,醫院送來一個身患卵巢囊腫的藏族老人,老人肚子脹得很大,好幾天吃不下飯。羅蒙不忍心看老人“受罪”,開了足量的鎮痛劑,但老人依然疼得在床上直打滾。手術指征非常明顯,羅蒙提出了手術方案,可老人害怕“下不了手術臺”,不愿手術。
“這只是個小手術,風險不大,但再拖下去可就危險了。”羅蒙找到老人的女兒耐心勸說,向她詳細解釋手術流程,一一排查可能出現的問題。當天下午,家屬簽字同意手術。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老人很快康復。出院時,老阿媽拉著羅蒙的手一下跪在他面前,老淚縱橫,不停地用生硬的漢語說著“謝謝!謝謝!”羅蒙也含滿眼淚。那一刻,他覺得“實現了作為醫生的價值”。
阿里百姓說,羅蒙是個好醫生。羅蒙說,是阿里讓我們心靈受到洗禮,每一個生命奇跡都是八方支援共同創造的。
在內地,剖宮產手術一般使用人體可吸收的縫線,以免去拆線的麻煩和病人的痛苦,而阿里用的還是以前生產的羊腸線,很硬,每次使用前都要先用熱水泡,還容易斷。羅蒙打電話向漢中人民醫院“訴苦”,醫院很快寄來了專門的縫線。就是在這種八方支援的“輸血”傳遞中,生命之花才能綻放。
出生在醫學世家的羅蒙,從小看到父母的辛勞,“原本不打算從事這一行”,最終“每天都能看到新的生命”讓他一改初衷。如今,這種成就感在阿里被放大了。
援藏三年,羅蒙先后搶救急危重癥患者30多人,門診患者2000多例,開展各類手術800多例,成功接生嬰兒700多名。
每每看到產婦懷抱著粉嫩的嬰兒,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場景,羅蒙常常忍不住落淚:“我沒盡到一個做父親、兒子和丈夫的責任,虧欠家人太多。”母親過生日,羅蒙托妻子訂了一個大蛋糕,在電話里祝壽:“媽,我愛你!”一說完,電話兩頭都哭了。這么“難為情”的話,41歲的羅蒙還是第一次對母親說。
回到漢中后,羅蒙不管多忙,每天都要抽出時間,陪父母“嘮一嘮”、幫妻子分擔家務、給兒子輔導功課,彌補那份“虧欠”。
從西藏回來,羅蒙沒帶冬蟲夏草、藏紅花,卻帶了50多條哈達,他用這些哈達當枕芯,給父母做了一對新枕頭——按照藏族的風俗,這代表著吉祥安康。
“我的心在阿里!”盡管援藏結束已一年多,羅蒙依然時常想起藏民們期盼的目光,使命感油然而生:“他們太需要我了。”
羅蒙仍然保留著在阿里的手機號,幾乎每天都要跟阿里的“學生們”通電話,“遙控”指導次仁白珍做手術,給央吉寄去執業醫師考試的復習資料;向別人介紹阿里的時候,他會習慣性地脫口而出“我們阿里”……
“老師,您什么時候回來?”采訪結束時,尼瑪桑木從阿里打來電話,告訴羅蒙,經他搶救治療的卓瑪大姐又給他送來自家做的酸奶,經他獻血治療出院的次仁德吉剛剛分娩了一個健康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