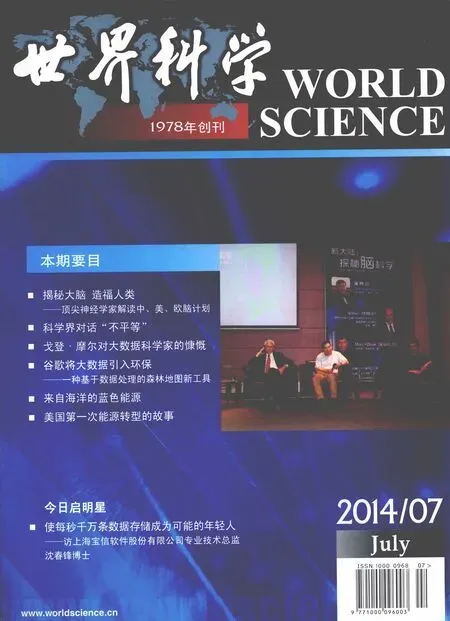語言:迷失在轉換中
葛利云/編譯

吉娜·庫珀伯格(右)通過記錄閱讀時的大腦活動來研究病人的語言過程
●揭示精神分裂癥語言功能障礙的奧秘可為探討疾病本質提供線索。
人們知道瑞士精神病學家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可能是源自一個多世紀前他提出了“精神分裂癥”這個術語。同時,他也為理解語言紊亂為特征的精神分裂癥鋪平了道路。患者的某些表述一直以來被當作典型精神分裂癥語言功能障礙類型的經典案例記載在醫學文獻中。其中兩種來自患者的表述在數十年后依然存在反響。第一種表述出現在布魯勒191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
“我一直很喜歡地理,我以前的專業老師是奧古斯特·艾(August A)教授。他是位擁有黑色眼睛的男士。我也喜歡黑眼睛。還喜歡藍色、灰色和其他各種顏色的眼睛,我曾聽說蛇的眼睛是綠色的。所有人都有眼睛。”
第二個案例來自南希·C·安德森(Nancy C.Andreasen)在1986年發表的關于“當前政治問題,如能源危機”的論文中:
“他們正在破壞過多的牛和油,僅僅為了制作肥皂。當你跳進一池水時,是否會需要肥皂;然后當你去購買汽油時,人們又總是會去想他們應該有所選擇。但他們最想得到的還是機油和錢。”
在第一種表述中,布魯勒的患者演示了“說話跑題”,即說話時失去重點并偏離話題——在這類情形中患者在講話時是突然被更有趣的眼睛主題給攪亂。安德森則展示出一種更加深層的跑題:盡管在有提示的情況下,他仍然不能進行一段讓人理解的演說,反而將一些看似有聯系但實際毫無意義的詞句堆砌在一起。
這兩種令人費解的語句正是思維紊亂的臨床表現,并一再地激發歷代研究者去探究如何更好理解語言在精神分裂癥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因為它們總是以獨特和引人注目的形式存在,所以它們能體現出語言和思維交織在一起的奧秘。
加拿大蒙特利爾市麥吉爾大學著名神經學家黛布拉·蒂托內(Debra Titone)說道:“語言就像心靈的窗戶。”經過數十年的研究,人們已經相當了解正常語言功能的規則和機制。我們不是無所不知的,但我們充分懂得并開發出充足的研究工具,如通過觀察人類正常大腦如何選擇和安排一些詞語形成句子使其變得有意義,從而來跟蹤語言的流露方式。
很多研究者與蒂托內一樣借助語言來研究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大腦和紊亂的思維。他們的目標是鑒定和推斷精神分裂癥的語言功能紊亂產生的潛在原因,并幫助辨明導致嚴重精神疾病的神經學原理。對病人來說,這項研究最終可為他們帶來以下希望:如早期診斷、更好的治療方案以及針對特定大腦功能和認知行為的介入式治療,最后使患者的語言能力和生活質量得以改善。
蒂托內和其他專注于伴有心理疾病的語言病理學的研究者均沒有將語言和思維分開對待。第一次關于這個主題的激烈辯論早已結束。曾經將語言心理學用于研究精神分裂癥的美國馬塞諸塞州塔夫茨大學認知神經系統專家吉娜·庫珀伯格(Gina Kuperberg)說道:“許多已儲存在思維中的物體表達恰恰跟語言表達出來是一樣。”蒂托內也認為:“如果你想知道大腦在組織語言時的活動,并不是說那時正好就會有語言器官正被激活。”
艱難過程
正如布魯勒和安德森這兩個例子(均被庫珀伯格引用在其2010年發表的論文中),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語言中也通常保留著正常的語言結構。一般都遵循語法規則:語言的基本要素、音韻學以及一些語法,但語言不連貫也很難理解。蒂托內將這種現象歸因于這一事實,即從我們出生時語言結構特性就已滲入我們大腦中。等到了精神分裂癥發病的兩個典型期——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期早期,語言結構早已牢牢鎖定在大腦中。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交流混亂特點的主要問題在于如何組織語言來表達出其完整的意思。潛在的問題還包括大腦中詞義的存儲、個人組織方式和信息的更新。同時也是美國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家的庫珀伯格認為:“詞義即大腦。它存儲于整個大腦中并表現非凡。”在運用語言時,我們對內在和外在世界的思維表達方式已存在于復雜的神經網絡中。
在交流中,精神正常者可以將大量千變萬化的存儲信息進行分類,從而表達出可被理解的語言。但對那些精神分裂癥患者,這個基本能力已受損。這個問題通常被描述成“聯想渙散”,如詞語的選擇不是因為詞義而是因為患者能簡單將它們和其他詞語聯想在一起。因其受過A教授的教導,那個聲稱自己是地理學愛好者的患者先運用了他學習經歷中存儲的知識,然后迅速轉移話題并完全拋開教授,轉向一連串相關性不大的眼睛主題。安德森則是一位更嚴重的聯想受損患者,關于能源危機的問題使他的大腦像一個彈跳球一樣彈起來,激發了存儲神經網絡,轉化成語言時則成了胡言亂語。
當與其他人或外在世界互動時,不是精神分裂癥的人們會隨時更新和重新組織已有的信息。一天中,他們會根據與他們交流的人的特征(如他們的老板)來改變說話時的聲調。但是庫珀伯格的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難以進行這類實時更新,從而限制他們儲存知識和調整日常交流的能力。這種異常情況與大腦的前額葉和顳區間快速持續的互動障礙有關聯。在其他情況下,這個問題會引起認知剛性障礙,從而導致在講述某一主題時失去前后一致性。例如,在藥劑師向其索要處方時,患者會跟藥劑師討論天氣,因為幾分鐘前有人在巴士上談論過天氣。庫珀伯格還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自己意識不到交流障礙。
詞義理解
一般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在調用和組織大腦中信息方面存在問題,而不是指在首次存儲的信息方面。但是蒂托內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她說:“存儲的信息是基于現實世界的經歷。”精神分裂癥患者對世界有著不同的感受,所以信息存儲的方式即存儲結構可能起主要作用。
我們知道語言本身富有靈活性,有許多細微差別和模棱兩可,這些都會給精神分裂癥患者帶來困難。在一項研究中,庫珀伯格使用核磁共振成像系統、腦電圖和其他檢測手段來對比研究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語言功能差異。給她的實驗者每人發一句話:“每天早晨的早餐,雞蛋要吃。”這個句子結構有點小小的耍滑:單獨的詞語在語義上是相關的,但在整體上卻不能疊加起來用。試驗中,監測實驗者的腦電波活動,發現這句話甚至愚弄了正常人大腦的前百分之幾秒,之后意識到與存儲的知識(難以理解的句子)是相矛盾的,然后再進行語言的重新組織。然而,與實驗對照組不一樣,精神分裂癥患者不會進行額外的組織工作,也不會把這句話納入難以理解的語句。他們去認識矛盾、解決矛盾的額外能力已經受損。整個實驗過程中,測量和記錄了兩種腦電波的模式,一種是語法,一種是知識儲備。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對知識儲備的完全依賴戰勝了語法規則。
蒂托內說:“語言本質上是模糊的。單詞總是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在我們組織語言的時候需要動用很多認知能力來減少其中的歧義。而精神分裂癥患者在這方面就顯得特別困難。”
對類似“雞蛋要吃”這個上下文的反應遲鈍現象不只是理解能力的問題,而且與自身語言組織方式有關。在正常組中,神經網絡會結合上下文去理解某個語句或單詞。比如對于“bear”這個單詞你會根據情況區分它的各種含義。但神經分裂癥患者這方面的能力則差很多。蒂托內說,“如果你一聽到某一詞就下意識條件反射般給它下定義,將會很難再利用上下文去理解它。”
另一種部分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并發癥,特別在理解能力方面,事實上他們是逐字逐字去組織語言。當然,這種語言處理過程非常快,因為正常的大腦必須運用已經構建好的上下文去處理實時遇到的每個新詞。庫珀伯格說:“為了做這些,我們需要快速調動所有我們存儲的知識,并運用它們將單個的詞語結合起來從而產生新的意思。然后利用這些新信息更新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知識記憶存儲。”換句話說,對于語義記憶和工作記憶受損以及語境失靈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來說,這是一類更高階的語言功能。
語言隔離
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大學研究人類社交行為的心理學家吉姆·繆爾塞(Kim Mueser)指出,另一小組精神分裂癥患者面臨的問題是感情遲鈍。他們在交流過程中看起來情緒穩定,但實際上正經歷各種情緒波動,盡管他們的溝通能力是受損的。“當你談論社交行為時,通常他們中有90%談論的是語言能力。”
因此,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語言功能障礙對他們可以說是一場復雜的風暴,將會帶來復雜的心理疾病和同等復雜的高級大腦皮層功能障礙。患者將遠離交流帶來的簡單快樂,并無法與他人分享他們的思維和情感,這對他們來說的確是十分殘酷的。
拋開她的研究發現,轉而每天興奮地闡述兩個人交談時所發生的奇跡,庫珀伯格實際上想告訴我們一個觀點,她說:“你有你的世界、你的議程和你的目標。我有我的世界、我的議程和我的目標。并且我們互相不認識。可是你也可通過語言這個神奇的事物、它的詞序和音節與我進行交流,并用你的思想更新我的大腦。這難道不是件很酷的事?”
體現在奇妙又美好的語言中的有序思想的確是件很棒的事。因此,科學家在堅持不懈地探索精神分裂癥患者如何失去這個寶貴的禮物,并可能在某一天使他們恢復這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