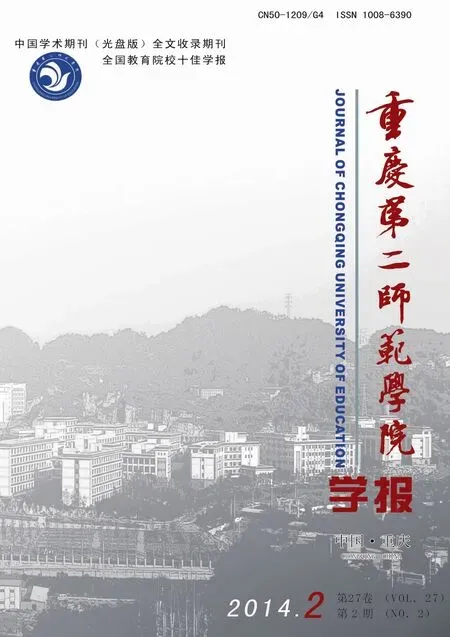內容有涉大明宮的三方唐代墓志再探
——兼與胡明曌、鵬宇二先生商榷
何 山
(西南大學 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
《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5期胡明曌先生《內容有涉大明宮的三方唐代墓志》[1]一文(下簡稱胡文),集中刊出三通新墓志銘文,分別為《大唐贈靖德太子哀冊文》(下簡稱《靖》)、《唐故韋府君崔夫人合祔墓志》(下簡稱《崔》)和《李公之妻京兆韋氏墓志》(下簡稱《韋》),公布拓片、釋文并考證,不僅有利于文史研究,而且為深入考察大明宮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顯得十分可貴。但筆者近日細讀之,發現其釋文有脫、衍、誤、倒等諸多錯誤,斷句和標點也有不當,對有關靖德太子名號等的分析存在問題,值得繼續探討。鵬宇先生《關于〈內容有涉大明宮的三方唐代墓志〉的幾個問題》[2]一文(下簡稱鵬文),主要就釋文中的一些淺層問題予以糾正,還有多處釋讀錯誤沒有解決,而且未考論內容分析中的失誤,其研究內容又出現了新的錯誤。這些問題嚴重影響文獻文本的科學準確利用。現結合志石拓本,進一步補正釋文和研究中的缺誤,旨在為歷史、文化等研究提供可靠材料,以便學界有效使用。
一、志文釋讀問題
總體上看,三通志石保存完好,拓本文字基本清晰,但個別字跡有缺泐,俗體訛字眾多,又給釋讀造成一定困難。如果釋讀過程中不認真揣摩文意,把握墓志行文模式和石刻文字變異規律,便會出錯。現依各志原文順序,分條校補釋文錯誤,并作適當考證。
1. 制冊贈為靖德太子。鴻,名也。(《靖》/6①)
逗號應去掉,“鴻名也”成句,與其后“至德也”對應,均為盛贊語。由于標點失誤,導致內容考論無據,詳后“二、靖德太子名號辨識”。
2. 嗟六極之遭短,恨重爻之遇長。(《靖》/20)
3. 宿霧霾空,長煙漲野。(《靖》/22)
4. 川夜游而聲咽,露朝唏而淚灑。(《靖》/22)
“唏”字誤,拓片清晰作“晞”,當正之。整句意思為山川夜游而聲音嗚咽,朝露干枯而哀傷落淚,烘托出一種悲涼的氣氛,表達對逝者的悲傷之情。作“唏”則文意難明。
5. 繐悵霜皓,麻衣雪清。(《靖》/25)

6. 潤州刺史操,夫人曾祖。(《崔》/1/7)
據原拓,“夫人”后脫“之”字,當補。
7. 衣必純素,食必糗糲……(《崔》/1/13)

8. 公食旨聞樂,忌音與味。(《崔》/1/16)
9. 遠自湖濱,達于京師。(《崔》/1/26)
10. 而附身附棺之具,衣服儀衛之要,無不必備。(《崔》/1/27)
11. 今夫家志著美也。(《崔》/1/27)
12. 彼女宗之見賴也如此。則右之遺范,彤史之載美。(《崔》/2/1)
“則”后掉一“闑”字,鵬文已補,但斷句標點之不當卻未予校正。“如此”應下屬,即整句應為“今夫家之著美也,彼女宗之見賴也,如此則闑右之遺范,彤史之載美,方于夫人,又何加焉?”表達了對夫人美好而又崇高德行的贊美之情。
13. 其年五月七日,祔遷與萬年縣少陵原……。(《崔》/2/5)
14. 端肅好禮,實儒林之壯士。(《崔》/2/7)
15. 既弱冠而明經登第。(《崔》/2/7)
據原拓,“弱”字誤衍,當刪。志文表達崔氏之子行加冠禮成人,通曉經術,科考登第。
16. 于戲,夫人貞方不渝。(《崔》/2/15)
17. 義以奉夫,諧以六姻。(《崔》/2/16)
“諧”后的“以”字誤,原拓清晰作,應改作“于”。
18. 勒銘泉垌,垂裕無涯。(《崔》/2/18)
19. 省太夫人太平里第,遇疾九日而終。(《韋》/12)
二、靖德太子名號辨識
胡文釋讀每通墓志并標點后,再結合志文考論相關問題,特別是有關大明宮的內容,作出了盡可能合理的分析與考證,值得充分肯定。但個別問題由于缺乏周密細致的考察,其結論亦有不妥之處,《靖》哀冊文中“鴻”并非志主靖德太子之名便是其中之一。
胡文云:“志文稱‘鴻,名也’,據《舊唐書·玄宗諸子靖德太子琮庶人瑛傳》:‘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直。……(開元)三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廢太子瑛,……改名鴻,(開元)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由此看,志主名不應為‘鴻’,而當作琮。”
細審志文,發現胡文致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誤解文意,從而誤斷文句。“鴻名也”不可點破,因為從該志行文格式看,并沒有介紹志主名號、表字的內容,而是直接記述“天寶十一年五月二日戊申,慶王薨于大明宮之十王院”后,總贊其“盛名”和“盛德”,即曰:“翌日有命自天,制冊贈為靖德太子,鴻名也;爰初地居守器,固辭而退就維城,至德也”。“鴻名也”與“至德也”相對為文,均為盛贊之詞,文意順暢。作者不明此意,誤將“鴻名也”標點作“鴻,名也”,并對照史傳,武斷地認為哀冊文記錯志主大名,后又以此批評撰文人“雖是位居高位的文人,卻將志主名字誤為太子瑛的曾用名‘鴻’,不可思議”,這是毫無根據的。隨后作者又舉史傳誤記死者卒年的例子,進一步論證即使高位文人也誤記死者相關信息的情況。其實,史傳乃后人所記,而墓志乃當時所作,故其卒葬時間等信息的準確度后者一般要高于前者[23],與上述情形不完全一樣,因此其旁證是無力的。故史傳所載志主名號與哀冊文并不矛盾,相反,據胡文,哀冊文“慶王薨于大明宮之十王院”與《新唐書》“十王宅,所謂慶、忠……”等的記載,可互證互補,墓志史料價值明顯。
三、撰文人趙楚賓
正如胡文所言,趙楚賓于史無征,但檢唐代出土墓志,除《靖》哀冊文外,他還撰寫有兩通墓志,分別為:天寶九年《唐榮王故八女墓志銘》,撰文人題名為“太子侍讀、兼侍文章、朝散大夫、守太子諭德、上柱國臣趙楚賓奉敕撰”;天寶十一年《大唐贈南川縣主墓志銘并序》,撰文人題名作“太子侍讀、兼侍文章、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趙楚賓奉勅撰”[24]。從中可知趙氏的仕宦等情況:1.三墓志所記趙楚賓職銜基本相同,多為陪侍太子讀書論學的官職和文散官職,有利于了解其身份;2.從撰志對象看,三墓主均為皇室后裔,《靖》哀冊文中“靖德太子琮”為玄宗長子,《八女墓志》記志主為“今上幼孫,榮王之第八女”,《南川縣主墓志》記志主為“皇帝之孫,故棣王之第五女”。表明趙楚賓作為一位文職官員,服務對象主要是皇室子孫,稱得上是皇室后裔碑志的專業撰文人,因此對皇族子孫的基本情況應比較熟悉。這既可為唐代碑志撰文人研究提供新的、有特色的材料,又可反證上述胡文所持論斷的錯謬。
四、奉天皇帝琮追贈及改葬時間
胡文稱“唐肅宗在去世前的寶應元年(762),又贈給他(筆者按:指靖德太子)‘奉天皇帝’稱號,改葬齊陵”。查相關史籍,《舊唐書·玄宗諸子·靖德太子琮傳》記:“肅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冊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備禮改葬于華清宮北齊陵。”[25]《唐會要·追謚皇帝》記:“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本名嗣直……謚靖德皇太子。肅宗元年,追冊為奉天皇帝,葬齊陵。”又同書《諸陵雜錄》記:“奉天皇帝齊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26]據此,奉天皇帝追贈及改葬時間應為肅宗元年建寅月,至于《舊唐書》、《唐會要》所記日期“九日、六日”的差異,本文暫不考論。檢長歷[27],唐肅宗于公元761年9月去年號,只稱“元年”,公元762年4月改元“寶應”,而“建寅”指夏歷正月,按照這兩個條件可判斷奉天皇帝追贈及改葬準確時間應為肅宗元年(762)正月,即是說追贈及改葬時間在改元“寶應”之前,而并非胡文所謂的“寶應元年”,因此胡文誤,應改作“肅宗元年”。
五、大明宮“宣政前殿”名源問題
宣政殿是大明宮的三大殿之一,史書有清楚地記載,如《宋史》曰:“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只日常朝則御之。”[28]志文為何稱“宣政前殿”,胡文沒有找到確切的文獻依據,僅根據《文獻通考》的解釋得出結論:墓志文中所稱宣政前殿即宣政殿,宣政殿本身并無前殿后殿之分。其實,據文獻調查,“宣政前殿”是承襲漢代稱法。《續資治通鑒·宋太宗淳化二年》[29]:“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朝,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據辭書引此例的解釋,“前朝”意思為前殿[30],則“在漢為前朝”意指漢代開始稱“宣政殿”為前殿,唐人承此,因此偶有如志文所稱的宣政前殿,實則就是宣政殿,志文“君對策宣政前殿”與史書“試制策舉人在此殿”的記載不謀而合。明確這一點,既可補正胡文,又可進一步了解大明宮及其三大殿的沿襲情況,為深入研究大明宮的歷史和各殿之間的關系提供有力參考。
注釋:
①“/”后的數字標示所引志文在志石中的行次(下同),以便核檢。
參考文獻:
[1]胡明曌.內容有涉大明宮的三方唐代墓志[J].考古與文物,2010,(5):77.
[2]鵬宇.關于《內容有涉大明宮的三方唐代墓志》的幾個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1,(2):100.
[3][4][16]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6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86.284.18.
[5]黃征.敦煌俗字典[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411.
[6](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15.
[7](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399.
[8]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7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42.
[9]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8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274.
[10](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56.
[11][14][1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507.2526.583.
[12][17]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4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130.237.
[13][15][20]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5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339.54.146.
[19][21]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2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62.19.
[22]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3冊)[M].北京:線裝書局,2008.170.
[23]何山,馬錦衛.漢魏六朝碑刻補正史書舉隅[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11):265-268.
[24]吳剛,宋英主編.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卷2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30.132.
[25](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3260.
[26](宋)王溥撰.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20.417.
[27]方詩銘,方小芬.中國史歷日和中西歷日對照表[K].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29.
[28](元)脫脫等著.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9591.
[29](清)畢沅編著.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374.
[30]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二卷)[K].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