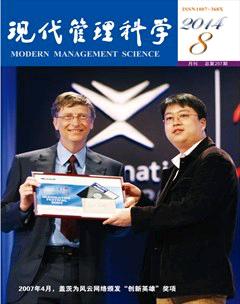消費模式改變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的影響機制
摘要: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居民的食品消費模式正在由“生存型消費”向“享受型消費”轉變,具體表現(xiàn)為“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和“按照美國水平消費”兩個變化趨勢。基于此,文章通過數(shù)據(jù)測算的方式,探討了消費模式改變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的影響機制。研究結論表明:中國人消費模式的變化趨勢將使部分農(nóng)產(chǎn)品需求大幅上升,進而給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帶來壓力,消費模式將成為中國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關鍵詞:消費模式;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影響機制
一、 引言
本研究將從“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食品”與“按照美國水平消費食品”兩個維度探討中國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供需情況,分析這種消費模式轉變趨勢是否會對中國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帶來威脅,進而判斷中國是否需要進行消費模式調整。
二、 城鎮(zhèn)水平消費趨勢下的食品需求變化與供給沖擊
為了判斷并預測在中國人食品消費模式“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變化后的農(nóng)產(chǎn)品供需情況,本研究假設隨著這種趨勢的發(fā)展,在未來某一時點,全體中國居民(城鎮(zhèn)與農(nóng)村)將以目前城鎮(zhèn)居民平均消費水平來消費食品。
1. 城鄉(xiāng)居民食品消費模式。由中經(jīng)網(wǎng)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庫相關數(shù)據(jù)可知,自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居民各類食品的直接消費量都出現(xiàn)了明顯的變化,但城鎮(zhèn)與農(nóng)村居民的食品直接消費量仍存在較大差異。在糧食方面,由于部分糧食被用于加工其他食品,城鎮(zhèn)居民和農(nóng)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費量(口糧)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呈下降趨勢,但農(nóng)村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仍然為城鎮(zhèn)居民的2倍左右。城鎮(zhèn)居民和農(nóng)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費量都呈增長趨勢,2011年城鎮(zhèn)居民的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費量為9.26公斤,而農(nóng)村居民則為6.60公斤。肉禽及其制品的人均直接消費量也有較大增長,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居民10年來的人均肉禽及其制品的消費量大約增加了30%~40%。蛋類方面,城鎮(zhèn)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費水平和農(nóng)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費水平差距有所縮小,但2011年該類農(nóng)產(chǎn)品城鎮(zhèn)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大約為農(nóng)村居民的2倍。奶類直接消費有較大幅度的提高,2011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奶類消費量是2000年的1.5倍,而農(nóng)村居民2011年人均奶類消費量是2000年人均消費水平的5倍左右。可見,無論是農(nóng)村還是城鎮(zhèn)居民,大部分食品的直接消費都隨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增加,只有糧食類食品(口糧)的直接消費有所減少。但這并不意味著糧食類產(chǎn)品的需求下降,畢竟還有很大一部分糧食類產(chǎn)品被用于加工生產(chǎn)或者轉化成其他食品,隨著其他食品消費量的上升,這部分糧食類產(chǎn)品的需求也在上升。因而從總量而言,糧食需求量仍然是上升的。
2. 城鎮(zhèn)水平消費趨勢下的食品需求變化情況。如前所述,假設未來某一時點,中國人都以現(xiàn)在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模式來消費食品,這將對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需求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作用。按照2011年的食品消費模式來計算,如果要保證中國人都以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模式來消費食品的話,除了糧食(口糧)以外,其他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需求量都將大幅度增加。
根據(jù)中經(jīng)網(wǎng)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庫的數(shù)據(jù)源計算而得,2011年中國農(nóng)村居民與城鎮(zhèn)居民的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人均直接消費量有較大差異。這兩者的差額分別為:糧食-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11.87千克/人、蛋類4.72千克/人、奶類12.74千克/人,這意味著如果所有農(nóng)村居民都按照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模式進行食品消費的話,將導致糧食直接消費量減少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費量增加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費量增加11.87千克/人、蛋類直接消費量增加4.72千克/人、奶類直接消費增量加12.74千克/人。那么,如果將上述數(shù)值乘以2011年中國農(nóng)村居民數(shù),所得到的信息則代表當農(nóng)村居民完全按照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模式進行食品消費時,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直接消費量的變化情況。此種情況下,食品直接消費將發(fā)生如下變化:糧食直接消費量減少5911.01萬噸、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費量增加174.65萬噸、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費量增加779.34萬噸、蛋類直接消費量增加309.90萬噸、奶類直接消費量增加836.46萬噸。
3. 城鎮(zhèn)水平消費趨勢對食品供給的沖擊。沿著上文的假設,將2011年的食品消費情況作為基準,當全國的居民都以城鎮(zhèn)居民的模式消費食品時,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需求將發(fā)生較大的變化,如果要保持國內供需平衡,則須增加國內供給,這必將給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出帶來一定的壓力。
由中經(jīng)網(wǎng)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庫相關數(shù)據(jù)可知,以2011年為基準計算,當全國的農(nóng)村居民都以城鎮(zhèn)居民的模式消費食品后,將給中國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帶來如下沖擊。第一,糧食(口糧)的直接消費量將減少,減少的幅度為2011年糧食產(chǎn)量的10.35%;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食用植物油產(chǎn)量的13.20%;第三,肉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肉類產(chǎn)量的9.79%;第四,蛋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蛋類產(chǎn)量的11.02%;第五,奶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奶類產(chǎn)量的21.95%。
另外,如果從城鎮(zhèn)化角度探討此問題,則可假設10年或者20年以后,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達到75%。那么如果75%的城鎮(zhèn)居民都以現(xiàn)有的城鎮(zhèn)水平消費食品的話,也將給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帶來一定的壓力。如前文所述,我們假設人口總數(shù)不變,2011年中國總人口數(shù)為134 735萬人(其中城鎮(zhèn)人口為69 079萬人),如果城鎮(zhèn)化率為75%時,城鎮(zhèn)人口則為101 051萬人,這意味著有31 972萬的中國人口由農(nóng)村戶籍轉變?yōu)槌擎?zhèn)戶籍。將上述轉變人口數(shù)分別乘以前文分析所得的城鄉(xiāng)人均消費量差額值,則可得到75%城鎮(zhèn)化率條件下,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直接消費量的變化情況。以2011年為基準計算,當城鎮(zhèn)化率達到75%時,中國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將受到如下沖擊。第一,糧食的直接消費量將減少,減少的幅度為2011年糧食產(chǎn)量的5.04%;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食用植物油產(chǎn)量的6.43%;第三,肉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肉類產(chǎn)量的4.77%;第四,蛋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蛋類產(chǎn)量的5.37%;第五,奶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奶類產(chǎn)量的10.69%。
可見,此種假設下,“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的趨勢將大大改變中國人對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的需求量。除了糧食產(chǎn)品直接消費量減少之外(其實糧食類產(chǎn)品的需求并未減少,因為用于加工轉化成其他食品的糧食需求量大大增加了),食用植物油、肉類、蛋類及奶類產(chǎn)品的直接消費量都將大幅度提升,在生產(chǎn)能力不變的情況下,這將降低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的自給率,對國內供給產(chǎn)生一定的沖擊。
三、 美國水平消費趨勢下的食品需求變化與供給沖擊
“按照美國水平消費”是中國居民食品消費模式變化的第二種趨勢,這種趨勢將對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需求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為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帶來了更大的沖擊。為了明確這種影響,本研究假設隨著“按美國水平消費”的趨勢不斷發(fā)展,未來某一時點將出現(xiàn)極端情況:中國人將全部以目前美國人的平均消費模式來消費食品。
1. 美國水平消費趨勢下的食品需求變化情況。如前所述,假設未來某一時點,中國人都以美國人的消費模式來消費食品,那么中國食品需求量將出現(xiàn)較大的變化。按照2009年美國居民的食品消費模式來計算,如果要保證中國人都以美國居民的消費模式進行食品消費的話,除了谷物(口糧)和蛋類以外,其他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直接消費量都將大幅度增加。
由FAO數(shù)據(jù)庫、USDA數(shù)據(jù)庫相關數(shù)據(jù)可知,中國居民的消費現(xiàn)狀與美國居民穩(wěn)定的食品消費模式有較大的差異。這兩者的差額分別為:谷物-63.09千克/人、油類24.95千克/人、糖類52.61千克/人、肉類2.69千克/人、蛋類-4.04千克/人、奶類63.25千克/人,這意味著如果所有中國居民都按照美國人的消費模式進行食品消費的話,將導致谷物直接消費量減少63.09千克/人、油類直接消費量增加24.95千克/人、糖類直接消費量增加52.61千克/人、肉類直接消費量增加2.69千克/人、蛋類直接消費量減少4.04千克/人、奶類直接消費量增加63.25千克/人。那么,如果將上述數(shù)值乘以2011年中國居民數(shù),所得到的信息則代表當中國居民完全按照美國人的消費模式進行食品消費時,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直接消費量的變化情況。此種情況下,食品消費將發(fā)生如下變化:谷類直接消費量減少8 500.58萬噸、油類直接消費量增加3 361.29萬噸、糖類直接消費量增加7 088.33萬噸、肉類直接消費量增加362.10萬噸、蛋類直接消費量減少543.74萬噸、奶類直接消費量增加8 536.11萬噸。
2. 美國水平消費趨勢對食品供給的沖擊。沿著前文的假設,以2009年的食品消費作為基準,當全國居民都以美國人的模式消費食品時,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直接消費量將發(fā)生較大的變化,如果要保持國內供需平衡,則須增加國內供給,這必將給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出帶來一定的壓力。
以2009年為基準計算,當全國居民都以美國人的模式消費食品后,將給中國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出帶來如下沖擊。第一,谷物的直接消費量將減少,減少的幅度為2011年谷物產(chǎn)量的16.37%;第二,油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油類產(chǎn)量的254.12%;第三,糖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糖類產(chǎn)量的471.93%;第四,肉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肉類產(chǎn)量的4.55%;第五,蛋類的直接消費量將減少,減少的幅度為2011年蛋類產(chǎn)量的19.34%;第六,奶類的直接消費量將增加,增加的幅度為2011年奶類產(chǎn)量的224%。
可見,此種假設下,“按照美國水平消費”的趨勢將大大改變中國人對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的直接消費量。除了谷物(如同前文所述,盡管谷物的直接消費量有所減少,但用于加工轉化成其他食品的谷物需求卻大量增加,因而谷物的總需求量仍然是增加的)和蛋類的直接消費量減少之外,油類、糖類、肉類及奶類產(chǎn)品的需求都將大幅度提升,在生產(chǎn)能力不變的情況下,這將降低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的自給率,對國內供給產(chǎn)生一定的沖擊。
四、 思考:消費模式改變與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問題
1. 供需變化與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人的消費模式正由“生存型消費”轉變?yōu)椤跋硎苄拖M”,具體表現(xiàn)為“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和“按照美國水平消費”兩種趨勢。隨著這兩種趨勢的發(fā)展,中國人的農(nóng)產(chǎn)品直接消費量將產(chǎn)生較大的變化,進而對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出帶來沖擊。
當然,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是指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體系意義上的安全,應該既包括消費者安全,又包括生產(chǎn)者安全以及市場穩(wěn)定。如果從中國社會繁榮、政治穩(wěn)定與經(jīng)濟發(fā)展多個方面綜合考慮的話,消費者安全應放于第一位,畢竟每個中國居民都是食品的消費者,消費者安全涉及的范圍最廣、影響最大。因而如果消費者安全受到?jīng)_擊,必將威脅到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而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角度的消費者安全主要體現(xiàn)在能否保證每個消費者都有足夠的食品進行消費,這無疑將受到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供需變化的影響。可見,當國內供需變化對消費者安全產(chǎn)生直接或者潛在威脅時,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問題也將隨之產(chǎn)生。
2. 消費模式與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那么,消費模式變化是否已經(jīng)構成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問題?對此問題的分析則需要進一步探討:這種消費模式變化趨勢是否會對消費者安全存在威脅。
盡管前文的需求變化與供給沖擊是在不考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提高,產(chǎn)量上升的前提下分析而得到的結論,但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分析沒有意義,相反這將給予我們一定的警戒與啟示。一方面,中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受限于土地、水資源等稀缺要素,即使不斷增加農(nóng)業(yè)技術投入,實現(xiàn)大部分農(nóng)產(chǎn)品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也較低。尤其是當中國居民都實現(xiàn)了美國人的消費模式時,油類消費增量為2011年產(chǎn)量的2.5倍、糖類消費增量為2011年產(chǎn)量的4.7倍、奶類消費增量為2011年產(chǎn)量的2.2倍,這種大幅度的需求變化根本不可能通過國內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提升來實現(xiàn)。因而消費模式的變化必將進一步挑戰(zhàn)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的自給率,對中國居民食品消費產(chǎn)生一定的威脅。另一方面,假設今后中國農(nóng)業(yè)領域內能不斷進行革命性技術創(chuàng)新,大大提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使得國內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能夠滿足這種因為消費模式變化而增加的農(nóng)產(chǎn)品消費量,這是否就意味消費模式變化不會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帶來任何威脅?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即使國內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能通過變革性技術創(chuàng)新來應對這種消費的大量增加,也改變不了這種消費模式變化對國內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帶來壓力的必然事實。換句話說,如果通過調整使得消費模式不發(fā)生這種趨勢性轉變,則將大大減緩國內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壓力,降低消費者安全的潛在威脅。
可見,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國內食品供需角度而言,消費模式將影響消費者安全,進而導致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問題的產(chǎn)生。一方面,如果國內生產(chǎn)能力能夠隨著消費模式轉變和大部分食品需求上升而不斷提高,這種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威脅將是潛在,即如果能控制調整這種消費模式變化趨勢,將能大大減緩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產(chǎn)出壓力,為其他產(chǎn)品釋放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如果國內生產(chǎn)能力不能夠滿足這種消費模式轉變所帶來的巨大需求增量,則這種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威脅是直接的,部分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的自給率將大大降低,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問題將越來越嚴重。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對中國人食品消費模式做出了趨勢性判斷,并通過數(shù)據(jù)估計的方法簡單測算了這種消費模式變化趨勢對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供需的影響作用,從而判斷消費模式變化是否會威脅中國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盡管數(shù)據(jù)測算部分并未采用科學的預測方法,數(shù)據(jù)本身也存在統(tǒng)計口徑差異等問題,但這僅會對數(shù)據(jù)精確度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并未影響趨勢性判斷。而本研究重點在于趨勢與影響作用判斷,而并非數(shù)據(jù)預測,因而上述問題對研究結論的影響作用有限。
通過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1)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居民的食品消費模式正在由“生存型消費”向“享受型消費”轉變,具體表現(xiàn)為“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和“按照美國水平消費”兩個變化趨勢。(2)中國人消費模式的變化趨勢將使部分農(nóng)產(chǎn)品需求大幅上升,進而給國內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帶來壓力,消費模式將成為中國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據(jù)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引導中國居民自我調整消費模式的轉變。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居民食品消費模式存在“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和“按照美國水平消費”的變化趨勢,而這兩種趨勢將大大提升部分農(nóng)產(chǎn)品(糖類、油類、肉類、奶類等)的需求量,進而給國內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帶來壓力,威脅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因而可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向中國居民傳播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知識,讓中國居民清楚這樣的消費模式存在一定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安全威脅,長期如此,將影響部分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自給率,最終可能導致食品大量進口,價格上升,影響中國居民的生活質量及水平。通過這種方式,引導中國居民對消費模式做出自我調整。
第二,倡導一種可持續(xù)、綠色的中國居民食品消費模式。由前文分析可知,“按照城鎮(zhèn)水平消費”和“按照美國水平消費”其實就是一種大量消費油、糖、肉、蛋、奶的消費模式。這樣的消費模式,一方面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現(xiàn)狀,因為中國的農(nóng)業(yè)資源有限;另一方面也并非健康的消費模式,是一種高蛋白和脂肪攝入的生活模式,容易產(chǎn)生各種營養(yǎng)病。因而適合中國的可持續(xù)消費模式應該是一種以谷物為主,蔬菜與肉蛋奶結合的綠色消費模式,這不僅有益于人體健康,而且能保證長期的國內供給。因而相關部門應該通過輿論、宣傳等途徑,在全國范圍內倡導一種可持續(xù)、綠色的中國居民食品消費模式。
參考文獻:
1. 許進杰.居民消費模式變化與資源性供給緊約束——以食品消費為例.蘭州商學院學報,2010,(4):7-11.
2. 許進杰.我國居民食品消費模式變化對資源環(huán)境影響的效應分析.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2009,(5):534-538.
3. 喻占元.發(fā)達國家食品消費模式的變化對世界糧食消費的影響.武漢糧食工業(yè)學院學報,1992,(3):64-68.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與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同步發(fā)展研究”(項目號:13AZD00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農(nóng)戶生豬養(yǎng)殖合作經(jīng)營創(chuàng)新發(fā)展與金融支持政策研究”(項目號:13YJCZH142)。
作者簡介:蔡鍵,中國人民大學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發(fā)展學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4-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