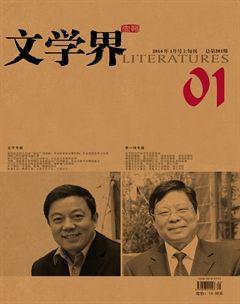“在場者”的言說
周明全
二○一二年,入魔似地迷戀上了文學批評,到處搜尋可資學習的理論專著和名家批評文集。忽一日,在一家專營二手書的書店,尋得王干的《南方的文體》,隨便一翻,看到了其中一篇《槍斃小說———魯羊存在的可能》,讀之,深受震撼,感慨道:原來文學批評可以寫得如此之率性,遂買下,收之于枕邊,每晚讀。一夜,忽有一夢,夢到和王干把酒暢飲,于是,起了見王干之心。錢鍾書老爺子說,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味道不錯就行了,何必要去拜會那個生蛋的母雞呢?然我卻入了魔,能把文學批評寫得如此行云流水之人,能把深奧的理論化簡成人人都讀得懂的人,非大師何以為之,大師都不見,還瞎搞文學批評做甚?
在友人劉濤的引薦下,于北京深冬一晚,在一間小茶室,終得一見,酒沒喝成,但卻發現,我和王干有共同之愛好———抽煙。這些年我發現,大凡抽煙者,即便是第一次見,亦能暢談甚歡。此后,和王干有幾次對飲,皆甚歡。
我學的是繪畫,搞文學批評屬半路出家,無師之教誨,無專業訓練之根基,然回頭反觀自己一年有余的文學批評之路后發現,其實,《南方的文體》便是我師,王干亦是我師。此有三解,一是我粗翻一下拙作《隱藏的鋒芒》,很多引文,或者寫作思路,皆來自《南方的文體》;二是我第一篇刊發在學界享有盛譽的《南方文壇》上的《批評·寬容·懺悔》一文,乃是王干兄極力推之的結果,且一年來的起步之路,甚得王干兄之提攜與鼓勵;三是拙作《隱藏的鋒芒》的序言,乃是王干兄所作,王干兄在序言中,對我的優勢和缺點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實乃是我今后為文需深記于心的。
拉拉雜雜說一大堆,似是未切入寫作主體,實不然,文學落到實處還是人學,大凡在歷史中留下盛名的,一定是那些德高望重之人,成績會有大小之別,而做人,卻只有一條正道。王干兄讓我折服的正是這一點。他為人率性、所以文亦率性,這是很多文人,尤其是批評家很難為之的。板起面孔做學問,學問自然是死的,王干兄喜美食、善書法、喜交友,他是活生生的文人,他的文字,無論是散文隨筆還是文學批評,自然也泛著生機與活力。
近期正責編王干兄的《在場》一書,幸福之感難以言表。
一、文學的味覺
牛學智在《李敬澤:新總體論文體批評》一文中說,《人民文學》在新時期特別是李敬澤任編輯、副主編、主編以來幾十年間的選稿標準、引導方向,尤其在全國“最優秀”的稿源里馳騁縱橫所練就的“全國性”眼光,再加上散文創作對其語言的鍛造,使得李敬澤的文學批評呈現出兩個方面的價值。一是眼光獨到;二是散文創作練就了他靈動、輕巧又從容、跳躍的文體意識和語言風格。王干在一個專訪中也說,李敬澤他們都叫他“干老”。其實,王干和李敬澤的工作經歷完全相仿。王干一直和文字打交道,在《文藝報》《鐘山》《中華文學選刊》工作多年,目前在《小說選刊》任副主編。策劃過《鐘山》《大家》等多種文學刊物,主編有《新狀態小說文庫》、《突圍叢書》《華文2005年度最佳小說選》等,并且,出版過多種散文隨筆,二○一○年,《王干隨筆選》還獲得了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07—2009,散文雜文類)。
王干兄屬早慧型批評家。三十歲不到即蜚聲文壇,并且始終站在文學思潮的前沿,他以創新的精神推動了當代文學的發展,“新寫實”“新狀態”“城市文學”“女性寫作”,直至近年來的網絡文學浪潮,都能看到王干勇立潮頭的身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其他批評家是在岸上看魚游泳,而我自己是在游泳。”從開始寫小說,評論小說,到后來在《鐘山》編小說,發小說,推小說思潮,推小說作家,最后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小說、賣小說,可以說一個完整的鏈條差不多都做過來了。這些“轉身”,讓王干始終處于文學的最前沿,感受著文學最新鮮的氣息,一直保持“在場”的姿態。這是為什么王干的批評文章會深入讀者喜愛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學院派身居高墻內,板起面孔做研究,和當下創作幾近脫節,而王干自始至終,一直在文學的現場,潛身感受文學的鮮活,文字自然鮮活。
王干的文學批評之路,始于對汪曾祺小說的研究。汪曾祺是中國現當代小說大家,他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也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王干自己曾坦承:汪曾祺給了我一個比較好的審美的眼光,或者說能夠鑒別文學的一個味覺,這個味覺判斷的能力比較強大是很重要的。那時候模仿他的小說,研究他的小說,到最后跟他接觸,就是味覺提升了。我覺得汪老他給了我一個文學的味覺,一個良好的味覺,能判斷各種味道。
有了良好的味覺,才能對流動的問題、對嶄露頭角的新人、新作有所判斷。在《文藝批評ABC》一文中,王干說,文藝批評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它的預見性和警示性,一個批評家從一部作品看到某種好的苗頭加以褒揚和深化,可能促進作家對一個藝術問題的思考,會導致新的藝術方式的出現。反之,一個批評家從一個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種不好的傾向,對作家提出忠告甚至嚴厲的批評,亦是文藝批評的正常功能之一,或許這種不好的傾向可能是作家無意識流露的,甚至是作家最為深惡痛絕的,但并不能阻止批評家的批評和警示。
莫言的《紅高粱》,成為了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兩年探索新潮文化的組成部分,但王干卻在眾聲喧嘩中,看到了莫言創作的“反文化”,寫下了《反文化的失敗———莫言近期小說批評》這一有深遠影響的文章。王干認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就是因為正視人性和世界的負面,才使人類意識到自己有一條割不斷的動物尾巴,意識到在理性的表象下藏著非理性的本能和沖動,反文化便成為人的新的生存要求。但是,王干從《紅高粱》中,卻發現了莫言在反文化的旗幟下干著文化的勾當,莫言在褻瀆理性、崇高、優雅這些圣神了的審美文化規范時,卻不自覺地把齷齪、丑陋、邪惡另一類文化圣神化了,也就是把另一類未經傳統文化認可的事物“文化”化了。
王干直言汪曾祺對他的影響,除了“提高了自己的審美”外,我想,對文本、語言的影響亦在王干所言的影響之列。這在《槍斃小說———魯羊存在的可能》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這讓我第一次見到這篇文章時,驚呼,原來文學批評可以這樣寫。后來,在酒桌上和王干聊起我當初讀此文的驚呼時,王干笑答:那時年輕,現在很難寫出這樣的文章了。其實,這是王干的自謙,王干文學批評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活,語言活、觀點活、文本活,屬感覺型批評家———王干的文學批評,很少使用注釋,這在學院派批評家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在接受采訪時,王干說:文學每天都在變化,新人在不斷涌現,作品在涌現,比方說,我不可能對一個“茶杯”研究三年五年,或者說三、五個月都不行,那么我就必須感受,我說它是白的,或者是別的什么,至于它是不是橢圓的,我可能就忽略了,我就抓住它白的這一面去感受它。這就是我意識的當代的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中,當下的這種關照,就更需要一點感受、感覺的東西。對流動的、沒有坐標體系的小說進行評判,是件相當考驗批評家判斷力和眼光的事。但王干有這個實力,王干是才子型的批評家。endprint
《槍斃小說———魯羊存在的可能》打破了文體限制,整篇評論文章行云流水,但又不是批評家的判斷。當看到魯羊的《仲家傳說》之后,又在《收獲》讀到魯羊另一個短篇時,王干不禁感嘆道:五年之后又是一個蘇童。
王干的評論,文風跟學院派評論完全不一樣。張莉曾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讀評論的經驗,有的評論看起來真有學問,也可能很有理論功底,但作為讀者的我們不想看,而有些評論卻是我們很想看的,因為它深入銳利,別開途徑。王干的評論,就是我們很想看的評論。它好看,可讀性強。王干說,我的評論內部隱藏著一種敘述的東西,而且,在文風上,王干受古代文風影響比較大,有時候會帶有抒情成分。比如詩評,王干追求的境界,簡單地定位就是以詩評詩。
二、南方的文體
王干一直在呼喚一種嶄新的文體———南方的文體,“這樣的命名就是一次神示”。那什么是“南方文體”呢?王干的定義是:描述的文體是一種南方文體。在王干看來,南方文體不是一個“主義”,也不是一個流派,更沒有宣言,它是評論的一種狀態,一種猶如蟬之脫殼的新狀態。南方文體是一種作家的文體,是一種與河流和湖泊相對應的文體,它的流動,它的飄逸,它的輕靈,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體的嚴峻、凝重、解釋、樸素。北方文體是學者的文體,這是與山峰和長城密切相關的文體,在文學理論和批評的領域里,北方文體始終占據中心和主導的地位,而不像南方文體處于邊緣的、被遮蔽的狀態;北方文體追求立論和結論,而南方文體更注重過程的狀態;北方文體相信公共原則,而南方文體則傾向于大化的語體……但是南方文體顯然是一種新鮮的文體,是一種需要發展、需要補充的文體,它的熱情,它的稚嫩都充滿著一種青春的光彩,而北方文體的成熟、老到都是一種中年的象征。
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必須有自己的理論構建,王干的“南方文體”構建,和早年的工作經歷相關聯。一九八二年,王干在高郵,負責收集編撰地方志的資料,這種紀實性很強的工作,限制了王干評說的沖動,當然,也讓王干意外收獲了不少,他自己也說,要感謝那個職業對我個人化書寫的充分限制,要是一開始就讓我從事文學這種個人性、自由性很強的職業,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選擇文學批評這樣一個特殊的方式。
王干說,所謂南方文體,就是一種描述的文體。王干說,直到如今,我的評論文字仍含有大量的描述成分,有時描述甚至大于說理。我對描述有種特殊的喜愛,因為我在描述時感到筆端有種說不清的滋潤和靈動,這似乎與我環繞我周圍的湖泊和河流有關,讓我初習評論便帶有一股水意,從而避免了初學者易犯的文字枯燥癥。描述作為一種評論的方式顯然不是完美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但它可以展示具體的而不是干巴巴的文學現象和作家狀態,它生發出來的信息量不再是簡單的、僵死的結論,而且有一種重新組合、重新認識的可能。
王干是南方文體的倡導者,亦是踐行者。王干幾乎所有的評論文章,都是“南方文體”的展現,它飄逸、輕靈、敏捷。比如《蘇童意象》一文,王干以第一次與蘇童相見,蘇童醉于草莓為敘述點,將蘇童小說中常用的一個意象“紅”做了深刻的分析,繼而,王干發現,蘇童小說中的人物名字,竟然大多與“紅”的韻母“ong”相同或相近,這讓王干按圖索驥地發現,“ong”韻母之所以為蘇童反復用之。乃是和蘇童的種族記憶和童年經驗有關,而且,蘇童的太太魏紅,自然也帶上了“ong”音。這樣的介入方式,非天才無以為之。
這也不難理解,當網絡文學繁盛之時,王干愿為之吶喊。在王干看來,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相比,它是欠規范的,是流動發展的,是有彈性的。它的很多地方會逸出傳統文學的規矩之外,或放大、或縮小,在一些獨特的地方才華橫溢。尤其在文體上,打破常見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以及評論的局限,或者將這些文體雜糅在一起,不拘一格,不是帶著鐐銬跳舞,而是在跳舞時砸碎鐐銬或化鐐銬為道具。他歡呼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理想中的開放文本,在今天終于通過網絡得到了實現。
三、批評是條魚
王干無數次“轉身”,但始終在文學這個行當中,在“流動的文學之中”,無怪乎他會寫下《批評對我來說,是條魚》。“文學是水,批評是魚”,王干自喻為魚,大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味道。
郜元寶說,王干作為文學里面非常獨特的一個現象,非常少見。這么一個編輯,一個評論家,他能影響當代文學的走向和動靜。這么一個人,對文學能像一個文學的發動機,不斷給文學增添新的話語、新的話題。王干這對文壇的貢獻是很大的。
王干自喻為魚,能第一時間感受到文學之水的寒暖,自然對很多新事物、新現象能快速地把握到、把握準,并用適當的方式將之表達出來。比如,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王干就在《北京文學》發表《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提出了“還原生活、零度寫作、與讀者對話”三個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成為后來“新寫實”小說的理論概括。
王干說,我做文學評論,是建立在對文學思潮的跟蹤、描述、分析和研究這個基礎上的,而且我是一直在做這個事的,后來我又把這種思路帶到做刊物上去了,這樣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樣了。人家刊物呢,可能就作家做作家,就作品做作品,那我可能把一個作家一個作品,或者幾個作家幾部作品把它當成一個現象、一個類型、一個思潮來概括,來推出,所以給人的就不是那種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覺,而是一種整體的、一個浪潮的沖擊。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感覺,所以大家覺得,啊唷,王干一出手就動靜比較大。這個呢,按照以前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嘛,就是要找到一種事物發展的脈絡,或者所謂的規律。當然文學的規律是相對而言的,因為任何一種概括都是犧牲到其他跟你不吻合的東西作為代價的,所以這有時候也帶有一點揠苗助長吧,但不論怎樣,它可能比一般的辦刊物、一般的寫評論啊,輻射面、信息量都要大———這就是魚對于水的敏銳。
汪曾祺老人家曾說,有王干在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了。汪老已仙逝,王干責任重大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