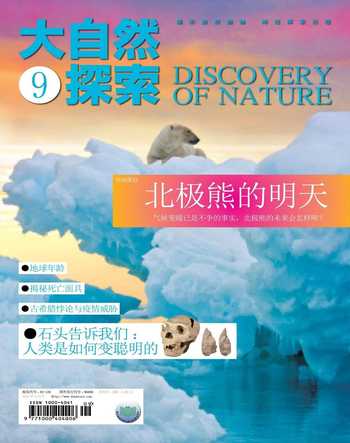呼吸新鮮空氣
文穎




屋頂上的發現
冷戰高峰時期的1968年,一個溫暖的夏夜,英國國防部最著名的化學和生物研究基地——波頓高地上,微生物學家亨利·道格和K·R·梅兩人正站在一間實驗室的屋頂,在他們的心頭盤旋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如果發生一場生化戰爭,如果一枚攜帶致命細菌的炸彈在倫敦上空爆炸,生化細菌的危害將會持續多久?
為了尋找答案,兩人用人造蛛絲纏繞兩把梳子,再在蛛絲上噴灑一些大腸桿菌。然后,他們將其中一把梳子暴露在屋頂的氣流中(之所以用人造蛛絲纏繞梳子,是為了阻止細菌被風吹走),而把另一把梳子裝進一個溫度和濕度同室外一樣的盒子里。
兩個多小時后,屋頂上幾乎所有被困在人造蛛網上的細菌都死了,而在被裝進盒子里的梳子上,居然有一半以上的大腸桿菌仍然存活。這是怎么一回事呢?難道是新鮮空氣中有什么東西殺死了細菌,一旦封閉空氣,這些東西就消失了?
接下來的許多實驗結果顯示,這種神秘東西的力量(被稱為“露天因素”)在每個晚上都會發生變化。
隨著冷戰結束,生化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減小,研究人員停止了對這個項目的研究。
時間過去了很多年。如今,隨著病原體對抗生素產生越來越多的耐藥性,人類對于對抗傳染病的“新式武器”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迫使研究人員開始重新審視那些塵封已久的研究報告。
事實上,最早注意到新鮮空氣好處的并不是亨利·道格和K·R·梅。早在19世紀中葉,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護士先驅南丁格爾率先發現,英軍士兵在骯臟的野戰醫院里的患病死亡率比戰場上的死亡率還高。于是,南丁格爾對戰地醫院進行了一系列改造,其中包括敞開窗戶。結果,戰地醫院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南丁格爾回國后,將這些經驗引入英國醫院。她曾寫道:“有必要給病人頻繁地更新空氣,這樣可以帶走從肺部和皮膚散發出來的病態臭氣。”
被稱為“南丁格爾病房”的病房擁有狹長的房間和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推拉窗,新鮮空氣得以流通。稀釋空氣中的病原體,并殺死它們——這不正是波頓的兩位英國研究人員所希望的嗎?
南丁格爾病房設計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病房的長邊都朝南,這可以讓充足的陽光穿窗而入。很快,大眾普遍認識到了陽光對于健康的好處,特別是對肺結核患者大有裨益。在當時擁擠的城市中,有1/5的人因患肺結核而不幸過世。
陽光不僅能將空氣中的細菌以及皮膚上的細菌殺死,它還能促進身體制造更多的維生素D,增強人體免疫系統,殺死體內的結核病菌。到20世紀末,“太陽診所”成為一種時尚,它利用新鮮空氣和陽光作為結核病治療方案的一部分。輪式病床被推到陽臺上或者安裝有能讓紫外線滲透進來的特殊玻璃的溫室中。
最終,還出現了一種專為醫院研發的紫外線燈。不過,這種紫外線燈很快失寵,因為它被發現增加了患者患皮膚癌和白內障的風險。今天,這種燈通常只被用作外科手術的滅菌設備。
培養皿中的奇跡
1928年,在亞歷山大·弗萊明外出度假期間,他的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細菌發霉了……幾年后,青霉素的發明讓醫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的近乎神一般的效力相比,新鮮空氣和陽光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新的抗生素如雨后春筍般被研發出來。到20世紀60年代,許多醫生認為傳染病很快就會被征服,因為病人一旦感染上某種疾病,醫生就會給他開抗生素,病人服用后身體就會有所好轉。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又帶來了“能效”這一新概念,人們認識到開窗會讓寶貴的熱量流失,于是便在室內安裝機械通風設備,靠機器的過濾系統循環空氣。南丁格爾的教誨被人們拋之于腦后,人們關閉窗戶,擋住陽光,“露天因素”不再受到關注。
然而,人類征服傳染病的希望不幸破滅。在過去的30年中,每一年都會新增一例傳染病。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遭遇了非典和禽流感等大規模時疫的侵襲。更糟糕的是,一些在20世紀60年代很容易治愈的疾病,現在都以耐抗生素的形式卷土重來,其中包括結核病、肺炎和淋病。就連醫院本身也成為耐抗生素痢疾和傷口感染的最大致病源。在英國,近9%的病人是在入院期間感染上新的傳染病的。
更令人崩潰的是,新型抗生素的短缺情況越來越嚴重。自1990年以來,全球自主研發新型抗生素的大公司數量已從原來的18家下降到可憐的4家。2013年,英國首席醫療官薩莉·戴維斯在其年度報告中警告說:“我們過去能夠輕易控制的疾病,如今可能會卷土重來,對我們的身體健康造成更顯著的威脅。”
當然,還有許多備選藥物可供選擇,其中包括“群體阻斷性藥物”,它們并不殺死病菌,只是起到阻止病菌發起攻擊的作用。這樣的藥物應該不會像傳統抗生素那樣引起耐藥性。另一種備選方案是噬菌體療法,也就是使用轉基因的病毒來消滅病菌。
然而,這些備選方案都需要幾年時間才能用于臨床,現在還指望不上它們。那我們應該怎么做呢?
露天療法的回歸
也許,前抗生素時代的一些經驗可以派上用場了。有專家指出,重新引入陽光和新鮮空氣,應該能為阻止疾病傳播帶來好處。英國微生物學家斯蒂芬妮·丹尼爾指出:“未來醫院的設計,應允許打開窗戶,患者也可以被推到病房外。”她試圖重振醫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她說:“只有在抗生素失效、病人無法康復的今天,我們才會想起回顧塵封已久的歷史。”
當然,僅僅靠拉開窗簾、打開窗戶是治愈不了病人的,但對醫院的設計進行一些改良,這或許可以幫助阻止疾病蔓延到無辜的人身上。一種老式的疾病預防方法已見成效——僅僅是讓醫護人員勤洗手,就能有效阻止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和梭狀芽胞桿菌這兩種超級病菌在醫院的蔓延。在英國醫院,MRSA的發病率從2004年的峰值下跌了約80%,雖然勤洗手不是唯一的因素,但似乎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醫生勤用酒精搓手的醫院,MRSA的發病率降低。
在秘魯首都利馬,一個英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可否采用傳統的方法減少空氣中結核病的蔓延。結核病的傳染多發生在已確診病人和易得病、身體虛弱的未確診病人,尤其是那些艾滋病感染者之間,因為后者的免疫系統比常人低很多。擁擠的候車室是病菌傳播的高發地,醫院門診室和急診室也是如此。
在利馬城內,英國研究小組在兩種醫院——仍依賴于被動氣流的老式醫院,和使用現代化機器通風設備的新式醫院——做實驗:打開二氧化碳滅火器,并測量氣體被驅散的時間。結果顯示,老式醫院的通風率是新式醫院的兩倍。受該研究的影響,利馬醫院的管理者正盡可能多地增添醫院的窗戶數量。
不過,經常讓病房的窗戶大開也不是辦法。該研究團隊又開始探索:人造陽光是否也能有所幫助呢?他們將豚鼠分別暴露在有紫外線照射和未有紫外線照射的病房中。結果顯示,紫外線燈將出現結核病感染跡象豚鼠的比例從35%降低到了10%,這表明人類患者也能因此受到保護。
這項研究成果已經吸引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結核病和艾滋病高發地區國家的注意。該實驗在南非被復制,那里干燥的空氣似乎進一步增強了紫外線的效果。現在,秘魯、俄羅斯和巴西的很多醫院里都安裝了紫外線燈。
有一種方法或許能使紫外線燈變得安全,從而在醫院里被廣泛推廣。紫外線是波譜中波長為10~400納米的那一段。其中,波長為207納米的紫外線可被蛋白質分子吸收,而且只能在人體細胞中穿行一小段距離,不會到達DNA造成變異。而對于病菌,由于病菌的體積比人體細胞小得多,所以這種紫外線能夠完全穿透,并輕輕松松將其殺死。實驗室中培育的細胞顯示,這種短波輻射不會傷害人的皮膚組織,但能殺死包括MRSA在內的病菌。現在有專家建議,將醫院里所有的燈都換成能發出207納米波長光線的紫外線燈。
除了人造陽光,新鮮空氣是否也能帶來好處呢?40多年前,亨利·道格和K·R·梅最終認定,他們在波頓的屋頂發現的那些神秘的殺菌劑是羥基自由基——空氣中的臭氧和水反應,再加上來自植物的有機物質的催化,羥基自由基分子在大氣中不停地被產生出來。如此看來,還是開窗更簡單吧。不過,英國醫院規定,為了防止患者從窗戶掉下去,患者能夠到的窗戶打開寬度不得超過10厘米。
流通的新鮮空氣,不僅可以讓醫院減少疾病傳播,也可以讓任何人類密集居住的地方獲益。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美軍士兵駐扎在沙特阿拉伯沙漠中。一項研究發現,與住在帳篷或倉庫中的士兵相比,住在配備了空調的營房里的士兵更容易感冒咳嗽。還有一項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在通風不暢的宿舍里睡眠的學生,有35%在一年時間內感染了疾病;而在通風較好的宿舍,這個數字是5%。
在未來,我們很可能看到建筑師和醫生攜手努力,在營造我們舒適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時,盡可能多地考慮那些在我們身邊的微生物。當然,我們還要向偉大的南丁格爾護士學習,盡可能多地把一縷縷新鮮空氣引進家門。她說:“永遠不要害怕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