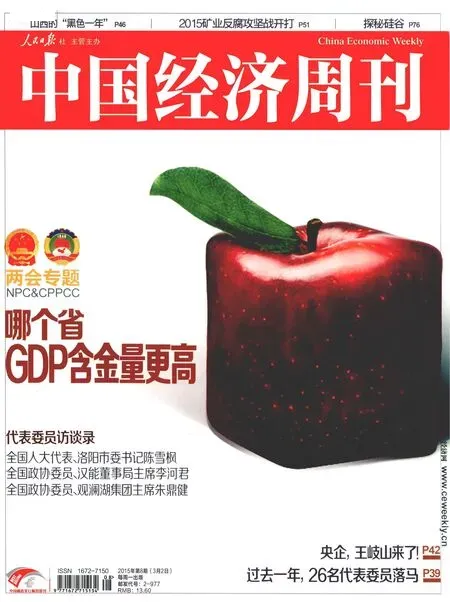從沃爾克戰通脹看央行保持獨立性之難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之一,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在這本沃爾克的傳記中,新任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撰寫了序言,講述了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如何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沃爾克奇跡”,并為美國此后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

《力挽狂瀾: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推薦指數:★★★★
作者:威廉·西爾伯
譯者:綦相 劉麗娜
出版: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1979年8月5日,卡特總統提名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接替威廉·米勒。此時,美國正遭受著高通脹的困擾。
沃爾克在紐約聯儲當過操盤手,懂得市場心理的脆弱性,也相信芝加哥和明尼蘇達學派的合理預期理論。因此,按當時的形勢來看,他明白回旋的余地不大,治理通脹不能操之過急,一上來不能火力太猛,以致瞬間彈盡糧絕。不到真正的危機階段,過于激烈的舉動難以得到社會上的理解和支持。這就是為什么他在上任之初,顧及美聯儲有些董事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在主持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上,建議聯邦基金利率緩步上升。由于美國通脹的嚴重性,光是調整聯邦基金利率已經無濟于事,所以,沃爾克要考慮提高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這個問題的爭議很大,因為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對市場的影響更加直接,市場的反應也將更加激烈。所幸,他的建議以微弱多數得到通過。
沃爾克實施的貨幣政策,打擊通脹的力度之大,被喻為法國元帥菲利普·貝當的1916年凡爾登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貝當以傷亡35萬血肉之軀的代價,抗擊德軍,守住了陣地。沃爾克能否守住,承受幾十萬失業大軍的壓力,同樣是嚴峻的考驗。我當時初到美國工作,對美國經濟的特點和運作沒有深刻了解,但是,親身體驗了這種驚心動魄的抗通脹之戰的氛圍。利率飆升,貨幣市場的利率一路攀升至21.5%。當時,有些人并不看好沃爾克這場“豪賭,認為他賭技不高,賭注卻下得很大。
沃爾克親自發動的這場抗通脹大戰,是對他智慧和毅力的雙重考驗。他斷然否認自己是賭徒。沃爾克認為,一旦傳統的辦法無濟于事,就得探索新的路徑,雖然新辦法是未經證實的策略,那也只能如此。市場最初的反應是正面的,歐洲諸國對他的舉措持肯定的態度。沃爾克贏得了這一美譽:“25年來第一個拿了那份薪水做了該做的事情的美聯儲主席”。
客觀世界總是復雜的,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按照合理預期理論,抗通脹手段會使短期利率飆升,另一方面,對通脹下降的預期又會使長期利率下降。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十年期國債利率隨著聯邦基金利率一起上揚。這就不得不使人懷疑合理預期的理論是否站得住腳。但是,沃爾克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明白合理預期理論在現實中得到證實,需要一定的條件。他認為,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不降反升,乃是因為美聯儲的公信力存在問題,市場懷疑這種政策的持久性。沃爾克堅信自己的路是對的,因此放手讓利率自由浮動,而將貨幣發行總量作為緊緊對準的目標,讓市場深信這是美聯儲負責任的政策,是新的綜合性政策的象征。他汲取前聯儲主席伯恩斯的教訓,不能半途而廢。但是,美國當時的通脹是非常頑固的,一兩劑猛藥下去,短期內也難以奏效。
當經濟運行處于某種失控狀態時,無論是通脹、通縮,還是金融、債務危機,采取應對措施時,一要拿得準,二要堅持到底。頂住各種壓力,面臨一時挫折也不為所動,實在是非常難的事情。
美聯儲的高利率政策,遭到了國會的強烈反應。有人揚言要彈劾沃爾克,甚至質疑美聯儲是否有必要存在。卡特總統對沃爾克也很不滿,雖然不能直接去干預沃爾克的政策,但是,其對美國經濟短期內造成的嚴重影響,作為一個謀求連任的總統來說,是不可能不關心的。卡特認為,他后來之所以敗在里根手下,主要是美聯儲的政策使然。里根當選之后,情況并未改善,通脹依然高企,失業率達到8.6%。雖然里根同樣不滿,但是他認為美聯儲應該是獨立的,總統無權威逼美聯儲主席下臺,也不能撤換任何董事。里根的競選口號是減稅,刺激經濟,但是,減稅直接減少財政收入,擴大債務,從而引發通脹預期。所以里根上臺之后,美聯儲的形勢似乎更加嚴峻。
沃爾克堅持認為,必須削減財政赤字,在此基礎上再對稅收政策做出最后的決策。沃爾克謙恭而強硬的立場,使得里根無可奈何。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終于和里根總統達成諒解,里根同意增稅,削減赤字。里根內心的盤算是,到1983年沃爾克任期屆滿時,讓他走人。但是,總統也拗不過市場的力量。他入主白宮之后兩年,沃爾克已經成功地把通脹降低了三分之二。等到里根面臨對沃爾克去留的抉擇時,他找不到第二位人選在形象、地位和業績上能和這位美聯儲主席匹敵。雖然在沃爾克的壓力之下,里根有違競選時的許諾,被迫增加稅收,但是,他上任之后美國經濟逐步好轉,走出高通脹的困境,這是明擺著的事實。當美國的經濟總體上向好的方向發展時, 選民是不會糾纏在一兩件事情上責問總統競選時的承諾的。事實上,正是沃爾克的功績,里根在連任競選時,才有底氣向選民提出了充滿信心的問題:“和四年前相比,你們的生活是好了,還是壞了?”
美國國會對美聯儲構架的設計和董事任期的確定,有一番精心考慮,以防止行政當局干預其獨立決策。美聯儲董事的任期是14年,任期的時間是交叉的,因此,每位總統在任期內先后最多可以任命兩位董事。但是,獲得連任的總統有機會任命四位董事。沃爾克能夠頂住國會和總統的壓力,執行一條對美國經濟長期發展有利的政策,除了他個人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之外,還得益于董事會多數成員的支持。不過,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主席也只有一票,孤掌難鳴,獨木難支。里根的連任使他獲得了任命四位董事的機會,當這個“四人幫”開始左右局勢之后,沃爾克執掌下的美聯儲就逐步失去了獨立性,為現政府服務的傾向性日益明顯。
如此看來,要做出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多么的困難。在崇尚權力制衡的美國尚且如此,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其難度,就可想而知。問題是,為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是否應當朝著獨立貨幣政策這個方向去努力?中央銀行不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不能有過多的政策目標,過于寬泛的貨幣政策目標必定是造成宏觀經濟混亂的根源。
(文章節選自本書序言,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