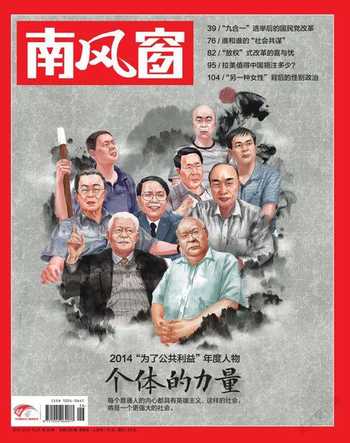秦暉:用底線構(gòu)建公共話語(yǔ)的文明城邦
葉竹盛
秦暉,以及這個(gè)時(shí)代其他真誠(chéng)地在為這個(gè)國(guó)家尋求底線、堅(jiān)守底線的學(xué)者,實(shí)際上是用底線為思想與言論建構(gòu)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沒(méi)有這樣的城邦,當(dāng)人們向著理想進(jìn)軍之時(shí),思想的論爭(zhēng)必然會(huì)在權(quán)力與利益的糾葛中,要么迷失方向,要么硝煙彌漫。
秦暉講過(guò)一個(gè)故事。2002年在法國(guó)的一個(gè)研討會(huì)上,他談?wù)摗白杂芍髁x與社會(huì)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時(shí),遭到一位法國(guó)學(xué)者的詰問(wèn):主張自由放任的人與主張福利國(guó)家的人,怎么可能有共同立場(chǎng)?秦暉用法國(guó)當(dāng)年大選中發(fā)生的事情做回應(yīng):“怎么不可能有?最近你們這次大選中,反對(duì)勒龐上臺(tái)不就是這兩者的共同立場(chǎng)嗎?”
勒龐是法國(guó)極右翼政黨的領(lǐng)導(dǎo)人,這個(gè)被稱(chēng)為新納粹黨的極端黨派支持“驅(qū)逐移民”、“恢復(fù)死刑”、“在憲法中寫(xiě)入法國(guó)人優(yōu)先”等極端政策。在法國(guó)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問(wèn)題漸入困境的情況下,勒龐當(dāng)時(shí)的支持度連年上升,在2002年大選的第一輪投票中得票排名第二。為了防止勒龐當(dāng)選,法國(guó)左右兩派政黨摒棄前嫌,左派社會(huì)黨也將選票投給了右派候選人希拉克,成功助后者高票當(dāng)選。“為什么要反對(duì)勒龐?因?yàn)槔正嬌吓_(tái)會(huì)威脅到法國(guó)已有的許多東西、即左右派都認(rèn)同的自由民主人權(quán)等基本原則。”秦暉說(shuō)。
上面這個(gè)故事是秦暉在他去年出版的《共同的底線》序言中提到的。在這本書(shū)中,秦暉試圖在思想、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等方面的話題中尋找共同底線,論證堅(jiān)守底線的意義。為什么被法國(guó)人“忽視”或是“漠視”的底線問(wèn)題,在中國(guó)會(huì)有特別的意義?秦暉認(rèn)為,在歐美這些國(guó)家,底線是一種實(shí)然狀態(tài),除了勒龐這樣的極端情況,爭(zhēng)論各方在底線上已經(jīng)達(dá)成了默認(rèn)的共識(shí),因此分歧也只不過(guò)是在共同底線基礎(chǔ)上的分歧,不會(huì)演化成你死我活的斗爭(zhēng),但是中國(guó)尚未形成共同底線,而有意義的爭(zhēng)論應(yīng)該建立在共同底線之上。
底線為什么重要?論爭(zhēng)的目的在于消除分歧,解決問(wèn)題,但假如沒(méi)有底線,話語(yǔ)上的論爭(zhēng)就可能變成肉體上的斗爭(zhēng),解決的不是問(wèn)題,而是提出問(wèn)題的人。秦暉認(rèn)為,沒(méi)有底線的共識(shí)是靠不住的。他舉例說(shuō),假設(shè)在一個(gè)可以把“異端”燒死的神權(quán)體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討論什么樣的共識(shí)?所謂的中庸是指基督教與儒教間的中庸,還是火刑制度與廢除火刑、承認(rèn)信仰自由間的“中庸”?如果是基督教與儒教間的教義問(wèn)題,沒(méi)有宗教自由如何討論這樣的問(wèn)題?
忽視底線的論爭(zhēng)還可能遮蔽了真問(wèn)題。上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中國(guó)公共話語(yǔ)圈論爭(zhēng)的思想資源,主要來(lái)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與社會(huì)民主主義,分別對(duì)應(yīng)國(guó)內(nèi)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自由派提倡私有化,強(qiáng)調(diào)市場(chǎng)的作用,減少?lài)?guó)家干預(yù)。而新左派則認(rèn)為放任自由會(huì)破壞平等,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政府的角色,在二次分配中更多地將財(cái)富分配給弱勢(shì)群體。兩者之間是否有共同的底線?秦暉提出,不論要實(shí)現(xiàn)自由市場(chǎng)的“交換”還是二次分配的“慈善”都要首先反對(duì)權(quán)勢(shì)的“搶劫”—也就是通過(guò)權(quán)勢(shì)損害他人利益獲取自己利益的行為。
離開(kāi)這個(gè)“不搶劫”的共同底線,討論政府是否要汲取更多財(cái)政或是國(guó)家是否應(yīng)該當(dāng)甩手掌柜,不提供或少提供社會(huì)福利等公共產(chǎn)品,就可能成為假命題。因?yàn)榧偃绮荒芗s束政府權(quán)力,政府汲取更多財(cái)政后,也未必會(huì)用在社會(huì)福利上;而政府撇清責(zé)任之后,卻還是可能收不住伸入民眾腰包的手。因此秦暉說(shuō):“比如你主張一個(gè)責(zé)任大權(quán)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張一個(gè)權(quán)力小責(zé)任也小的政府,但我們要的都是權(quán)責(zé)對(duì)應(yīng)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那種權(quán)力大到不受制約、責(zé)任小得不可追問(wèn)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
當(dāng)?shù)拙€尚未建立,一些本是為了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的論爭(zhēng)即使有了結(jié)果,后果也可能是南轅北轍的。秦暉提出過(guò)一個(gè)“尺蠖效應(yīng)”的理論。左派支持?jǐn)U大政府角色,擴(kuò)大國(guó)有部門(mén),以服務(wù)于社會(huì)福利,促進(jìn)平等;右派支持?jǐn)U大市場(chǎng)角色,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兩方面都是出于好心,但在一個(gè)權(quán)力不受約束的國(guó)家,不管采用哪方面的政策,都可能辦成壞事。政府可以先采納左派意見(jiàn),從私人手中收羅財(cái)產(chǎn),壯大國(guó)有部門(mén),但因?yàn)闄?quán)力不受約束,國(guó)有部門(mén)的利益就可能落入權(quán)貴的腰包,而不是投入社會(huì)福利。政府也可以采納右派意見(jiàn),將國(guó)有部門(mén)“市場(chǎng)化”,但是不受約束的權(quán)力下,市場(chǎng)化過(guò)程不可能公正,獲益的還是權(quán)貴。這樣的政府就像尺蠖這種爬行蟲(chóng)一樣,它的身體不論是伸還是縮,最終都是向著中飽私囊的方向前進(jìn)。只有當(dāng)權(quán)力受到約束,政府權(quán)責(zé)一致之時(shí),這種局面才能避免。因此秦暉認(rèn)為,建立底線才是中國(guó)現(xiàn)階段的真問(wèn)題。
近些年來(lái),秦暉頻繁和不同立場(chǎng)不同理念的學(xué)者進(jìn)行討論、辯論,反復(fù)闡發(fā)他關(guān)于共同底線的思想。秦暉始終最為關(guān)注的是底線的上下之爭(zhēng),而不是立場(chǎng)的左右之爭(zhēng)。在一次與左派學(xué)者韓德強(qiáng)的對(duì)話中,他說(shuō)自己根據(jù)共同的底線既批評(píng)過(guò)左派,也批評(píng)過(guò)右派,兩邊因此都批評(píng)過(guò)他,并因此分別把他劃入對(duì)方陣營(yíng)。雖然媒體上一般稱(chēng)秦暉為自由派學(xué)者,但是他倒不介意自己被劃入哪方陣營(yíng),也不介意成為“左右公友”還是“左右公敵”,因?yàn)椤拔也⒉皇钦停恍枰懞檬裁慈恕薄?/p>
這種超然于立場(chǎng),一心注視底線的態(tài)度,與他早年的經(jīng)歷不無(wú)關(guān)系。秦暉出生在城里,但是15歲那年就在“文革”中下鄉(xiāng)“插隊(duì)”,在廣西一個(gè)偏遠(yuǎn)的山村當(dāng)了9年“農(nóng)民”。因此秦暉后來(lái)考上研究生后,就把農(nóng)民作為主要研究對(duì)象,把農(nóng)民問(wèn)題當(dāng)作“自己的問(wèn)題”。現(xiàn)在有些人傾向于把城市和農(nóng)村對(duì)立起來(lái),比如說(shuō)城市的發(fā)展是以犧牲農(nóng)村為代價(jià)的,又把一些城市問(wèn)題歸結(jié)為太多農(nóng)民工擁入城市。而秦暉早年提出,城里人和農(nóng)民實(shí)際上面對(duì)著共同的問(wèn)題,他們都同樣不自由,都不過(guò)是“共同體的附屬物”,因此改革的目標(biāo)不應(yīng)該是在城鄉(xiāng)之間重新分配利益,而是要將城鄉(xiāng)人員都從具有依附性的共同體成員轉(zhuǎn)變成具有個(gè)性的自由人。秦暉在不同話題上始終強(qiáng)調(diào)共同底線的意義,便是這種超越立場(chǎng)的思考模式的延續(xù)。
《共同的底線》出版后,獲得了各種榮譽(yù),發(fā)表獲獎(jiǎng)感言時(shí),秦暉連用幾個(gè)“常”來(lái)描述自己,“在下一介書(shū)生,有平常心,做尋常人,講正常話”。沒(méi)有底線的社會(huì)不會(huì)是一個(gè)正常社會(huì),共識(shí)無(wú)處生長(zhǎng),分歧無(wú)處安頓,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秦暉,以及這個(gè)時(shí)代其他真誠(chéng)地在為這個(gè)國(guó)家尋求底線、堅(jiān)守底線的學(xué)者,實(shí)際上是用底線為思想與言論建構(gòu)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沒(méi)有這樣的城邦,當(dāng)人們向著理想進(jìn)軍之時(shí),思想的論爭(zhēng)必然會(huì)在權(quán)力與利益的糾葛中,要么迷失方向,要么硝煙彌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