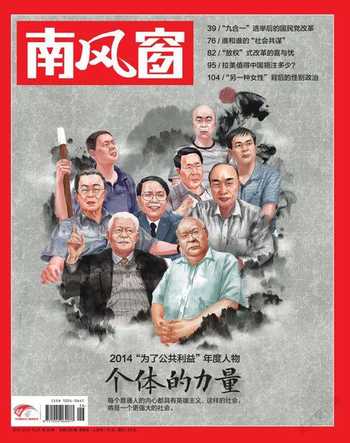2014,“放權”式改革的喜與憂
譚保羅
2014年,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啟動之年,改革二字,無疑是這一年中國經濟的主題。
2013年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規劃了中國新一輪經濟改革藍圖,而接下來的這一年則被各方給予“厚望”。高層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決心有多大,改革障礙有多大,以及改革道路有多曲折,這一年的變化會給出部分答案。
這一年,中國第一次在官方話語系統中將GDP增長的數據限定在“7.5%”的上下浮動,中國經濟正式進入重質量,而不光看速度的“經濟新常態”。此外,各方面的經濟改革幾乎是齊頭并進式推進,金融改革、國企改革、資源價格改革等老大難問題再次啟動。
和30多年前的那一場改革相似,2014年啟動的本輪改革主要模式也是“放權”。民營銀行的放開、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出發點都是簡政放權,擴大準入。但不能忽略的現實是,世易時移,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部業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早已不同于30多年前,“放權”式的改革并不能包治百病。
人們總說“歷史會驚人地相似”,時隔35年,兩輪經濟改革路徑的確存在某些明顯的共通之處。
2013年12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修訂了《公司法》,新法將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2014新公司法”共修改了12個條款,將公司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取消了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這是一次最明顯不過的“放權”式改革,并由此啟動了2014年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

時間回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各大城市,創業熱情同樣高漲,于是國家拋棄了所謂“資本主義尾巴”的說法,鼓勵返城青年作為個體戶在城市開門創業,啟動了中國企業群體的一次大復興。
本次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同樣推動了創業熱情,至少從數據看是樂觀的。統計顯示,推進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后,最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國內新增注冊公司顯著增加,改革半年時間內,新登記的市場主體659.59萬戶,同比增長15.75%。
但不能忽略的問題是,市場主體新注冊的熱情并不一定說明了市場的繁榮和經濟的堅挺。
當下,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已逐漸被國內外人士所完全接受。2011年,中國GDP增速為9.2%,2012年,降至7.8%,2013年,為7.7% 。對于2014年的中國GDP增速,大多數機構都把預測數字定在了7.4%至7.5%的區間之內。換言之,GDP“保八”的游戲在2012年結束之后,并未有過“溫和調整”,而是直接向下跌去。
在數據之外,更應看到本質的問題。對當下中國來說,產能過剩、消費不足這些問題已是老生常談。它們只是現象,更深層的問題是權力或者說行政手段的介入,破壞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機制。廣受詬病的過剩產能,其伴隨的必然是投資的不斷加碼,其背后又是廉價資金的運用,以及金融市場風險定價機制的形同虛設。
金融體系的最大問題是,大部分金融資源都是以權力或者“關系”來調配的,所以才會不計后果地涌入“鐵公基”和那些收益率極低的領域。可喜的是,所有人都認識到調配扭曲的癥結是管制,于是中國開始逐漸推動了金融改革,從2014年年初的民營銀行申報熱開始,民間資本都像打了雞血,紛紛上書請辦銀行,準備從金融管制開放的大餐中分羹一杯。
事實上,金融改革可看作價格改革的一部分。所謂價格改革,幾乎是中國30多年改革歷程中從未缺席過的主題。改革開放之初,普通中國人最憎惡的腐敗問題莫過于價格“雙軌制”,比方說,很多“官二代”會從權力部門拿到低價的商品配額,然后轉手到市場賺取一筆巨額差價。
而如今,這場價格改革仍是一場未竟的改革。30多年來,資金、土地、能源等領域價格改革都沒有真正完成。價格改革的停滯,直接導致了生產性要素的價格無法市場化,其價格沒有市場化,便永遠都有尋租的空間。更要緊的是,直接破壞了企業生產鏈條的“公平性”,更直接在經濟體中形成一個背靠權力“收租”的群體,高利貸放貸者、有“關系”的地產商、周濱之類的“民營”能源巨頭都是此中人。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普通中國人的創業艱難,并非因為中國人缺乏商業的智慧,而是背負著太重的“租金”。
經濟增速下滑,其本質是“政府公司化”發展模式正在走向窮途末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必然需要真正的公司群體。實際上,中國經濟當下最不缺乏的便是資金,真正的好公司一定不會缺乏投資,也不會在乎那幾萬元的注冊資本。因此,即便修改了《公司法》,放開市場準入,只要“租金”的問題沒有改變,中國人的創業熱情很快便會被新一輪的經濟形勢變動打得七零八落。
中國“有經濟而無企業”之憂,何時能解?
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是解藥嗎?
2014年11月,在浙江烏鎮出席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介紹,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四家企業進入全球互聯網公司十強。看起來,中國已經成為互聯網產業的強國。
一直以來,中國的“四大行”、“三桶油”等“特許經營”企業長期雄踞世界500強榜單,但它們并不能讓中國人驕傲。而互聯網企業的數據則足以讓中國人興奮,因為這個行業看起來體現了市場“公平正義”的自由價值,大企業和好企業也體現了這個國家在該產業的真正實力。
2014年年底,在紐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超越了3000億美元,遠超過了美國最大的電商企業亞馬遜,也超過了亞馬遜和另一家電商巨頭eBay公司的市值總和。權威統計數據還顯示,2014年,中國大陸地區網民已增長至6.32億,而到2015年,這個數字將超過8.5億。換言之,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還將因為網民技術膨脹而迎來新一輪發展。
但一個有趣的問題是,2014年的中國經濟,“新經濟”和“舊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謂冰火兩重天。“舊經濟”好壞的最直接體現莫過于股市,A股在經歷長期低迷之后,終于在年底迎來一輪暴漲,散戶紛紛重操舊業。但遺憾的是,幾天之后,A股便進入暴跌。沒有好企業,光靠高杠桿的融資,怎么能撐得起股市的長期繁榮?
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旨在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意見》的精神和此前半年公布的三中全會決議完全一致,是決議的具體化。按照《意見》的精神,中國將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拓寬企業和居民投融資渠道,以此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股市是企業的股市,企業質量是市場好壞的根本。因此,《意見》圍繞提高上市公司質量這一目標,提出了諸如履行好信息披露義務、規范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行為、鼓勵建立市值管理制度、開展員工持股計劃等措施,希望以此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運營質量。不過,上市公司的質量靠的必然不是一紙文件,而是根本的改革。這個改革不光在于股市的監管,也在于整個企業營商環境的脫胎換骨。
“新經濟”的好和“舊經濟”的不好,其存在都扎根于中國現有的營商環境。以電商巨頭為例,其運營的重要邏輯是中小商貿企業“地租”成本太高,而影響普通消費產品定價過高,導致普通中國人無法去商場消費。而電商則解決了這個問題,物美價廉的商品,它們其實意味著電商巨頭“拿走了”商業地產商的蛋糕,分給了中小商貿企業和網購者。王健林和馬云持續幾年的“豪賭恩怨”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新經濟”,并非中國經濟的“解藥”。中國的電商巨頭,其市值能夠超越美國同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兩國的營商環境存在極大差異。這個差異造成了“新經濟”的火,也造成了飽受各種“租金”困擾的“舊經濟”的冷。而互聯網經濟在中國的火爆程度早已近乎夸張,這并不完全是好事。
對后發國家來說,35年是一個里程碑,似乎也是一個“坎”。1961年,現任韓國總統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執掌韓國的軍政大權,1962年制定“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韓國經濟從此進入了快車道。1996年,韓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差不多在35年的時間里,韓國加入號稱“世界富國俱樂部”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式由發展中國家變為發達國家。
但這個國家很快為其“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付出了代價。在這個模式之下,國家通過金融、稅收等措施,以舉國之力支持幾家大企業搞研發,打造外向型經濟。這樣做雖然短時間內打造了一批世界級企業和品牌,但其負面效果不容忽視。
經過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底,韓國的人均GDP從1996年的1萬多美元下降到了6000多美元,縮水40%。危機之前,韓國全國的金融公司為2103家,金融危機后,僅存在一半。韓國的發展,其癥結之一也在于其資源,尤其是金融的配置并不完全靠市場,而是靠政策的傾斜,那么危險必然會臨近。
對中國而言,由于巨大的母國市場的存在,以及高儲蓄率的“金融保險效應”的原因,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看起來不大,但內部和外部的金融風險亦不能等閑視之。
除GDP增速的下行之外,另一個數據的變動也不容忽視。在12月初,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出現了不小的下跌,跌近6.1855元,刷新了2014年7月23日以來的近4個多月低位。
人民幣走軟的原因,固然有美國退出QE政策影響,但更大程度上必然是內部經濟變動在本幣比值上的反應。曾經,強大的“中國制造”奠定了人民幣長期升值預期的基礎,而如今,人民幣貶值預期已若隱若現。
可以說,不論從內部還是外部經濟環境來看,中國經濟改革勢在必行,并且步伐必須加快。但從目前來看,改革并不是那么輕松。
金融改革一直被認為是新一輪改革的重心,而銀行業改革更是重心的重心。公眾普遍認為,銀行機構的多元化是銀行改革的必要路徑,因此,民營銀行被寄予了極高期望。但遺憾的是,監管最終只批準了5家民營銀行,而在2014年,更有參與試點的民營企業“退出”了民營銀行的試點。
民營銀行熱冷卻的背后,是真正的金融改革遲遲沒有推進。一方面,中國的銀行供給早已屬于嚴重過剩的階段,盡管中國人的個人負債率很低,但企業部門的負債率已經“趕英超美”,這背后都是銀行的“產能過剩”。民營資本對進入這個“產能過剩”的領域,其實存在著嚴重的信心不足。
更重要的是,銀行改革的“雙輪”必然是機構的多元化和利率的市場化,但后面一個“輪子”的改革受到了阻礙。目前,監管部門放開了貸款利率的限制,但并未放開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管制意味著國有銀行仍然可以獲得低成本的儲蓄資金。在這種模式下,顯然無法改變目前這種普通國民對金融機構和大國企進行“利率補貼”的格局。
在這種格局下,國有銀行必然會把更多的資金以廉價貸給國有企業。事實上,按照統計數據,中國銀行業超過一半的貸款都貸向國有企業,國企不計風險成本的資金運用模式才是利率市場化的最大阻礙。
那么,改革國企吧。2014年,可以說是國企的改革年,目前的改革方式主要是混合所有制,在央企陸續推出各種改革方案之后,地方國資部門也紛紛出臺各種文件,形成了一波國企改革的熱潮。但實際上,改革僅僅停留在宣傳上,真正參與改革的民間資本并不多。
時間回溯到1978年,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年頭,當年國家財政收入僅1132億。2013年,中國的財政收入129143億元,比1978年增長100多倍。35年的時間內,中國的國力的確得到了提升,但經濟發展的質量,尤其是企業的質量才是未來改革應該關注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