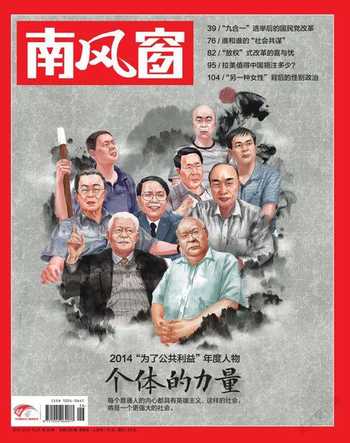西方和俄羅斯各自在糾結什么
方亮

俄政治上的寡頭屬性讓其經濟發展呈現出“逆淘汰”特征。
2014年10月中旬,當普京決定從俄烏邊境撤出軍演部隊、烏東部二州的親俄武裝也開始撤出重型武器,烏克蘭危機一度迎來實質性緩和。但緊接著,烏東部分離二州的選舉引起基輔當局的“經濟封鎖”,而普京在G20峰會上受到西方壓力提前退場,以及美國副總統拜登造訪基輔暗示將加強對俄制裁,則標志著圍繞烏克蘭的大國博弈重新加劇。
盤點這場持續一年多、造成4000多人喪生(其中1/4死于9月5日停火協議生效后)的危機,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烏克蘭“二月革命”是一場內部因素占主導的革命,革命的資金、人員、意志主要來自烏克蘭寡頭集團。這是在西方已“不愿”迅速接納新成員的背景下,烏克蘭的單方面“主動”西進。結果普京的板子打在了烏克蘭身上,賬卻算在了西方頭上。12月4日,普京在國情咨文中宣布,不允許西方以肢解南斯拉夫方式對付俄。
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初,“新冷戰”之論頻出,但外界清楚這種說法并無“冷戰”一詞本身的含義。奧巴馬2014年3月公開表態稱,俄羅斯只是一個地區大國,他還重復了2012年競選時的判斷:美國的“頭號敵人”為“基地”組織而非俄羅斯。任憑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在美國國會上高喊“我們不能靠毛毯打勝仗乃至維護和平”,歐美當時卻連武器都不打算提供給基輔。
在西方看來,盡管自今年夏季烏克蘭沖突加劇以來,俄軍機在歐洲的活動大幅增加,但莫斯科并沒有能力跟歐美演繹一出真正的“冷戰”大戲。盡管莫斯科吞并了克里米亞,并在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支持親俄武裝,北約卻在威爾士峰會上將“紅線”劃在了波羅的海國家至東歐一線。奧巴馬在烏克蘭危機高潮背景下訪問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宣稱對塔林、里加、維爾紐斯的保衛“與保衛柏林、巴黎、倫敦一樣重要”;北約峰會拿出的最“硬”舉措則為:在東歐北約成員國部署快速反應部隊。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歐洲國家普遍對這場危機不堪其擾的背景下于8月23日訪問了基輔,規勸波羅申科在克里米亞和東部二州的問題上展現靈活性。雖然德國原則上仍站在烏克蘭一邊,這一動作卻使得默克爾的角色在邏輯上已經類似于“慕尼黑陰謀”中的張伯倫和達拉第,而克里米亞則早已被國際媒體比作蘇臺德區。此中區別只在于一點:希特勒侵略前,英法兩國對捷克負有盟約義務,而如今西方卻并不對烏克蘭負有這種責任,2008年對格魯吉亞同樣如此。
西方對烏克蘭危機“隔岸觀火”,縱容了危機的惡化。用公投來決定是否獨立并加入俄羅斯的決定,是克里米亞議會在30名“不明身份”武裝人員劫持議會大樓后做出的,而且整個公投過程都在此類武裝人員參與下進行。雖然很難說武裝人員的存在壓制了真實的克里米亞民意,但它畢竟為公投的合法性打上了問號。而且,烏克蘭獨立后克里米亞半島一直存在獨立傾向,卻未能成功,此番俄羅斯發力它便迅速獨立。俄羅斯還將其收入囊中,創下冷戰后為數不多的吞并他國領土的先例。
但歐美選擇了綏靖和軟制裁。奧巴馬3月接受采訪時坦承,華盛頓對莫斯科束手無策。但實際上他的潛臺詞是,美國不會理會俄羅斯的胡鬧,也不會下血本幫助烏克蘭。歐美顯然在綏靖俄羅斯,只不過這種綏靖無法與二戰前英法對納粹德國的妥協等量齊觀。當從荷蘭出發的馬航班機在烏東部上空被擊落、“俄羅斯潛艇”的跡象出現在瑞典海域、法國石油巨頭猝死莫斯科機場等意外事件紛至,歐美的輿情就給俄羅斯貼上了疑似始作俑者的標簽。而10月末歐洲8國及北約緊急攔截26架逼近不同國家領空的俄羅斯戰機,更是將這種不信任暴露無遺。
當面對希特勒之流時,西方都有足夠的擔心作為理由來讓他們采取“割肉飼虎”式的綏靖政策,或是奉行絕地反擊的“杜魯門主義”。但是,普京的俄羅斯卻沒有能力讓西方產生制度面臨存亡威脅的恐懼感。
2014年9月初,奧巴馬剛在塔林放出了北約將保衛波羅的海三國的承諾,俄方武裝人員就上演了一出“跨境至愛沙尼亞抓人”的好戲,其間手榴彈爆炸引發的硝煙讓愛邊境百姓恐慌地以為戰爭又打響了。這種恐慌也體現在9月19日烏克蘭、波蘭、立陶宛三國防長簽署的組建聯合武裝的協議上。然而,對于更廣大范圍的國家來說,這次越境襲擊及其后續動作可能引起的是天然氣斷供、貿易利益的部分喪失、國家聯盟關系中的責任義務履行等,這些都無法直接引發存亡之憂。
對當下國際體系來說,俄羅斯所能帶來的最大威脅或許在于它的核武庫。但是,對于經歷過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而且在1985年的日內瓦收獲了“核戰爭中沒有贏家”這一美蘇共識的世界來說,普京及其將軍們動輒拿核武器說事的動作最多也就是給國內民眾提氣的“漂亮話”。當然,說到核武器,不得不說俄侵占烏克蘭領土確實給國際核體制帶來了潛在影響。因為蘇聯解體之際烏克蘭主動放棄了存留于自己境內的蘇聯核武器,并換得幾大國對自己進行安全保護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雖然這一承諾并不具法律約束力,但眼下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受侵犯透露出一個信號:主動放棄核武器的落得個悲慘下場,主動擁核的卻至今堅挺。這對國際核體制自然是一種動搖。
但俄羅斯行徑所帶來的這種“核威脅”畢竟是間接的、潛在的,它同樣無法引起普遍的恐懼。而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角度來看,俄羅斯當下這套政治制度及其邏輯難以向民主國家輸出。普京營建的以大資本壟斷為特征的威權政治制度是當下許多國家都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后蘇聯轉型國家,但它作為一種現狀卻并非各國追求的理想發展模式。俄政治上的寡頭屬性讓其經濟發展呈現出“逆淘汰”特征,使它從數字(去年GDP增長僅為1.3%,今年因受制裁和下半年油價暴跌30%而很可能負增長)到內容(日益墮為單純的能源經濟發展模式,重工業、航天等傳統優勢產業萎縮)都缺乏實際吸引力,遑論讓國情不同的國家效仿。
所以,俄羅斯無力輸出一種發展模式,就像當年布爾什維克不得不放棄世界革命一樣。普京亦希望以警惕法西斯復活和反美為意識形態基礎在國際間尋找朋友,他將相關表述列入了2014年7月金磚國家峰會通過的《福塔雷薩宣言》,但卻像前些年在南美部署戰略武器等嘗試一樣,未能取得影響和理想結果。普京也搞金元外交,但他在烏克蘭花數百億美元收買亞努科維奇政府中止加入歐盟轉而加入歐亞聯盟的動作卻引發了一場“二月革命”,弄巧成拙地“賠了盧布又折代理人”。普京基于傳統經濟聯系拉上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建立的歐亞聯盟,如今也因為它對“小兄弟”烏克蘭的動武而出現了較強的離心趨勢。最近普京找上了北約成員國土耳其,揚言要放棄經保加利亞向中南歐供氣的“南溪”管道項目,轉而考慮在土耳其和希臘邊境建立一個天然氣中轉站,但埃爾多安總統對此并未表態。
歐美自然因普京頭疼,西門子等德國大公司、荷蘭的食品供應商、法國的軍工企業、芬蘭貿易商,都因為出口利益損失而向本國政府施壓,勸后者不要繼續制裁俄羅斯。但歐美政府認為普京的反制裁其實鬧不起大風浪,他們不痛不癢地祭出了經濟上施壓卻不做軍事應對的戰略。直到烏克蘭總統前不久宣布將在幾年內就加入北約舉行公投,北約最高軍事長官才姍姍來遲地稱已制定援助烏軍的計劃。
“它們不想迫使俄羅斯做出政策上的改變,而是希望實現政權更迭。”俄外長拉夫羅夫11月22日的這番發言,揭示了莫斯科的深層擔憂所在。拉夫羅夫警告說,俄羅斯與歐洲的關系不會再“一如往昔”。
回溯二戰勝利后,蘇聯亦曾有過“少干涉”歐洲內政的打算。當時斯大林希望保留與美國的戰時盟國關系,為此同意了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占區舉行自由選舉,結果親蘇政黨大敗。這場失敗讓莫斯科在柏林的蘇占區再也不敢搞計劃中的公正選舉,而代之以讓西歐心驚膽戰的強權擴張政策。
如今,西方面對普京的俄羅斯時不再感受到恐懼,但俄羅斯對西方的恐懼感則存留至今。二戰前后,蘇聯忙著侵占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比薩拉比亞、在東歐建立共產主義政府、拒絕從伊朗北部撤軍、向土耳其提出領土和建立軍事基地要求等,以獲取所謂的安全屏障。現在普京認為,俄羅斯正遭受來自北約的安全威脅,而烏克蘭則要融入西方,莫斯科只能以向西擴張來換取緩沖空間。
就像遏制理論提出者、美國外交家凱南所言,支配俄羅斯人外交選擇的是它傳統的不安全感。而這種不安全感在遭遇“制度認同度低”這一現實時加倍爆發出來。普京有一種頑固的觀念:自己和自己營建的體制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而任何從民意角度對體制提出的質疑和動搖,都同外部入侵一樣應當被視為敵對因素加以處理。普京打擊反對派的系列審判“巴洛特諾耶案”一直在持續,不久前將最后一位受審者判刑;他還借烏克蘭危機的大背景將反對派指為“叛國者”、“第五縱隊”。
如果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俄羅斯人的不安全感僅限于領土威脅,那么在那之后制度安全問題所帶來的恐懼與日俱增。無論是反法同盟還是神圣同盟,沙皇追求的都不僅僅是領土安全,更有對皇權制度的維護。此后歷任俄國領導人都在這種深深的制度不安全感驅使下進行力量伸張。從沙皇到早期布爾什維克,從斯大林到普京,這種制度不安全感一以貫之。所以并不奇怪,前蘇聯末代總統戈爾巴喬夫早前在德國發言支持普京的烏克蘭政策,并指責華盛頓“需要一個可以讓他們到處插手的局面,無論結局是好還是壞,他們不關心”。
實際上,奧巴馬上臺后主動重啟了美俄關系,拒絕了繼續推進小布什時期的反導計劃,而且美國也不再力推北約東擴。可以說,奧巴馬主政時代,俄羅斯早些年最為擔心的兩個安全關切都已經至少暫時被美國解決。但是,普京還是對克里米亞祭出了侵占手段,理由卻仍是北約對俄造成了安全威脅。
可以說,驅動普京強力伸張的仍是不安全感,但它并非來自領土安全,而是來自對制度安全的擔憂。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是,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的戲碼幾乎和如今“二月革命”一模一樣,普京當時卻沒有做伸張動作。一個根本原因是,當時俄羅斯受惠于能源經濟正經歷著高速增長,如今俄羅斯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普京所建立的這套制度承受不了地緣上的大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