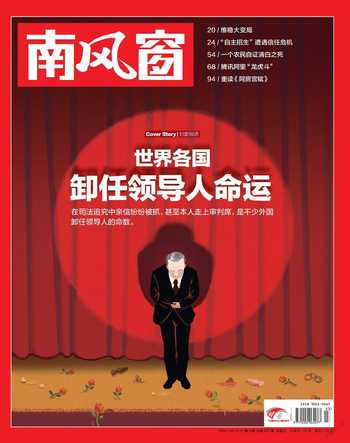法國作家奧利維耶·羅蘭:我寫作,因感覺自己站錯了時代
何蘊琪
奧利維耶·羅蘭,法國著名作家,1947年出生于巴黎西南面的布洛涅-比揚古市,童年曾經在塞內加爾生活。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文學、哲學),曾經為《解放報》和《新觀察家》擔任自由撰稿人。1983年發表第一部小說 《未來現象》。1994年創作小說 《蘇丹港》,同年獲得費米娜獎。2002年創作小說《紙老虎》,把對五月風暴的回憶以更加個人化的小說形式呈現,獲得2003年法蘭西文化大獎。2008年出版小說《獵獅人》,以19世紀印象派畫家馬奈的作品為題材,還原了濃墨重彩、情感與際遇皆跌宕傳奇的19世紀。他還創作了一系列的游記及文學評論。2010年榮獲法蘭西學院保羅·莫朗大獎(獎勵其所有著作)。
2014年1月初的一個夜晚,廣州老城區小巷幽深的一幢兩層老別墅里坐滿了年輕人,身材高大、魁梧的奧利維耶·羅蘭在翻譯家孟湄陪同下出現在博爾赫斯書店,落座于店內一張貝克特的黑白照片前—對此,他笑言“很有壓力”。這天晚上的講座主題為《現代小說的寫作與閱讀》,而第二天晚上,他將繼續應法國領事館邀請,在方所書店進行名為《小說家與他的時代》的講座。
這位67歲的老人步伐矯捷、沉穩,他曾在法國五月風暴中擔任一個極左翼組織的軍事領袖。2002年,他將這段經歷寫入小說《紙老虎》中(中譯本已由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譯者孟湄),并獲次年的法蘭西文化大獎。據羅蘭自己說,《紙老虎》的書名靈感來自于毛澤東的名言—“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革命與政治,并非這位小說家最醉心的話題,他關心的,是在時光的流逝下,怎樣重新講述一個特殊年代的故事,從而讓生命從狹窄走向寬闊。羅蘭毫不諱言,《紙老虎》中許多情節來自他對親身經歷的回憶,包括五月風暴時期,他所參與的左翼組織的非法地下活動,他說,在這些回憶中包含了兩種情感:對那個時代的同情,和對自己的嘲諷。
五月風暴所處的1960年代,世界上不同地區的許多革命運動彼此呼應,但對于包括羅蘭所在的西方年輕人來說,“革命”更像是一個隱喻:“在那個時代的詞匯里,我們都不講‘我’,只講‘我們’,我們對于個人、個人的利益,是否成功,是否有社會地位,都無所謂。我們實際上冒著很大風險去從事我們的理想和事業,也知道可能會被警察抓進監獄,或者挨槍子死去。我們很團結,互相聲援,一種戰友般的感情。后來,社會的潮流把這些很好的東西都掃蕩一空。”
當羅蘭提起筆寫下這段經歷時,時間已經過去了30年,他認為,那是他一生中最浪漫、最有意思的生活,但也充滿著矛盾。他自言當時包括自己在內的年輕人對歷史、文化毫無了解,“有整整7年時間沒有讀過一本文學書。”他說,“我們自己的觀點特別狹隘,老是排斥別人,對別人沒有任何包容。一個年輕人懷里揣著槍,走在大街上,做那些明明法律不允許的事情,覺得自己是豪情萬丈的綠林好漢。我們不學習,不愿意回家,不愿意遵守法律,對自己過分的狂妄自信……我們常常到法國周邊的工廠去,深深相信每個工人都比我們要有知識、對世界的理解比我們更高深。”
羅蘭說,他很喜歡博爾赫斯說過的一句話,“隨著每個生命走向垂危,每個事情的無限性隨之消失,文學有一個重要的使命是把這些事情留下來。”在羅蘭看來,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曾經如此燦爛,如此有趣,或者如此值得嘲諷,也應該用文學把它留下來。“只有靠文學能讓我們的生活無限擴大、無限寬闊,比如我們能看到在我們生活之外,有無限的生命在延續。”
歷史和時間,在這位經歷了革命風暴又踏入另一條河流的作家看來,從半個世紀前直到現在,有一個質的轉變。“從那個時代到現在,世界變化太大了。那個時代,我們從歷史中可以得到靈感,未來也有一個燦爛的光輝—全人類的解放、全人類的幸福,而相對來說當下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時間是一個沙漏,從過去走向未來,我們在中間守望。但與此相比,世界發展到今天已經完全不一樣,歷史被認為是毫不足道,未來也沒有什么輝煌燦爛的前景讓人類為之奮斗,反而當下成為巨大無比的東西,大家都重視在當下好好活著,珍惜現在。”
因此羅蘭認為,我們的時代在時間上有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小說重要的不是講故事,而是它提供很多東西給人思考,它不一定能提供答案,但至少能讓人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它帶著讀者經歷、穿越時間的河流,在經歷的過程中去思索。就如同今天已經沒有人能理解五月風暴時的左翼青年,連他自己也好奇,當初怎么做過這樣的事情。“我想把這些經歷都記錄下來,讓后面的人知道。我們常常忘記,今天是從過去來的,今天的法國人這樣生活,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延續。”

對時代的思考始終自覺貫穿羅蘭的寫作,他承認,是對時代的不滿和不適應,讓自己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如果我的生活很優裕、很中產,大概決不會寫作。我和很多作家、很多藝術家一樣,我們感覺自己不是在應該在的位置上,或者說感覺自己站錯了時代,待錯了地方,才去寫作”。
值得一提的一個小細節是,這位小說家為了準備中國之行的文學講座,八易其稿,講稿一早就已翻譯好,分段投影在屏幕上,讓人對其中的嚴謹細致肅然起敬。在講稿中,羅蘭提出了一個問題:對人物命運的關注也即故事情節,是否真能把我們引向關于小說有意義的方向?
羅蘭提出,小說獨有的讓人如癡如狂的東西,并不因情節的披露、懸念、高潮而被左右,而是另有自己的邏輯—真正超越一切地位的,是小說的風格。正如福樓拜所強調的,“詞語和句子應當是構成小說真正內容的材質,有如木料或石材。”詞語的藝術,結構的藝術,應當先于故事的藝術。小說如同萬有引力,追求的是閱讀的震驚,那種讀者經受的“癱瘓和魔力”。
這樣的震驚過程是如何發生?“讓讀者驚嚇無比的地方,是從那些被施加組合、張力、扭曲、壓迫的詞語中,從那些爐火純青的、達到福樓拜所言‘無法被改變’的詩句里,一個有力量的、意想不動的形象噴射而出,如一束火苗。地點和時間構成了它的舞臺,僅此而已。一部大小說就是這些爆發的總和。”當讀者忘記故事情節的曲折,文字故事的機器便會倒塌,但在那里,從語言創造中誕生的那種“仍舊存活、依稀發光”的東西,就是一本書的能量所在。
羅蘭用兩種形象來比喻兩種不同的小說形態。一種小說,或者說傳統小說,可比喻為電影,小說的構思如同一個大劇本的展開,“劇終”兩個字在最后一幕出現。而另一種小說,或者說現代小說,可以被想象為一個藝術館展廳,里面琳瑯滿目掛了很多幅繪畫,瀏覽沒有方向,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可以從一個門進去另一個門出去,一切完全是偶然,但畫與畫之間有一種聯結,一種回響。
因此,現代小說并不從歷史和情節、或者并不從歷史和情節里獲得它的偉大力量。與這種現代寫作相對應的,是小說的現代閱讀,它是慢的、深度的、細致的,與其說它關注情節動態,不如說它在意一個場面的力量和神秘,那是語言的力量和神秘。當一位年輕讀者問到,這樣的現代小說如何與詩歌的目標區分出來時,羅蘭說,情節并不是小說的靈魂,但情節仍然和小說的每個部分都是相關聯,形成架構的,這一點和詩歌不一樣。“詩歌可以作出一個樂句,但一個樂句和一個奏鳴曲或者一個交響曲還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