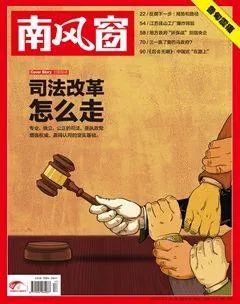地方政府“環(huán)保戰(zhàn)”劍指央企
譚保羅

從2013年中石油高管被查開始,中央在央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幾乎就在同時,地方政府也對央企刮起了“環(huán)保旋風”,污染罰單、水土補償標準提高和廠區(qū)搬遷要求成為了地方的“利劍”。
在1990年代的財稅金融和國企改革之后,壟斷央企成為了地方政府加大當?shù)赝顿Y和發(fā)展經(jīng)濟的重要幫手,其對后者也一直具有強大的“議價能力”,而遭遇了來自于地方政府的大幅度“反彈”,這還是頭一遭。一向?qū)ρ肫蟀佾I殷勤的地方為什么敢于對央企“說不”?
一方面,隨著經(jīng)濟下行以及國企反腐的推進,央企的投資增幅開始放緩,對地方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的貢獻也在縮小;另一方面,在經(jīng)濟下行期,地方政府開始更關(guān)注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稅收,而央企特殊的中央集權(quán)經(jīng)營模式固然可以提供GDP,但真金白銀的貢獻往往不多。因此,雙方曾經(jīng)的利益同盟開始出現(xiàn)裂痕。
再從公平正義的視角來看,央企已經(jīng)獲得“國家特許經(jīng)營”的優(yōu)勢和低廉的金融資源,因此不應在環(huán)保標準上再享受特殊待遇,而是要在承擔環(huán)保成本方面起到表率作用。但也不能忽略,中國更多的環(huán)境破壞并非來自于央企的傲慢和自私,而是來自于別處。
利益集團是個抽象的概念,而央企巨頭則是現(xiàn)實的存在。
2013年9月,曾當過中石油董事長的蔣潔敏因涉嫌嚴重違紀,在國資委主任的位置上被中央調(diào)查,成為繼原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總經(jīng)理高嚴和原中核工業(yè)黨組書記、總經(jīng)理康日新之后,改革開放以來第三位被查的“中央委員”級別國企高管。
不久之后的10月,陜西榆林市當?shù)胤ㄔ簝鼋Y(jié)了中石油旗下產(chǎn)油大戶長慶油田分公司的22個銀行賬戶,直接導致7萬余職工短期內(nèi)無法發(fā)工資。事件起因是,長慶油田未繳納兩年零9個月、共8.5億元的水土流失補償費和滯納金,被榆林水土保持監(jiān)督部門告上法庭,隨后輸?shù)袅斯偎荆虼吮环ㄔ簭娭茍?zhí)行。
差不多同時,鄰近的甘肅省慶陽市也加入了對長慶油田的“討債”,當?shù)卣J為之前的補償標準過低,需要重新制定標準。當?shù)厝耸繉Α赌巷L窗》記者透露,長慶油田在慶陽共有7個采油廠 ,都是處級單位。油田為增大產(chǎn)量,采取了“注水采油法”,對地下水的消耗量極大,當?shù)厝罕姺Q之為“以水換油”。此外,慶陽境內(nèi)8條較大河流也都因為采油而受到污染,其中部分河流水質(zhì)監(jiān)測僅為5類。
環(huán)境的代價和油田的繁榮形成了反差。長慶油田被稱為“西部大慶”,目前原油產(chǎn)量占全國的1/10,天然氣產(chǎn)量占全國的1/4,還是中國陸上最大產(chǎn)氣區(qū)和天然氣管網(wǎng)樞紐中心。長慶油田的工作區(qū)分布在陜、甘、寧、內(nèi)蒙古等多個省(區(qū)),這也意味著遭受環(huán)境“傷害”的地區(qū)很廣。
慶陽市一位官員對《南風窗》記者透露,長慶油田去年之所以和陜西榆林打官司,主要是陜西制定的補償標準較高。油田擔心如果在陜西交了高標準,油田工作區(qū)的各地都會跟風提高補償,這樣每年會多出數(shù)十億的成本。
有分析稱,長慶油田和西部地方政府的“糾紛”由來已久,而本輪紛爭則是地方政府利用央企反腐,特別是石油窩案被查的特殊時點,希望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某種程度上說,凍結(jié)油田賬戶這樣的事情屬于特殊時點的“偶然事件”。
但“偶然”背后是“必然”。在我國,地方對企業(yè)征收水土補償費用的標準主要參照1991年的《水土保持法》,該法給予了省級人大充分的立法自主權(quán)。其中,水土流失補償費的具體補償標準,由省來確定。隨后,這個標準成為了各省招商引資的重要籌碼,部分地區(qū)往往樂于采取較低標準來吸引企業(yè)進駐。
不過,資源企業(yè)對地方環(huán)境的破壞是始料未及的,地方政府面臨很大的環(huán)境修復壓力,乃至于“民怨”沸騰。于是,地方開始積極修改法規(guī),希望將補償標準上調(diào)。以上慶陽市官員便向《南風窗》記者透露,甘肅省的補償新標準有望于今年年底前出臺。屆時,將以新標準向油田征收補償。
據(jù)其透露,另一家央企華能集團下屬的新莊煤礦仍拖欠慶陽超過100萬元的水土保持費。按照以前的標準,央企采煤企業(yè)僅需在煤礦建設期交納補償費用,在開采期則不需交納。這種模式“顯失公平”,因此越來越不被當?shù)卣邮堋0凑赵鹊臉藴剩肫竺旱V對慶陽的生態(tài)補償費僅為建設期的數(shù)百萬元,而按照鄰省陜西的新標準以出煤量征收,還可在開采期每年獲得數(shù)千萬的補償。
“反彈”并非環(huán)境承載能力本身就差的西部地區(qū)獨有。在2013年的“11·22”中石化黃島爆炸重大事故之后,在東部經(jīng)濟大省江蘇,南京的石化央企也不斷收到當?shù)氐摹爸鹂土睢保惺聦俚慕鹆晔軌毫ψ畲蟆5刂聊壳埃鞍犭x南京”仍未有定論。
在本輪紛爭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以前,針對央企的環(huán)境處罰和補償要求一般都是由國家環(huán)保部開出,盡管背后可能是地方政府的“意志”。而地方環(huán)保部門直接向央企“挑戰(zhàn)”則是新鮮事。2013年,中石化安慶分公司在應急處置一次停電事故時出現(xiàn)短時間黑煙排放,因此被安慶環(huán)保局開出一張9萬元的罰單。盡管錢不多,但這被認為是開啟了地方環(huán)境部門直接“挑戰(zhàn)”央企的先河。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地方政府對央企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和央企反腐大潮的展開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這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做了正確的事。但從現(xiàn)實利益的角度看,從招商“橄欖枝”到環(huán)保部門的“罰單”,這個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背后是央企和地方作為利益同盟,正在因為經(jīng)濟形勢的轉(zhuǎn)變而開始出現(xiàn)裂痕。
何種市場主體可以和地方結(jié)成利益同盟?其決定因素在于這個主體能給地方政府帶來多少資金。在1990年代的分稅制和金融改革之后,國家的財政和金融資源實現(xiàn)了向中央的過度集中,在中央對地方正常的財政轉(zhuǎn)移支付之外,還形成了另一套“民間轉(zhuǎn)移支付”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的主角之一是房地產(chǎn)商,另一個則是央企。
地產(chǎn)商的運作模式,可以看作是從國家控制的銀行中通過開發(fā)貸和個人購房貸獲取資金,投入地方的城市開發(fā)。而這一點,央企同樣可以做到,而且其獲得的資金成本可能更低。央企直接在地方投資巨型項目,瞬間便為地方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增加了分量。尤其在那些缺乏明顯中心城市的區(qū)域,比如西北地區(qū),地產(chǎn)商資金進去很少,因而央企成為這套“民間轉(zhuǎn)移支付”系統(tǒng)的主角。
事實上,在中西部很多欠發(fā)達省區(qū),當?shù)孛磕旯嫉漠數(shù)仄髽I(yè)10強或50強,大部分都是駐地央企。公開數(shù)據(jù)顯示,2002年末,央企的資產(chǎn)總額為7.13萬億,而2013年末,這個數(shù)字超過了35萬億元,約為11年前的5倍。這一時期,央企投資其實成為地方經(jīng)濟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沒有央企進駐,有些地方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根本沒法看。”中西部一位長期參與經(jīng)濟規(guī)劃制定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的廳局級官員對《南風窗》記者分析,比如央企建一個廠 ,建廠會創(chuàng)造GDP,而建廠之后,每年的產(chǎn)出又可以計算GDP。對著眼于“數(shù)據(jù)政績”的地方官來說,引入一家央企便一勞永逸,是任內(nèi)最大政績。
但不能被忽略的問題是,央企對地方經(jīng)濟的拉動有著天然的缺陷。首先,地方官的短暫任期和央企的“利益集團化”,使得雙方的“交易”往往存在不對等。簡而言之,地方官只管任內(nèi)的招商引資和GDP政績,做的都是“一錘子買賣”。但央企卻日益形成穩(wěn)固的利益集團,后者會更多考慮“長期利益”,因此時常會簽“不平等條約”。
在中西部部分省市,當?shù)卣畬σ恍┤腭v央企竟只會一次性征收環(huán)境補償費用。再以石油化工企業(yè)為例,其在油區(qū)一直有增產(chǎn)動力,因此會采取諸如“注水采油法”等節(jié)省自身成本,但把環(huán)保成本轉(zhuǎn)移給地方的辦法。但地方政府當初的協(xié)議卻并未把環(huán)保成本的上升考慮在內(nèi),而是把問題留給“下一任”。在這種情況之下,地方和央企的環(huán)保“糾紛”必然爆發(fā)。
除了“不平等”帶來的“同盟”不穩(wěn)定之外,央企對地方經(jīng)濟的拉動也逐漸呈現(xiàn)出疲態(tài)。一直以來,央企對地方經(jīng)濟的拉動很大程度是通過其資產(chǎn)的擴張來實現(xiàn)的,但擴張并非沒有邊界。《南風窗》記者查閱國資委網(wǎng)站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2009年,中央企業(yè)資產(chǎn)總額比上年增長19.5%,2010年的數(shù)字是16%,而在2013年,擴張增幅下滑更明顯,僅為11.7%。
再以營業(yè)收入為例,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中央企業(yè)營業(yè)總收入增幅分別為6.4%、32.9%、20.8%、9.4%和8.4%。可以看出,在2010至2013年,央企營業(yè)收入增幅都高于GDP,它們無疑是中國拉動經(jīng)濟,應對金融海嘯的主力軍。但增速放緩在所難免,2014年上半年,中央企業(yè)營收同比僅增長5.1%,遠低于上半年7.4%的GDP增幅。
盡管央企營收和地方GDP增長并不存在直接關(guān)系,但分析認為,央企投資和增長放緩導致其在拉動地方經(jīng)濟增長方面的貢獻比例逐漸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央企在地方的增長拉動“系統(tǒng)”之中的“系統(tǒng)重要性”開始降低,矛盾便會顯露。不過,這個維持數(shù)十年的利益同盟之所以出現(xiàn)明顯“裂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當經(jīng)濟下行,地方政府的關(guān)注點開始悄然轉(zhuǎn)變。
顯而易見,真金白銀總比GDP重要,特別在經(jīng)濟下行的時點,稅收比什么都讓人揪心。以上廳局級官員告訴《南風窗》記者,目前,央企進駐地方之后的稅收主要面臨一個“身份問題”。如果央企在地方設立的是子公司,那么大部分稅收都要交給地方,但現(xiàn)實中,很多央企為加強北京總部的控制,采取了“中央集權(quán)模式”,即只在地方設立分公司,這也意味著交給地方的稅收很少。
2010年,陜西省政府的高層官員就公開抱怨,省屬國企延長石油采掘1噸油交給地方的稅收為680元,而央企中石油采走1噸油只交給地方60元,兩者相差10倍。該官員還說,央企在當?shù)剡M行天然氣開發(fā),開發(fā)1立方米氣留給地方只有1分錢,而地方氣源地要用氣,必須去中央要指標。
除了稅收和GDP的不匹配,環(huán)境污染更可能危及一些地方的最重要的現(xiàn)金流來源— 樓市。在沿海部分城市,由于主城區(qū)地段開發(fā)殆盡,政府開始向海濱或者江濱要地,但石油石化企業(yè)多建在水邊,因此它們嚴重影響了地價。在地方土地出讓金下滑,并且沒有“好地”可賣的情況下,對央企施以環(huán)保壓力,即便不能讓央企搬走,也可以改變地方政府在稅收、投資等方面對央企“議價能力”較差的局面。
事實上,地方政府對央企的“議價能力”較差,很大程度在于部分央企正逐漸成為利益集團,其背后“樹大根深”。根據(jù)公開報道,地方對央企的環(huán)保問責,主要發(fā)生在十八大召開之后,特別是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其中諸如“凍結(jié)賬戶”等手段也主要是出現(xiàn)在央企反腐大潮推進之后。因此有分析認為,此前雙方相安無事,并不排除部分地方官員“畏懼”央企背后的強大力量。
央企固然強大而傲慢,但換個角度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的污染源主要都是來自于中小企業(yè),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遠比向央企要環(huán)保成本難。一直以來,地方政府對中小企業(yè)的環(huán)保問責不足很大程度在于腐敗。
《南風窗》記者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僅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以來,地方落馬的環(huán)保局官員已超過20人,地區(qū)范圍涵蓋了中西部和東部沿海,其中不少都是主掌當?shù)丨h(huán)保權(quán)杖的廳局級。以敢于對央企“叫板”的江蘇省為例,近年來,該省環(huán)保領(lǐng)域職務犯罪發(fā)案數(shù)量逐年上升。統(tǒng)計顯示,2009年該省立案查辦環(huán)保領(lǐng)域職務犯罪僅6人,2010年升至20人,2011年為30人,2012年為40人。從查辦的案件看,具體表現(xiàn)在監(jiān)管人員收受賄賂,對企業(yè)排污放任不管,有的甚至偽造檢查報告。
“央企要管,但中小企業(yè)和民企更‘唯利是圖’,監(jiān)管更不能松懈。”以上廳局級官員對《南風窗》記者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