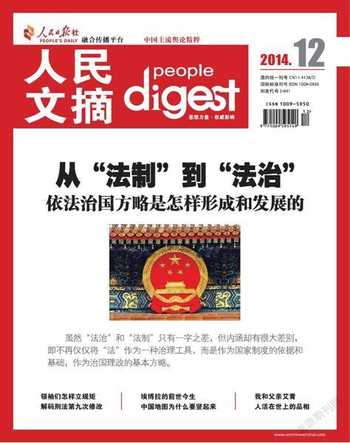古代也有“吃空餉”
洪振快
最近,媒體連續曝光數起“吃空餉”事件,如福建龍巖市“九年吃空餉公務員”、重慶萬州“官二代吃空餉兩年”、湖南永州“數百教師吃空餉”等,使得“吃空餉”現象再次成為熱議話題,“吃空餉”也成了新詞條。
“吃空餉”并非最近才有的現象。早在1999年,媒體就報道人口僅33萬的國家級貧困縣寧夏同心縣,吃財政飯者1.1萬人,超編2800多人,有拿工資不上班的“掛職干部”,也有僅10歲的“娃娃干部”“書包干部”,甚至有四五歲的“學齡前兒童干部”。十多年來,“吃空餉”報道不絕,可見頑疾難治。
追究“吃空餉”的語源,“餉”本意指軍糧,引申為軍人的俸給。所以,“吃空餉”本意是指軍官虛報兵員冒領軍餉。在二十五史中,未出現“空餉”這個詞。但在清代的官方文書中,有“空餉”一詞。在行政領域,中國古代的確存在“不上班但是可以領工資”的現象,但并沒有類似同心縣那樣嚴重的情況。中國歷史上特別是明清時代,地方財政的管理極為嚴格,其整飭有序出乎我們現在的想象。
不妨舉一個例子。
據同治十年纂修的《合江縣志》(該縣位于長江上游,隸屬四川)記載,該縣吃財政飯的公務人員,正式編制包括:知縣一名,年薪45兩,養廉銀600兩;典史一員,年薪31.52兩,養廉銀80兩;教諭、訓導各一名,年薪各40兩;稟生(縣學學生)20名,共64兩;衙役之類的縣政府辦公人員,包括門子、皂隸、馬快、轎傘扇夫、仵作、膳夫、捕役、門軍、禁卒、更夫、斗級、倉夫等共68名,工食銀每人每年6兩,共408兩;民壯8名,每人每年工食銀8兩,共64兩;鋪遞兵6名,每人每年工食銀6兩,共36兩;救生船水手12名,每人每年支銀7.2兩,共86.4兩;還有用于春秋祭祀文昌廟、社稷壇等用銀每年66兩。總計財政支出1560.92兩,其中吃財政飯的共118人,工資1494.92兩。當然,如果遇到有閏月的年份,稟生、衙役等要加補一個月的工資。
這就是說,清代的州縣吃財政飯的人很少,一個縣只有一百來個人,而財政支出明確,財政紀律嚴格,工資的來源也清楚:比如養廉銀共680兩出自火耗,救生船水手工資86.4兩是鹽庫給錢,因為設置水手的目的是負責鹽船在江上的運輸安全,其余大部分出自地丁銀。當地稅收中留用為工資的在財政制度中叫“存留”,其余都要上交,稱為“起運”。
清代地方財政收支制度非常嚴格,運行效率很高。這種財政制度也有弊端,主要是地方財權太小,很多地方公共服務沒有財政支持。但其好處是,因其執行的剛性,扼制了財政支出的混亂,“吃空餉”之類的現象就沒有了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吃空餉”普遍存在于當時的軍隊中。軍隊與地方的差別,主要是地方管商民,負有征稅的職責,其腐敗表現為征稅時的攤派和多征,地方官場對這部分財富進行再分配;而軍隊沒有征稅權力,收入靠國家財政撥款,所以其腐敗主要是平時通過虛報兵員、戰時虛報軍用物資耗費實現的。因此,“吃空餉”成為軍隊的常見貪腐手段。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1838年,禁煙派官員黃爵滋在奏折中說:“糧多冒領,則有餉無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愛仁則向皇帝奏稱,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兩萬一千余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可見當時軍隊中“吃空餉”現象之嚴重。
古代軍隊的“吃空餉”,與當下“不上班但是可以領工資”的現象,盡管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共同點,即財政的混亂和低效率。公共財政本來應完全用于公共服務,但“吃空餉”卻使公共財政支出轉化為個人私利。
當下中國財政制度的缺陷,是行政成本過高,導致用于公共服務目的的財政支出不足。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財政支出不夠的負擔轉嫁給民間,致使教改、醫改、房改等變形。
行政成本過高,既與行政機構膨脹、人員龐雜、人浮于事有關,也與“三公”消費嚴重、“吃空餉”屢禁不絕等現象有關。因為養了太多的人,耗費了太多的財政資源,導致本該用于公共服務的財政資源被壓縮、擠占。要改變這種現象,必須讓財政真正回歸到公共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