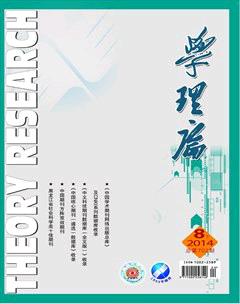管仲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
王秋霞
摘 要: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化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在文化和思想學術的發展上真可謂百家爭鳴,辯家鵲起,創造了輝煌的先秦文化,對后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管仲就生活在這個時期,他的法家倫理思想和道德倫理思想也被后人所傳頌,這些都與他生活的環境、個人境遇有很大的關系,他的倫理思想對當今中國夢實現也是有深遠影響,我們應該以歷史的角度去看古人的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關鍵詞:管仲倫理思想;法治思想;道德倫理思想;價值影響
中圖分類號:B82-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4-0026-02
管仲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的著名人物。在先秦諸子著述中有《管子》一書存世。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法家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后代。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被譽為“圣人之師”和“華夏文明的保護者”。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伙經商失敗,后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于士”。《戰國策》、《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左傳》等都有記載他的生活傳記,《論語》、北宋蘇洵的《管仲論》對管仲的事跡做出了分析和評價。
一、管仲倫理思想產生的背景
政治經濟方面,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為平王。鑒于鎬京殘破,又處于犬戎威脅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鄭、秦、晉等諸侯的衛護下,遷都洛邑,建立了東周。據《左傳》記載,春秋時共有一百四十多國。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齊、晉、楚、秦、魯、宋、鄭、衛、陳、蔡、吳及越等國。春秋時期,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時已名存實亡,“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進入了一個動亂的時代。動亂的局面,給周邊少數民族以發展的機會。齊國在今山東省的北部,是東方一個大國。它地處海濱,擁有豐富的漁鹽和礦藏,從太公開始,就“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到了春秋年間,農業、手工業,特別是冶鑄、紡織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公元前685年(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即位,任用管仲為相,積極改革內政。管仲從“富國強兵”的目的出發,在整飭舊制的基礎上,對各項制度加以改進。
文化方面,春秋時期歷史社會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許多思想家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當時的社會變革,發表不同的主張,周之季氏,北有孔孟,南有老莊,截然兩方思潮循時勢而發展,而墨家毗于北,農家毗于南,如驂之靳焉。法家之言,以道為體,以儒為用。韓非子實集其大成。而其源頭則濫觴于孔老學說未立以前之政治家,是為管子。根據齊地人少地薄,不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加上又有得天獨厚的魚鹽資源和有經商的傳統,種種條件使齊不發展商業都不行。所以太公“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經濟、政治、軍事活動范圍大大擴展,已遠遠超出禮的儀式規范,時代迫切需要制定各種標準來統一人們的行為,重新規范社會秩序。如社會生活中的度量規定,軍事戰爭中的賞罰標準,官員的晉級和降處等,大都超出了禮的約束限制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法治思想逐漸形成并傳播。
二、管仲主要的法治倫理思想
管仲的思想在《管子》一書中有記載,有些內容是他自己整理的,還有一些是其后人整理的,但都體現了他的思想。在眾多的先秦思想家中,大多沒有管理的經驗,孔子56歲才當上魯國的大司寇,代理宰相職務,為時三個月;孟子雖曾在齊國被尊為上大夫,只不過是個空發議論的虛銜而已。其他如墨子、韓非等更遠離廟堂。由于缺乏實際從政經驗,因此他們的言論或流于空疏迂闊,或限于偏激片面。管仲位高,身居相位,齊桓公尊為仲父,君臣相得,言聽計從,親密無間。從政四十年之久,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國家治理經驗,利于克服其他思想家的空疏、偏激、片面的觀點,管子的治國內容更全面、更實用。他認為法具有制度、標準和刑罰三層意思。首先,法用來指涉國家所設立的憲律制度,這種意義上的法又常稱為法制、法度。《管子》說:“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于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于官則為法,施于國則成俗(《法禁》)。”法由官府頒布制定,實際上也就是成文法。其次,法是一種標準。《管子·七法》:“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尺寸是長短的標準,繩墨是曲直的標準,規矩是方圓的標準,斗斛、角量是容量的標準,這些都稱之為法。國家統治的法,也是一種標準,它是明斷是非曲直的標準。再次,法是一種懲罰措施。法設定以后,人們就應該遵守,否則也就失去了其作為表儀、制度的意義,為此就要以刑罰來保證其實施。《管子》中的《立政》中提到:“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可見,國家和諧也是管仲追求的最高目標。他認為和睦團結就能協調,協調就能一致,協調一致就能無敵于天下。他認為禮法互補,也就是法治和禮治是可以相互補充的。一方面,仁義禮樂的推行要靠法律來保障,《任法》“君臣不用禮儀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法治有助于道德教化的推行;但另一方面,僅僅依刑重罰,還不防止人民做壞事:“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對君主而言,一方面,禮與法同可作為治國之“儀表”:“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明法解》)。”只是對象稍有不同。另一方面,禮法還同是君主論功酬勞的手段。《君臣下》說:“故其(人君)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叁伍相得而周舉之。”再一方面,英明的君主能注意內行法而外行禮,《形勢解》所謂“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這一思想實際上吸取了商鞅一派的法治思想以及儒家的德治思想,經過綜合揚棄,得了道德教化和法律制裁不可偏廢的結論。
三、管仲主要的道德倫理思想
他的道德體系是“禮、義、廉、恥”。《牧民》篇:“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禮”要求人們嚴格遵守封建等級秩序,“禮不逾節”;“義”指循禮而不自進,即不以不正當的方法謀取利實祿;“廉恥”則是關于守身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惡”是說不隱蔽壞事;“恥不從枉”是說不姑息邪枉之事。四者之中,禮義是對行為的約束,廉恥指內在的情操。他認為禮有八經。“八禮”即上下、貴賤、幼稚、貧富的尊卑等級秩序。“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管仲學派認為,這個秩序是亂不得的。《五輔》“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這與儒家的五倫要求大體相同。知禮的目的是維護等級制度。管仲學派對禮的論述與儒家殊途而歸,所不同的是:管仲學派強調外在的規范制約,儒家強調內在的認同內化,方法不一樣,根本目的相同。“義”是人們行為的準則。“義有七體”,《五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孝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戮。纖嗇省用,以備饑饉。孰■純固,以備戰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以此規定個人、社會和國家正當行為的準則。這七方面的前三方面,是完整意義上的道德要求,后四方面實際上是臣民對國家的義務。廉即純潔清高之意,“廉者,清不濫濁也(《周禮·小宰注》)。”清白不污,純正不茍即為“廉”;能辨別是非,舍利取義,是謂“廉明”;能自我檢束而不貪求,即為“廉儉”,《淮南子·原道訓》云“廉猶儉也。”“廉”為德目,最根本的是要在取予之間,重道義去邪心,嚴格自檢自束。這種人格,孟子稱為“廉士”。“恥”即發自內心的羞惡之德性。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人有自我反省而有羞惡之自覺,即謂知恥,故“恥”重在自恥。《孟子·盡心上》:“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不能夠沒有羞恥,從沒有羞恥到懂得羞恥,才能夠無羞恥。《孟子·盡心上》:“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羞恥對于人至關重要,以奸詐多變為得計的人,沒有地方用得上羞恥。不因比不上他人而羞恥,怎么能趕上他人呢?故恥之真義,在自覺于羞惡,以此作為行善去惡的內在動力。
四、管仲倫理思想的影響
管仲對倫理學最大的貢獻是他的道德基礎論。管仲認為,一定的道德觀念是與人們一定的生活水平相應的,這就是他的著名論點:“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他主張“禮”與“法”并舉的思想也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里,管仲已經自覺地認識到經濟對道德的制約作用,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不謀而合。禮與刑并重,是管仲倫理思想的一大特色。這一特色,后來成為中國兩千余年封建社會政治的主要特色。而在今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即可以看出管仲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得以運用。梁啟超曾說過:“中國最大之政治家,亦學術思想界一巨子也。”這些足以見得管仲的先進倫理思想對后世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馮友蘭的評價比較公允:“他是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變時期的改革、進步路線的創始人。李斯、韓非的法家思想,是這條路線在思想戰線上的發展的高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事業,是這條路線在政治路線上的完成。”
參考文獻:
[1]宣兆琦.圖說管子[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7.
[2]張連偉.《管子》哲學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團,2008.
[3]孔澤人.管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4]程國政.管子雅話[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5]余秉頤,李季林.法家金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6]姜正成.春秋名相管仲[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7]周俊敏.《管子》經濟倫理思想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出版,2003.
[8]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9]趙守正.管子的經濟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
[10]曹旭華.論《管子》的富國富民思想[J].管子學刊,1989(1).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