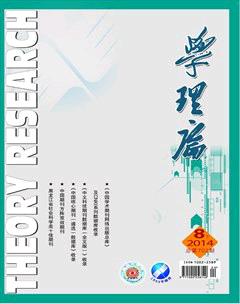從電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
王璐怡
摘 要:思維方式是溝通文化與語(yǔ)言的橋梁。思維方式的差異,正是造成文化差異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思維方式的差異本質(zhì)上是文化差異的表現(xiàn)。東西方屬于不同的文化體系,因而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東方人注重倫理、道德、直覺(jué),重和諧、意象、守舊;西方人注重自然、科學(xué)、技術(shù)、實(shí)證、求變。《刮痧》是由鄭曉龍導(dǎo)演的電影,講述了一個(gè)北京移民家庭在美國(guó)生活時(shí)發(fā)生的故事,以美國(guó)作為背景,以傳統(tǒng)中醫(yī)療法《刮痧》為切入點(diǎn),剖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從“倫理型”與“認(rèn)知型”、“整體性”與“分析性”、“意向性”與“對(duì)象性”、“后饋性”與“前瞻性”這四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解析中西方文化差異。
關(guān)鍵詞:思維方式;文化差異;刮痧
中圖分類號(hào):G12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4)24-0122-02
一、“倫理型”與“認(rèn)知型”
“倫理型”是指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側(cè)重反映人倫—政治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最重要的社會(huì)根基是以血緣關(guān)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其中“孝”是最基本的原則。這種道德信念延伸到社會(huì)組織中,衍生出“君為臣綱”,孝道轉(zhuǎn)化為治國(guó)之道。所以,判斷人的標(biāo)準(zhǔn)往往比較注重身份、地位、倫理、道德。
“認(rèn)知型”是指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文主義,主張個(gè)性解放,認(rèn)為個(gè)體是自由的,注重以自我為中心。判斷人的標(biāo)準(zhǔn)為注重個(gè)人的行為、表現(xiàn),注重個(gè)人奮斗,注重個(gè)人成就。
東方思維具有“倫理型”特點(diǎn),因?yàn)橹袊?guó)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huán)境、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和春秋戰(zhàn)國(guó)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哺育了儒家思想。儒家學(xué)說(shuō)建立在血緣宗法關(guān)系基礎(chǔ)之上,其思維的中心在于倫常治道,在于確立和論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zhǎng)幼有序。古代君主為了唯護(hù)君臣關(guān)系向來(lái)是推崇儒家學(xué)說(shuō),古代先哲以政治、倫理為視覺(jué)焦點(diǎn),以維護(hù)封建宗法制的倫理道德為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重倫理綱常,重道德修養(yǎng)。
西方思維具有“認(rèn)知型”特點(diǎn),因?yàn)槲鞣秸軐W(xué)家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應(yīng)與大自然和睦相處。西方智者們分析自然構(gòu)造,尋求物質(zhì)元素,重視本體論、認(rèn)識(shí)論和方法論,把自然科學(xué)看作是戰(zhàn)勝自然的一種工具。隨著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西方人從物質(zhì)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說(shuō)明其種種屬性,從而產(chǎn)生以實(shí)驗(yàn)為基礎(chǔ)的逐層深入的邏輯分析方法和種種推斷、證明、解釋的思維形式,造就了無(wú)數(shù)的科學(xué)理論和體系,形成了西方科學(xué)認(rèn)知型的思維。
在電影《刮痧》中大同替父承認(rèn)刮痧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維方式。電影中大同為了不影響父親辦綠卡而說(shuō)是自己給兒子刮痧,并且沒(méi)有因?yàn)楣勿鹗录?zé)備父親,反而設(shè)法隱瞞。這種行為體現(xiàn)了中國(guó)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視倫理綱常,父親在子女心中有絕對(duì)的權(quán)威,子女孝順父母,在中國(guó)人看來(lái)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當(dāng)爺爺?shù)弥约航o孫子刮痧引起了麻煩時(shí),獨(dú)自一人找到大同的老板昆蘭,用手語(yǔ)和圖畫向其說(shuō)明是自己給丹尼斯刮痧的,而不是大同。昆蘭無(wú)法理解大同為什么要說(shuō)謊,大同的妻子簡(jiǎn)寧一語(yǔ)道破:“因?yàn)槲覀兪侵袊?guó)人”。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guó)人深受群體取向價(jià)值觀的影響,思維上整體優(yōu)先,以群體的和諧、利益為重,注重親情和人情,父慈子孝。
二、“整體性”與“分析性”
“整體性”是指中國(guó)人處理事情時(shí)善于運(yùn)用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中國(guó)人的整體性思維注重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靠主體的主觀經(jīng)驗(yàn)和感受進(jìn)行分析論證。注重宏觀調(diào)控,定性把握,橫向聯(lián)系,群體共存,經(jīng)驗(yàn)積累。
“分析性”是指西方人在處理事情時(shí)傾向于運(yùn)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據(jù)嚴(yán)密的分析和邏輯進(jìn)行分析論證。注重微觀分解,定量分析,理論思辨縱向深入,個(gè)體獨(dú)立,科學(xué)實(shí)驗(yàn)。
在電影《刮痧》中對(duì)于刮痧是中醫(yī)療法還是虐待兒童的爭(zhēng)論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維方式。代表東方思維的中國(guó)文化依賴傳統(tǒng)經(jīng)驗(yàn)及形象的思維方式,而西方思維模式注重推理實(shí)證,講究理性與論證。在《刮疹》中,許大同在法庭上試圖對(duì)刮疹進(jìn)行解釋:“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中醫(yī)療法,中醫(yī)認(rèn)為,人體的七經(jīng)八脈,就像無(wú)數(shù)條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體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生命網(wǎng)絡(luò),氣在全身流動(dòng),氣沉丹田。”大同認(rèn)為刮痧是中醫(yī)治病的方式,通過(guò)刮痧所造成背部的刮痕是身體有疾病的表現(xiàn)。而法官等其他西方人只相信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不相信在背部進(jìn)行刮痧能治療肚子痛,而背部的刮痕正說(shuō)明這是一種虐待行為。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正是源于中西方醫(yī)學(xué)來(lái)源于不同的思想基礎(chǔ)。中醫(yī)學(xué)基本是建立在莊子的哲學(xué)基礎(chǔ)之上,《莊子·齊物論》中說(shuō)“天地與我并生,萬(wàn)物與我為一”,這是一種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天人一氣”、“萬(wàn)物一體”的宏觀宇宙觀。刮痧是中醫(yī)治療的方法之一,具有很豐富的臨床實(shí)踐性。神農(nóng)嘗百草的故事生動(dòng)地說(shuō)明中醫(yī)理論重體驗(yàn),輕理論;重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輕演繹推理;重解決實(shí)際問(wèn)題的技術(shù)方法,輕指導(dǎo)實(shí)踐的科學(xué)理論。而西方的哲學(xué)思想是實(shí)踐論,西方的醫(yī)學(xué)建立在科學(xué)哲學(xué)的思想基礎(chǔ)之上。西方的醫(yī)學(xué)注重生理學(xué)、病理學(xué)、解剖學(xué)的研究,傾向于運(yùn)用化驗(yàn)、透視、切片等先進(jìn)的科學(xué)驗(yàn)證手段。用西醫(yī)的理論來(lái)解釋中醫(yī)的理論是解釋不清的,因?yàn)槠渌枷敫春屠碚摶A(chǔ)是大相徑庭的。影片中爺爺不禁自問(wèn):“刮疹在中國(guó)幾千年了,到了美國(guó)怎么就說(shuō)不清楚了呢?”這體現(xiàn)了中醫(yī)的治病理念是崇尚“整體和諧”而西醫(yī)則注重運(yùn)用科學(xué)的、分析的、實(shí)證的方法。
三、“意向性”與“對(duì)象性”
“意向性”是指中國(guó)人在處理事情時(shí),總是會(huì)把情考慮在其中,親情、友情、愛(ài)情等等,以情作為判斷事物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理是定的而人情是活的,善于經(jīng)世致用的中國(guó)人總是能在處理繁雜的事務(wù)中運(yùn)用好“情”。
“對(duì)象性”是指西方人受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人文主義的影響,提倡人的個(gè)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以人為中心,所以形成了西方人反對(duì)以情感作為評(píng)判事物的標(biāo)準(zhǔn),而是以科學(xué)認(rèn)知為基礎(chǔ),以事實(shí)作為判斷事物的標(biāo)準(zhǔn),排除主觀因素而強(qiáng)調(diào)客觀因素。
在電影《刮痧》中昆蘭在法庭上沒(méi)有應(yīng)大同的要求做證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維方式。在電影中,大同請(qǐng)他的朋友昆蘭在法庭上替他做證,即使昆蘭是出版法方面的律師而非家庭法方面的律師,大同依然堅(jiān)持讓昆蘭替自己辯護(hù),按照中國(guó)人的觀點(diǎn),為朋友就得“兩肋插刀”,但是當(dāng)昆蘭看過(guò)丹尼斯背上的瘀痕后義無(wú)反顧地站到了證人席上,昆蘭選擇讓證據(jù)說(shuō)話,并沒(méi)有因?yàn)榇笸亲约旱呐笥讯咚酵鞣ā4笸J(rèn)為昆蘭背叛了自己,他憤而辭職,與昆蘭分道揚(yáng)鑣。在中國(guó),主體意向性思維從主體的需要和實(shí)用出發(fā),以人的倫理規(guī)范和審美情趣為標(biāo)準(zhǔn),以主體意向統(tǒng)攝客體對(duì)象,以價(jià)值選擇優(yōu)先于真假問(wèn)題,寓事實(shí)與判斷于價(jià)值判斷之中。正是這種價(jià)值判斷型思維,而非事實(shí)判斷型思維,具有明顯的主觀性和意向性。中國(guó)人認(rèn)為法律只適用于陌生人之間,家人和朋友之間進(jìn)行交往時(shí)一般只注重情理,至于法律法規(guī)可以根據(jù)情況適當(dāng)遵守。而在西方處理一切事物的標(biāo)準(zhǔn)就是要符合法律法規(guī),所以人們?cè)诮煌倪^(guò)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其行為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規(guī)的要求,這也就不難理解昆蘭為什么拒絕為大同做證了。中國(guó)儒家傳統(tǒng)以“人情”為依歸,人們?cè)谌饲榈南嗷ネ鶃?lái)中實(shí)現(xiàn)了物質(zhì)、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共享。而西方人往往是理智超越情感,公事公辦是他們的基本原則,即使對(duì)家人和朋友也要做到依法辦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西方人不講人情,沒(méi)有親情和友情,在電影中昆蘭親自去唐人街的中醫(yī)館嘗試了刮痧后在法庭上為大同做證,以自己身上看似像傷痕的刮痧痕跡為證據(jù)向法官證明了大同的清白,這不僅體現(xiàn)了昆蘭與大同之間的真摯友情,亦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在美國(guó)一切都以證據(jù)為依據(jù),這種做法在中國(guó)人看來(lái)可能不近人情,但卻從側(cè)面證明了美國(guó)是一個(gè)講求證據(jù)的法制國(guó)家。
四、“后饋性”與“前瞻性”
“后饋性”是指中國(guó)人具有“唯圣”、“唯書”、“唯上”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中國(guó)人崇古敬老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上重經(jīng)史、社會(huì)上崇祖先、心理上懷古舊和思想上好常惡變,求穩(wěn)怕亂。中國(guó)人善于總結(jié)前人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從過(guò)去了解現(xiàn)在并推知未來(lái),因而偏向于注重時(shí)間而非空間。
“前瞻性”是指西方人具有崇尚民主、自由、科學(xué)和理性思維的傳統(tǒng)。西方人不斷探究事物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對(duì)未來(lái)的發(fā)展善于提出預(yù)測(cè)和預(yù)言,進(jìn)而運(yùn)用預(yù)見(jiàn)、理性和科學(xué)信念,面對(duì)未來(lái),不斷提出假設(shè)、理論和方法,不斷探索、開(kāi)拓和創(chuàng)新。
在電影《刮痧》中大同當(dāng)著老板昆蘭打兒子這件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維方式。在大同打了兒子丹尼斯以后,大同的父親說(shuō)道“當(dāng)面教子,背后教妻”。這句話出自《朱子家訓(xùn)》:堂前教子,枕邊教妻,對(duì)癥下藥,量體裁衣。后來(lái)(清)吳獬著的《一法通》也有提到:堂前教子,枕邊訓(xùn)妻。所以爺爺對(duì)于大同打?qū)O子這件事并沒(méi)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yàn)檫@是經(jīng)歷幾千年從老祖宗那兒流傳下來(lái)的,是權(quán)威,是圣言。這正體現(xiàn)了中國(guó)人“向后看,立足于過(guò)去”的后饋性思維特征。而昆蘭不能接受大同所謂的因?yàn)榻o他面子而打了丹尼斯的說(shuō)法,文藝復(fù)興以后,西方人不再時(shí)興以圣賢之言作為論據(jù),較少引用前人的名言。西方人注重“唯真”、“唯實(shí)”、“唯理”、“唯法”。所以昆蘭認(rèn)為丹尼斯與保羅打架是孩子們自己的事情,與大人無(wú)關(guān),所以他不能理解大同的做法。
隨著全球經(jīng)濟(jì)化、一體化,中西方的交流愈來(lái)愈頻繁。在交流的過(guò)程中由于思維方式的差異,文化沖突油然而生,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從沖突到融合是一個(gè)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們要用寬容的態(tài)度和真誠(chéng)的心去感受文化的差異,彼此尊重信任,隨著深入的交流互動(dòng),我想因文化差異而引發(fā)的沖突會(huì)越來(lái)越少,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也會(huì)越來(lái)越融洽。電影的最后大同教丹尼斯講中文正暗示著中西文化正在走向融合,文化沖突也會(huì)逐漸被吸收。
參考文獻(xiàn):
[1]連淑能.英漢對(duì)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彭辰寧.從電影《刮痧》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J].河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5(1).
[3]彭如青.從電影《刮痧》透視中美文化差異與沖突:語(yǔ)篇系統(tǒng)觀[J].電影文學(xué),2009(15).
[4]李文慧.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看《刮痧》中折射出的中西文化差異[J].咸寧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7).
[5]韓楓.從電影《刮痧》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J].生物技術(shù)世界,2012(8).
[6]李佩君.從電影《刮痧》透析中西方文化差異[J].新聞傳播,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