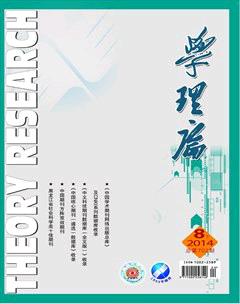論在我軍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的依據與意義
曾皓
摘 要:世界新軍事革命與我軍力量體系結構變革對軍事人才職業能力內涵特征提出了新的要求,國際法是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應當具備的職業知識。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是夯實強軍之基的客觀要求,是培養軍事人才的現實途徑,是提升軍人軍事能力的重要方式。
關鍵詞:軍隊;國際法;教育訓練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4-0092-02
世界新軍事革命與我軍力量體系結構變革對軍事人才職業能力內涵特征提出了新的要求,實現中國夢和強軍夢對軍事人才建設賦予了新的時代標準。面向部隊廣大官兵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對于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提升軍人人才職業特質、專業品質、創新素質有著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一、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是夯實強軍之基的客觀要求
習主席強調:“要牢記,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依法從嚴治軍,是古今中外治軍之道的精要所在。《韓非子》認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1]人們一般習慣地把依法治軍之“法”理解為與軍事有關的各種國內法規范。其實,這種認識并不全面。因為,依據法理學對法的分類,“法”可以分為國內法與國際法。相應的,我軍治軍之“法律依據”,也有國內法與國際法之分。其中的國內法規范主要包括我國的軍事法律、法規和規章;國際法規范則主要涵蓋與軍事有關的、我國締結或參加的一些國際條約。如日內瓦四公約及其議定書、《聯合國憲章》第51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有關登臨權、緊追權的條款等等。所以,我們所說的依法治軍,不但包括依據相關國內軍事法規管理部隊,還應包括依據對我國有約束力的國際軍事法規來治軍。此外,由于我國《憲法》第29條規定,軍隊要履行對內與對外兩方面的任務,對軍隊的法治也同樣應該包括兩個層次,即對內用法規制度規范部隊戰備、訓練、管理、保障等各項工作;對外遵循國際法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認識是行為的先導,學習是落實的前提。要真正做到依法治軍,就先要學法、懂法、尊法。誠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言,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關鍵在于培育治軍的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因此,要夯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這個強軍之基,軍隊就應當同時加強對國內法與國際法的教育訓練,引導廣大官兵學法遵法守法用法。
二、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是培育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的現實途徑
作為一名新型高素質軍事人才,在戰爭中,必須熟悉何種作戰方法與手段是國際法禁止使用的,必須能夠確定合法的攻擊目標,必須清楚評估其武力攻擊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在平時遂行多樣化軍事行動時,必須知道自己可以采用何種措施來合法、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因此,國際法是當代職業軍官必須具備的國際知識、專業知識。為了完善官兵的知識結構,提高他們的職業素質,軍隊自然應當自行組織或是依托院校,向指揮員與戰斗員系統講授國際法知識,讓他們熟悉武力使用法、作戰行為法、中立法和懲治戰爭犯罪法;并在部隊軍事訓練與演習中融入選擇攻擊目標、區分戰斗員與平民、管理戰俘、維護戰時群眾紀律等與戰爭法相關的訓練內容,以提高我軍官兵實際運用戰爭法的能力。另外,對于不同的軍兵種,依據他們在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中可能會遇到的法律問題,還應分別向他們傳授領土法、海洋法、空間法以及陸戰、海戰、空戰交戰規則。
熟悉與善用國際法,是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必須具備的職業技能。具體而言,由于在現代國際社會中,國際法一經確立,就會對政治、經濟、軍事等國際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為了在作戰中或遂行軍事行動中,取得戰略主動,獲取國際支持,并妥善處理戰后事宜,維護國家形象,基本上大多數國家在采取國際軍事行動之前,都會找到相應的國際法理論依據,以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次對外自衛反擊戰中都事先向國際社會說明了我國軍事行動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行使自衛權。而且,即便一國的軍事行動違反了國際法規則,這些國家也不會去否定國際法,而是想方設法去尋找國際法上的借口。例如,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政府就以國際法上的“集體自衛權”來為其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辯護。但實際上,這些案例是很難用自衛權來論證其軍事行動的合法性的。此外,現代國際法不但規定了個人刑事責任制度,還授權國際軍事法庭與國際刑事法院據此懲治那些因違反國際人道法或戰爭法而犯下戰爭罪行的個人。例如,二戰結束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分別懲治了德國和日本的戰爭罪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宣稱:“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人而不是抽象的實體所犯下的,因此,只有通過懲治犯下此類罪行的個人,才能使國際法的規則得到實施。”紐倫堡和東京審判后,聯合國大會決議確認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所包含的國際法原則。1950年,國際法委員會編纂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其中包括“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承擔個人責任,并因此應受懲罰”。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個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又有了新的進展。1993年的“前南國際刑庭規約”、1994年的“盧旺達國際刑庭規約”,1998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以及2002年成立的國際刑事法院,都標志著懲治戰爭犯罪的個人刑事責任不斷得到完善與健全[2]16,113。由此可見,一國軍事決策者在制訂對外作戰計劃時,必須要具備以下的職業技能:避免違反或有效規避相關國際法,以防止出現對其不利的國際局面;并制定相應的法律預案,以應對一些突發事件。
綜上所述,不同層次的軍事人才在履行使命任務時,如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策略、具體作戰計劃或是指揮相關軍事行動等等,都應當具備尋求法律依據、克服法律障礙、規避法律風險的知識與技能。這正如美軍原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在指揮海灣戰爭后所總結的:“法律方面的考慮對各級的決策都有影響。事實證明,在決策過程中,戰爭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軍要培養造就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就必須增強廣大官兵的國際法意識與思維,提高職業軍官運用國際法進行法律戰,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能力。
三、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是提升核心軍事能力的重要方式
2013年5月,習主席在聽取成都軍區工作匯報后指出:“我們講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但核心問題是打仗,打仗能力是軍隊的核心軍事能力,也是完成其他任務的基礎和支撐。”加強國際法教育訓練,能直接提升軍隊戰斗力,強化軍隊的核心軍事能力。
首先,學習國際法有利于我軍武器裝備建設。“打現代化戰爭,人還是決定性因素,但武器裝備的作用也決不能低估。”由于國際軍控條約對國家的武器研發使用都會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我軍通過加強國際法教育訓練,能讓我國軍方代表依據國際法在參與國際軍控談判、制定軍控機制時,反對與我國軍事戰略相左的規定,以防止軍控對我軍武器裝備的研制產生不利影響;修改或退出對我不利的軍控條約,依據我軍軍事戰略大力發展先進武器裝備。此外,我軍還可以在研究吃透現行國際法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現行軍控條約所不禁止的常規武器裝備;有效規避現行軍控條約的約束,研制先進武器裝備;利用軍備控制“代差”,搶先發展網絡、太空武器等一系列高新尖端武器。我軍還可以利用國際法限制其他國家違反國際法研發使用對我國不利,危害國際和平與穩定的武器裝備。
其次,學習國際法有利于我軍在戰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提升軍隊士氣。由于現代戰爭不單單是軍事對抗,還包括法律較量;如果我軍能夠在軍事斗爭或遂行多樣化非戰爭軍事行動中,利用國際法向國內與國際社會宣傳我軍軍事行動的合法性,揭露對方軍事行動的非法性,我軍就能利用《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集體安全體制等相關國際法規則,從政治、外交上打擊對手,使我軍得道多助,對方失道寡助,從而爭取戰略主動,爭取于我有利的戰略態勢。為確保打贏,爭得國內外輿論支持與法律支撐。
再次,學習國際法有利于我軍在新軍事變革中搶占先機,克敵制勝。外層空間、網絡空間等新空間已經成了新的作戰空間,但現行國際法既未規定在這些新作戰空間的交戰規則,一些傳統戰爭法規則也難以在新空間作戰中適用。例如,中立原則、區分原則,能否適用網電空間作戰,在網電攻擊中又如何遵守這些戰爭法規則;如何確定網絡攻擊的法律性質,是否可以對外國的網絡攻擊進行自衛,又能采用何種自衛手段,等等的法律問題,在現行國際法中都很難找到明確的答案。但又是新興軍事斗爭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一國能爭奪制定新作戰空間交戰規則的話語權,或是依據國際法理論做出對本國有利的法律解釋,無疑能直接提升軍隊的戰斗力。當前,一些軍事強國紛紛牽頭制定一些有利于該國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戰略的新空間作戰規則。如美國先后主導推出了《空戰和導彈戰適用國際法手冊》與《網絡戰適用國際法手冊》。這些國際法手冊,雖然目前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對于推動形成新作戰空間交戰法律規則將起巨大的指引作用,在將來甚至有可能成為國際習慣法,或是被編撰為國際條約。因此,加強對部隊的國際法教育訓練,研究新空間作戰法律問題,搶奪制定新空間交戰規則話語權,能為我軍在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中掌握軍事競爭戰略主動權,打贏未來高科技戰爭提供重要保障。
我軍在開展國際法教育訓練方面,有優良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基礎。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我軍就十分重視對官兵開展一些體現戰爭法基本價值的人道主義原則與交戰規則的教育。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我國陸續參加一些武裝沖突法條約,并積極進行裁軍與軍控談判,我軍更加重視戰爭法的教育訓練工作。而且,軍事院校通過多年努力,已經形成一支教授研究武裝沖突法的專家隊伍,產生了一批豐碩的教學科研資源,積累了一套豐富的教學經驗[3]29-30。部隊可以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與遠程網絡教學手段,依托軍事院校進一步加強國際法教育訓練。
參考文獻:
[1]吳長勝.戰斗力提升離不開依法從嚴治軍[N].解放軍報,2014-06-09(8).
[2]楊澤偉.國際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宋新平.我軍武裝沖突法教育訓練的特點[J].政工導刊,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