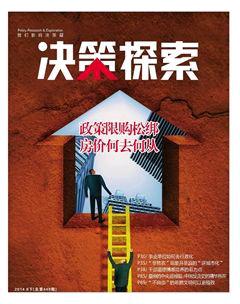從社會治理角度干預醫患沖突
房莉杰
近年來,中國醫患矛盾突出,暴力傷醫事件促使醫生群體集體發聲,甚至有人認為醫患沖突正在演變為兩個群體之間的“戰爭”。在我國,對醫生的不滿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醫生的逐利化傾向為大眾所詬病。隨著對醫生不滿情緒的增加,正面的醫患沖突開始出現,而在2005年前后,這種沖突升級為頻繁出現的“醫鬧”,近年來甚至出現非理性的暴力傷醫事件。針對醫患沖突,比較主流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是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從根本上杜絕“以藥養醫”和不恰當的醫療行為;二是依法嚴懲暴力傷醫者,以儆效尤。但即使上述兩點都完全做到,是否就能重建患者對醫生的信任?是否就能防止患者非理性行為的發生?答案仍是不確定的。因此,有必要對醫患雙方的行為和動機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醫生行為缺乏內部有效監管
毋庸置疑,目前我國醫患沖突的起源是醫生行為的失范。具體而言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醫生群體出現日益嚴重的逐利化傾向。因此,很多人提出鑒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應取消對醫生的激勵。不過這種觀點遭到駁斥,理由是醫療服務也是比較個性化、高風險的服務,如果沒有任何激勵,很難鼓勵醫生提高服務質量,更會產生推諉病人的現象,這對患者更不利。因此,任何國家,即便是實施全公立國家醫療體系的英國,都引入了一定的競爭和激勵,以促使醫生提高服務質量。然而,任何激勵手段都會使醫生產生相應的過度醫療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對醫生的監管就顯得異常重要。
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信息不對稱是經常發生的,尤其是對醫生這種專業化水平非常高的職業,普通民眾缺乏監管的專業能力,只能依賴兩種專業手段:一是外部監管,主要是通過政府和醫療保險機構對醫生的行為進行約束。一般而言,某種職業的專業含量越高,對其外部監管的成本也就越高,醫生職業自然也不例外。二是內部監管,即通過醫生的職業團體進行自我約束。一方面,醫生團體的成員都是由醫生組成,其專業性具有絕對優勢;另一方面,醫生團體也更有動力約束其成員的行為,從而保障群體大部分成員的利益。因此,這種內部監管的動力和能力更強,監管的有效性也更高。此外,由于醫生團體的存在價值是維護醫生群體的共同利益,因此醫生們也有意愿跟其簽訂“契約”并遵守其規定。在這方面,“美國醫師協會”的例子當屬典型,它是影響美國衛生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為醫生爭取利益的同時,對規范醫生行為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醫療服務商品化,使得市場激勵成為醫生行為的主要動力。但與此同時,政府監管卻有所欠缺。此外,也一直沒有形成真正的職業自治性質的醫生協會,即醫生是“原子化”的個體,不被職業團體保護,同時也不受職業規范約束。這種情況刺激了部分醫生通過自己的力量盡可能多地賺取利潤,即使其行為違背了職業道德。
缺乏專業的患者組織和社工組織給患者提供幫助
很多醫生認為,患者之所以對醫生不滿,是因為他們對醫生和醫療技術的期望值過高。而這背后隱含的是普通大眾醫學專業知識的缺乏。醫生和患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專業差距,從這個角度說,患者毫無疑問是弱勢者;加上處于患病狀態,患者及其家屬更會感到無助,因此迫切希望在心理上找到依賴。
這種依賴可以從兩方面獲得:一方面是醫生,尤其是家庭醫生。其中,家庭醫生通過與簽約家庭長期互動建立信任,了解患者長期的情況,幫助其選擇治療方案,是患者家庭最核心的專業支持者,同時也是心理支持者。另一方面是患者團體和社工組織,有相似病情的患者在社工的組織下互相分享經驗、互相支持,同時也可以作為患者利益的保護者。
在我國,患者也是“原子化”的個體,國內基本上沒有相應的患者組織和社工組織給患者提供幫助,因此患者只能將全部希望寄托于醫生。然而,由于我國既沒有家庭醫生制度,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又不高,加之優質醫療服務資源集中于大醫院,因此大醫院人滿為患,一號(一床)難求。即使掛到號或住進醫院的患者,也往往因為醫生工作量過大而得不到更“溫情”的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和家屬自然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正因為沒有患者團體和社工組織的介入,目前醫療行為基本上都是在醫患個體之間進行,醫護人員成了醫患矛盾的集中點,也是患者不滿的集中發泄點。因此,無論是以群體性的“醫鬧”對抗醫院,還是不滿情緒積聚為非理性行為,都是難以避免的。
綜上,要防止“醫鬧”和暴力傷醫,從患者的角度,就要改變患者和家屬的非理性狀態,給他們提供表達不滿的正規有效的渠道,并引導他們形成對醫療服務的合理預期。更進一步,就是要給他們更多的外部支持。
醫患雙方各自的組織化有助于緩解醫患沖突
在解決醫患糾紛的途徑上,通過醫療改革理順醫護人員的薪酬體系,以及加強對醫護人員的外部監管已成為共識。但是,對醫患沖突的理解和解決不應只局限于醫療領域,這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從社會成員角度看,個人既缺乏歸屬,也缺乏約束,對醫生和其他職業群體來說也不例外;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看,醫生與患者之間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互動關系,永遠存在陌生人之間的緊張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社會缺乏載體,導致管理成本高且效率低下,既無法控制醫生的行為,也無法解決患者的非理性問題。
因此,醫患雙方各自的組織化以及建立長期穩定的醫患互動關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一方面是從組織化的角度改變“原子化”狀態,通過醫患雙方的各自組織化,使他們成為自我管理的主體,包括醫患之間的溝通以及醫患矛盾的解決等都可以通過組織的渠道解決,政府的管理也可從面對個人轉向面對兩類組織;另一方面是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改變“原子化”狀態,在初級衛生保健領域,將抽象的“醫患”陌生人關系轉變為家庭醫生與簽約家庭的熟人關系,從而在長期互動中形成醫患信任。
具體而言,一是建立真正具有行業自治意義的醫生職業團體,保護醫生的利益,同時也規范醫生的行為;二是鼓勵患者組織和醫務社工組織的發展,保護患者的利益,同時也給患者和家屬提供心理支持;三是建立家庭醫生制度,使家庭醫生與患者之間形成長期的良性互動關系,變抽象的醫患關系為具體的熟人關系,并以此重建醫患信任。
事實上,醫患關系只是現代社會各種社會關系中的一種,其解釋邏輯亦可以應用到其他的社會關系中。而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整體信任水平的下降、職業道德的缺失、各種非理性暴力行為的出現以及各種服務和產品的安全質量等問題,也都可以從上述社會“原子化”的角度進行理解。因此,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背景下,社會的“組織化”是一個核心內容,也是解決中國目前很多問題的重要途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政策室副研究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