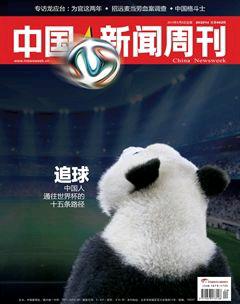畢業潮的機遇
今年,中國的高校畢業生人數預計將接近700萬,這個教字是美國今年高校畢業人數的2.5倍。而在1999年,這一數字在中國還不足100萬。中國政府預測,截至2020年,中國的勞動力群體中將有1.95億大學畢業生,而屆時美國的預期勞動力總數僅為1.67億。
高等教育急劇擴張的結果可想而知:隨著供過于求矛盾的加深,畢業生面臨的是高失業率與低工資增長兩大難題。上世紀晚期,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溢價下降了19個百分點,而近期畢業生的失業率已超過了16%。社會地位觀念深厚的大學畢業生們不愿從事那些需求旺盛但聲望低下的生產性工作,而堅持尋找政府或國有企業的辦公室工作崗位。可嘆的是,盡管領導層號召“創新驅動發展”,但中國經濟仍無法創造出足夠的高技能崗位,來吸收近年的高校畢業生大軍。
伴隨疲軟的大學畢業生勞動力市場的是低學歷勞動力的緊俏。非高校畢業生如今更樂于接受藍領工作,其失業率也降至4%。過去幾年里,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工資增長也因此超過了高技能行業。如今很多工廠工人的工資比辦公室崗位的入門薪資要高。這削弱了中國出口的競爭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的國際流動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為何由金融危機前的10%縮減至如今的2%左右。
聘用大量的大學畢業生意味著大學教育的工資溢價將降低,這將提高中國熟練勞動力以及高附加值部門的競爭力。事實上,韓國以及幾個東亞經濟體就曾采取這一措施,并成功提升了它們在價值鏈中的地位。上世紀80年代,韓國將大學錄取率提高了兩倍。至1993年為止,韓國大學生的工資溢價由1981年的125%降至61%,并順利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總體來說,大學畢業生比例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較小。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畢業生的質量值得考量。1997年高校擴招以來,學生與教授人數之比已經擴大了兩倍多。由于二本、三本高校的迅猛發展,大學生素質退化,部分內陸高校為了滿足錄取目標而刻意降低入學標準。
雖然全面提升大學畢業生的素質十分重要,但照亮畢業生就業前景的關鍵在于刺激中國發展服務業。服務業在中國GDP中的占比僅為43%,而韓國為60%,日本為70%,美國則接近80%。這個鴻溝壓抑著中國市場對畢業生的需求,因為服務行業比制造或建筑業需要更多的有技能的勞動力。
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改變和城市化進程,部分服務業會有所發展。人口老齡化會增加對醫療保健的需求,而城市化會刺激娛樂、交通和商業服務的發展。但是中國的服務業仍需要加速發展,并應當允許更多的私營企業進入電信、銀行與教育等國家主導的領域。這既能為高校畢業生帶來就業機會,又能刺激生產率,并提升中國在貿易服務中的全球競爭力。針對國企特權地位的改革也有所裨益。讓國企適度參與市場競爭有助于降低人們對國企工作的扭曲觀念,讓更多畢業生樂于進入私營部門。
中國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道路是不明朗的,其對全球的意義也十分復雜。向高附加值服務行業發展的中國,也將如幾十年前的日本那樣擠壓發達國家。日本的崛起使得美日貿易與投資關系變得十分緊張,盡管兩國在歷史上有著緊密的關系。近期,美日都感受到了韓國在高端制造業、科技甚至娛樂領域帶來的壓力。此外,中國在全球有競爭潛力的高附加值服務部門是網絡服務。中國電商行業預計將在今年超過美國,中國主流電商阿里巴巴的總銷售額比亞馬遜和ebay的銷量之和還要多1700億美元。
高校畢業生過剩既給中國決策者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雖然這種情況可能加劇社會矛盾,但如果能夠根據高等教育新的規模而相應地調整工資水平,并提升高等教育質量,中國也許既能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又能向西方國家的技術優勢發起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