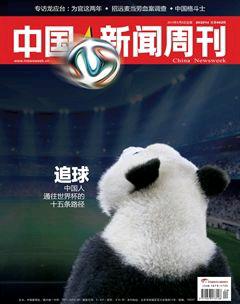網絡行為的“暗室效應”
徐賁
網絡暗室里交往的人們,如同帶著假面一樣,人們從平時的感情或行為約束中解放出來,也可能因為這種“解放”而肆無忌憚地做壞事。
人們注意到,許多網絡匿名發言暴戾囂張、尖酸刻薄、粗魯下流,這樣的行為經常對他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有人提出網絡實名制的主張,認為惟有如此才能改變不良的網絡行為。
毋庸諱言,網絡匿名發言是一種黑暗中的行為,而其不端往往由黑暗而生。19世紀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在《人生行為》(The Conduct of Life,1860)中就說過,“瓦斯燈是最好的夜間警察,世界也必須由最無情的公開來保護。”這個比喻被用在2010年初美國《心理科學》雜志發表的《好的燈是最好的警察》一文里。這是心理學家鐘承博、萬麗莎·邦士(Vanessa K.Bohns)等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他們指出,黑暗與不端行為有關,但是,黑暗對不端行為的掩護作用并非惡行出自暗處的唯一因素。不少美國媒體都報道了他們的一些實驗。
例如,研究者招募了84名學生,把他們均分成兩個組,其中一個組在裝有10個熒光燈的亮室中進行試驗,另一組在僅裝有4個小燈的暗室中進行。學生們各自拿到一個裝有10美元的棕色信封和一個空的白色信封。他們被要求在五分鐘內完成一個簡單的數學任務一在一個數字矩陣中找到相加等于10的數字對。他們每找到一對數字可以拿走50分,而其余的則需放回棕色信封。
研究者收集了實驗后留下的信封,并且回放了實驗最后五分鐘的錄像,結果非常出人意料。大多數情況下,暗室中的被試報告找到了更多對詞組,平均每人有7.78對。在實驗后進行檢查時發現暗室中欺瞞行為相當普遍,每一對被試所報告的找到詞組的對數平均比他們實際找到的多4.21對。而在明室中,被試僅比實際情況多報告0.83對。其他研究實驗也表明黑暗影響了被試的表現,“毫無疑問,黑暗增加了人們自私自利的行為。”
《時代》雜志在對該實驗的報道中說,研究者“并不建議交易大樓或……政客辦公室里都裝上大燈來使人們的行為更為高尚……但是,他們推測,我們用e-mail通信,在房間里面光線微弱時會比在滿屋陽光時更容易說謊或歪曲事實。”
由于匿名或使用假名,網絡交際本身就具有暗室效應。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是一位對“網絡自由”的負面個人和政治影響保持警惕的研究者,他指出,“社交傳媒的最大資產——匿名、感染力、相互聯系——也是它最大的弱點”。在網絡暗室里交往的人們,如同帶著假面一樣,他們彼此并不知道對方究竟是誰,也沒有明確的交往目的。人們從平時的感情或行為約束中解放出來,陌生人可以變成無話不談的朋友,不必為過分吐露心聲覺得難堪。但是,他們也可能因為這種“解放”而肆無忌憚地做壞事。
明亮、公開、透明是人們對公共事務和公共人物的基本要求。19世紀思想家密爾堅決主張民主投票應該公開,也就是投明票。不但議員該投明票,選民也該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議員應該投明票,從而向選民負責,因為選民有權知道他們選出的議員在每個重大議題上表示何種立場。
但是為什么認為選民也應該投明票呢?密爾的理由與主張網絡應該用實名頗為相似。密爾認為,遇到事情,我們往往有兩套選擇,“其一是根據個人理由的選擇,另一是根據公共理由的選擇。只有后者是我們愿意承認的。人們在秘密的情況下將比在公開的情況下更容易由于貪欲、惡意、嘔氣、個人的對抗,甚至由于階級或黨派的利益或偏見,作不公正的或不正當的投票。”人在公開行事的時候,比較注重自己的形象,比較愿意講理,展現自己好的一面,也比較會為自己的立場提出某種說得出口、拿得上臺面的理由。行事的公開本身就是對行為的一種制約。
但是,密爾并沒有把公開投票的優越性絕對化,他承認在某些情況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多數人被少數人支配,因而覺得不安全的時候,“投票者不怕得罪眾人卻唯恐得罪長官,不是向眾人負責而是向權勢者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說服力。如果選舉人不充分自由,那么秘密也就變得可以容忍了。類似的情況也使網絡匿名的秘密變得可以容忍。
人們在網絡上發言,不匿名是“明”,匿名是“暗”,明比暗好,這是因為惡行出自暗處。但是,月黑風高時和朗朗乾坤下所行的不端并沒有區別。明處也會有惡行,而出自暗處的并非都是惡行。這就像投票表決,明有明的好處,暗有暗的需要。關鍵是要了解暗處對惡行的誘惑,并能自覺抵制這種誘惑,惟有如此,暗中與明里的行為才可能在善的原則下盡量一致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