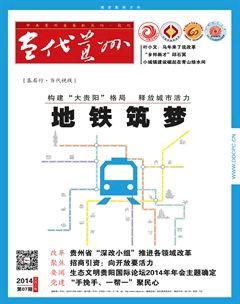合理有效配置生態資源
林永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不能過分依賴行政手段和計劃思維,而是需要運用法律尤其是環境經濟政策工具,發揮制度信號的規范和引導作用,讓市場決定生態資源的合理配置。
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
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是指利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正式制度(法律、政策、規章、條例等)或非正式制度(道德、倫理、習俗等)的總和。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主要是指從政府的立場出發,如何通過制度建設,規范和引導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行為,合理有效配置生態資源,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進而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出于兩點考慮:一是包括人與自然在內的生態系統都屬于稀缺性資源,而經濟理論中的稀缺性資源主要分為四類,土地、勞動力、資本和企業家,勞動力和企業家都是人,土地包括地下的礦藏資源和地上的森林物種等生物資源;二是“生態文明”是經濟增長、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三重均衡的社會形態,經濟增長、資源節約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問題,環境也是一種資源,如果在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某個國家或地區環境質量相對優良,就意味著綠色競爭力,因此,環境保護的核心也是環境資源配置問題。
目前,環保部已經批了涵蓋省、市、縣三個級別的多個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示范區,這些區域大都擁有非常豐富的生態資源,比如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森林公園和濕地之類的自然保護區、風景旅游景區)或歷史人文景觀、較高的森林覆蓋率、特色的生態工業園區或有機綠色農業等等。但總體來看,各地對如何通過構建制度體系配置生態資源的理論分析和現實做法仍然不夠,需要結合各地特色生態資源進行具體研究。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是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下,通過優化制度設計,合理配置生態資源,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關于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構建,《決定》明確提到四個方面制度:一是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二是實行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制度;三是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四是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前兩個方面制度實際上旨在解決生態資源歸誰所有以及自上而下進行區域空間規劃的問題,比如耕地紅線、水紅線、生態紅線,等等。第三個方面制度旨在制度化解決對生態資源的使用和維護問題。最后一個方面制度強調政府作用尤其是政府監管。
《決定》在解釋后兩個方面制度時,已經蘊含了運用市場化機制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路,比如“發展環保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實行污染物許可證制度,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等交易制度,發展環保市場,有助于解決環境資源配置問題,延伸到更廣泛的生態資源范疇,也必須運用市場思維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建立運行良好的“綠色市場”
所謂“市場”是指在一定的交易規則下,買方和賣方就某種產品和服務達成交易。因此,運用市場思維構建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就是要求通過制度設計,建立并保障“生態產品和服務市場”或叫“綠色市場”并保障其良好運行。
從交易產品來看,解決“買賣什么”的問題需要相關制度設計。迄今,全國多地已經出臺相關政策,鼓勵與生態資源相關的產品或服務交易,除了各類自然資源(花草植物、木材、能源、礦產等)以外,還包括衍生品,如綠色有機食品、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碳、COD)排放權、節能量(合同能源管理)等,但仍存兩個問題:
第一,衍生類交易產品不夠成熟、監測力度較為薄弱。通常而言,一個成熟市場上的交易產品一定是可識別、可核算、可交易。自2008年以來,先是北京、上海、天津,接著深圳、嘉興等地先后成立排污權交易所,推行二氧化硫、COD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權的交易,但這類衍生品交易進展緩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交易產品不夠成熟,缺乏監測,這就需要政府加強體制和制度設計,是環保部門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監測交易主體的污染物排放指標并公開可查詢或提供給所有交易平臺,還是委托第三方進行獨立監測,實行政府購買、服務外包的方式?需要各地認真探索。
第二,交易產品的范圍有待延伸和突破。能源、礦產、木材、綠色有機食品等都是可見的交易產品,衍生類的排污權已經算是對交易產品范圍的延伸,未來要通過制度保護生態環境,還必須要回答,維護良好的森林或濕地等生態資源,是否是可交易的?這也需要制度設計,進一步延伸交易產品的范圍,對“交易”的概念進行突破,分析誰來買賣,即交易主體的問題。
從交易主體來看,解決“誰來買賣”的問題也需要制度設計。誰擁有生態資源,誰才會是綠色市場上的賣方?《決定》中提出的“自然資源的產權制度”,實際上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表現為目前在全國大范圍推行的土地、森林、水域等“確權”行動。但依據現有的政策,如《決定》中提及的“用途管制制度”,即耕地、水、生態等各類“紅線”政策,大部分生態資源所有者,無論是居民個人、企事業單位、集體,還是國家,都擁有不完整產權,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合格的“賣方”,但同時“紅線”政策事關國家糧食和生態安全,不能動搖。
調動“賣方”生產、經營和維護生態資源的積極性,依靠強制性的行政甚至刑事處罰并不公平,政府需要測度這些“紅線”以內生態資源的外部性邊界,并設計相關的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制度,創造出“買方”來購買這些產品和服務,如果某個紅線區域內的生態資源只利于其周邊較小區域,那么這種產品和服務的“買方”就只能是周邊受惠區域的居民和政府,相應需要橫向的轉移支付或生態補償制度。如果區域的生態資源維護惠及全國,則需全國人民買單,運用中央財政實行縱向的轉移支付或生態補償制度。
排污權交易市場上的買賣主體相對復雜,在排污指標監測成熟的條件下,可由排污權交易所實行會員間的自愿性減排交易制度,更多要依靠國家環境立法創造出交易主體,即從法律上回答哪些主體擁有、為何擁有以及擁有多少可交易的排污指標或權利,哪些主體又必須要購買,如果不購買則會受到怎樣的處罰等。這實際上涉及到國家或地區環境容量及排污權初始指標分配問題。
從交易規則來看,保障交易秩序要依靠法律制度規范。在煤炭、石油、天然氣、水、電等能源資源市場,需要打破行政壟斷,同時穩步推進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最終取消指導價、階梯價、峰谷分時價,過渡到市場決定價格。在環境污染物排放權交易市場,需要完善監督體系,加強環境立法和執法力度。在自然保護區之類的“生態服務”市場,需要建立穩定、長效的轉移支付或生態補償制度。(作者系北師大中國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岳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