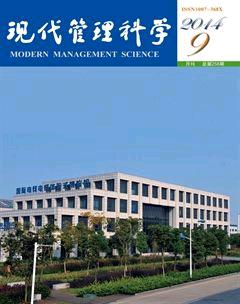組織忠誠感:概念、研究現狀與前瞻
陳致中 李靜
摘要:文章回顧了“忠”這一價值觀的歷史背景,探討了西方組織行為學中與組織忠誠相關的概念: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分析近年來海峽兩岸學術界對建構組織忠誠概念所做的努力,及目前存在的不足,并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組織忠誠感;主管忠誠;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
在華人企業中,員工的忠誠(Loyalty)無疑是十分受到重視的概念,企業領導人無比希望擁有一批忠于自己并忠于公司的員工。員工的“忠誠”與否,往往不僅是企業考核員工的重要標準,也是企業高管提拔部屬、培養接班人時重要的考慮因素。然而,忠誠感這一概念在西方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中,卻難以找到對應的研究背景。
事實上,并不是西方管理學界不重視組織忠誠,而是他們把忠誠這一概念融合在對其他組織行為學理論的研究當中,諸如心理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和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等重要的組織行為學概念,其中都包含了與忠誠感有關的內涵。然而畢竟中、西方文化背景、社會脈絡、組織架構等方面都存在差異,上述概念所包含的內容,與華人社會所重視的“忠”并非完全重合。因此為了對華人所說的“忠誠感”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必要深入考察忠誠這一概念的歷史背景,以及中西方相關的研究脈絡。
一、 忠誠:華人社會的固有價值觀
華人社會對“忠誠”的重視遠大于西方社會,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跟華人文化當中較高的集體主義傾向有關。Yang認為,華人社會與西方社會最主要的文化差異,就在于集體主義或關系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分野。而Hofstede對跨國文化價值觀的研究也表明,不僅中國,凡是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或地區,包含韓國、日本等,均有著較高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傾向。楊國樞和余安邦認為,集體主義傾向使得華人文化價值觀中帶有較強烈的權威取向(包含權威敏感、權威崇拜、權威依賴),這對華人組織行為的影響極為顯著,容易使得雇員對組織上級產生依賴甚至崇拜,而上級則將下級的服從、依附和忠誠視為重要的品質。
“忠”這一概念大致誕生于春秋時代,其最初是指個人內心的“誠”與“敬”,即誠懇厚道、盡心盡力之意;最初的“忠”并沒有具體的效忠對象,而是個人所應具備的一種泛化的美德。但后來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形成和鞏固,“忠”逐漸從個人的美德,轉化為一種以國家和君主為對象的片面道德義務,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成書于東漢時期的《忠經》可以說是對“忠”這一概念闡述最深入的典籍。《忠經》第一章“天地神明章”指出,忠是一種合乎天地運行的道理,其關鍵在于“聯結”,聯結個人而成為健全的人、聯結家人而成為“家”、聯結眾人而成為“國”,聯結國家、君主與天地萬物,則能夠做到“天人合一”。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忠”并不只是下級對上級的忠誠,而是一種聯結個人、家庭、社會乃至于天道,由小而大,環環相扣的一種普遍道德思想;如《忠經.天地神明章》所言:“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國忠之終也”。可以說,古代的“忠”,在其內涵上遠比今天的“忠誠”更加廣泛。
縱觀《忠經》的內容,可以歸納出“忠”的主要特點:(1)忠誠是個人修身、家庭興盛、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2)忠誠的關鍵在于“聯結”,是一種聯結上下關系的重要態度和行為準則。(3)雖然忠誠的本質不變,但會隨著個人所處的地位,而有不同的對象和表現方式。(4)忠誠的最終目的,是追求集體的利益。
宋代以后,“忠”的概念逐漸轉化為一種較為片面化的道德觀念,即“忠君愛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觀念。然而從前面的探討,可以看出華人的“忠”這一思想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和西方背景下的組織承諾、組織認同等,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姜定宇等人認為,西方強調的是個人與組織的心理連帶和歸屬感,而華人社會的“忠誠”,則往往首先強調對直屬上級或最高主管的個人效忠,接著才是對組織整體的效忠。
二、 西方組織忠誠相關研究
西方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者較少直接探討組織忠誠這一概念,或是將組織忠誠和組織承諾視為可以互換的概念。其他如組織認同、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助人行為、心理契約等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和組織忠誠有關。但整體而言,與組織忠誠有關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主軸:一是研究員工的忠誠“態度”,以組織承諾為代表;二是研究員工的忠誠“行為”,以組織公民行為為代表。
最初,組織承諾研究所關注的是行動承諾(Behavioral Commitment),即認為員工只要不離開組織,就表明他們具有忠誠度;換言之,若是員工認為離開組織會遭受較大的損失或具有較大的機會成本,他們對組織的忠誠度就會有所提高,這在后來演變為持續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和工具承諾(Instrumental Commitment)等概念。然而這樣的觀念只能解釋員工的離職與否,對于預測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投入感和績效卻毫無助益。
后來,組織承諾的研究逐漸轉向重視員工對組織的心理投入、認同和歸屬感,如Porter等人將組織承諾定義為員工對組織單方面的認同與投入,愿意付出額外努力以實現組織目標,且熱切希望能保有組織成員的身份。目前,加拿大學者Meyer和Allen對組織承諾所界定的三維度結構--持續承諾、情感承諾、規范承諾——最廣為后續研究者所采用。其中持續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指員工感知到離開組織會遭受較大損失,因此對組織產生歸屬感;情感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指員工對組織的情感依附,以身為組織成員為榮,并逐漸內化組織的價值觀;規范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則強調個人與組織關系中的義務層面,認為員工對組織的持續投入和心理歸屬,會產生一種對組織的道德責任或義務,即“公司的事就是我的事”。目前在西方研究中,規范承諾與情感承諾的差異并不明顯;但楊國樞和余安邦認為,在華人社會,角色義務是個人重要的行為準則,換句話說,規范承諾與華人的“忠誠”觀念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
然而,組織承諾基本上關注的是員工對組織投入、歸屬的態度方面,但華人所謂的“忠誠”不只是一種態度,還包含了實際的行動(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與組織忠誠有關的行為層面研究上,西方組織行為學中與之最接近的,要數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了。
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源于Katz的“角色外行為”,他認為為了維持組織的順暢運作,除了需要員工完成組織所要求的工作之外,往往還需要員工做出一些超乎角色要求的創新與自主行為。后來,Smith等人將這種“角色外行為”統稱為組織公民行為,并認為其應該包含助人(Altruism)和順從(Compliance)兩個面向;Organ則認為除了助人和順從外,組織公民行為還包括了禮節(Courtesy)、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和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另一方面,Van Dyne等人則通過政治學理論的探討,提出了所謂“積極公民特征”(Active Citizenship Syndrome),其中包含了組織服從(Organizational Obedience)、組織忠誠(Organizational Loyalty)、組織參與(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三個維度。其中“組織忠誠”指員工與組織一同面對威脅、維護組織聲譽,以及為了公司整體利益而與其他人合作。可以看出這里所謂的“組織忠誠”與華人所謂的“忠”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反映了組織公民行為這一概念與組織忠誠密切相關。
從上述文獻綜述可以看出,雖然“忠誠”這一概念在西方受重視程度比不上華人社會,但有許多重要的研究理論都和華人所說的忠誠密切相關,其中組織承諾更是長期以來組織行為學當中最受重視的概念之一。換句話說,不管是不是采用“忠誠”這個名義,華人“忠”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服從、盡責、正直、利他、奉獻、投入等觀念和行為,同樣也是西方人所重視的組織價值。
然而,由于西方長期以來將對組織忠誠的研究,區分成態度(以組織承諾為研究路徑)和行為(以組織公民行為為主要研究取向)兩條研究路徑,且兩者缺乏有效整合,使得實際研究工作中經常出現概念重復、混淆、界定不清等問題。換句話說,在華人社會對組織忠誠的研究中,實際上不宜直接引用組織承諾或組織公民行為等方面的研究;畢竟華人的“忠”包含了深遠的文化意涵和歷史底蘊,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果我們貿然地將一種文化背景下的概念,強行引入另一種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往往會導致廣泛的誤解和偏頗。因此,我們有必要基于華人社會的獨特背景,對華人組織行為學的這一特色概念——組織忠誠——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三、 華人社會組織忠誠研究現狀
許多歷史學者和文化學者都深入探討過中國傳統的“忠”這一道德觀念。劉紀曜論述自春秋時代到漢代之間“忠”的內涵轉變,發現在中國傳統社會體系下,一直存在著兩類忠誠概念,分別是對國家社稷的忠誠(公忠),和對君主個人的效忠(私忠),且隨著時代更迭,對私忠的重視逐漸超過了公忠。從這一方面來講,中國的“忠誠”顯然就和西方的相關概念不甚相同,西方人講到組織承諾或組織忠誠,主要是指員工對組織整體的忠誠,而非對任何個人的效忠。Jiang和Huangfu則進一步分析,提出中國式的忠誠更多地是基于地位尊卑、身份高下而體現的忠誠,而西方人所說的忠誠,則更類似于一種社會契約式的思想。
自1980年代以來,對華人社會背景下組織忠誠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如周逸衡深入訪談了我國臺灣地區43家大型企業的高管人員,發現高管心中的組織忠誠,通常與員工盡忠職守、盡心盡力、把公司當成自己的事業有關;同時,對組織的忠誠與對公司領導者的個人忠誠,往往是分不開的。李慕華更進一步指出,華人的組織忠誠與西方背景下的組織承諾有著顯著的差異:組織忠誠較強調情感面,而組織承諾強調工具面;組織忠誠往往是基于對老板或高管的個人效忠,而組織承諾則是以整個組織為對象。
鄭伯壎對華人領導行為的研究,則發現華人企業的領導者,往往會根據部屬的親(關系深淺)、忠(效忠程度)和才(能力稟賦)三項因素,來對部屬進行歸類。而且,領導者普遍對于忠誠的部屬更為照顧。鄭紀瑩則發現員工心中的組織忠誠,事實上可以區分為“對主管的忠誠”和“對組織的忠誠”兩方面,“效忠”的對象不同,態度和行為表現也有別;她的研究發現,華人組織中的組織忠誠,與一些正面的態度和行為變量有著顯著的相關性。
在中國大陸,雖然許多組織行為學研究中都有涉及到“組織忠誠”,但多半是直接引用西方的組織承諾概念,將組織承諾等同于組織忠誠。如周明建和葉文琴在研究組織忠誠、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間的關系時,直接采用了Meyer和Allen的情感承諾量表來作為“組織忠誠”的測量工具。鄭海蓮同樣采用了組織承諾量表,來探討審計人員組織忠誠感對其知識共享與整合的影響。張健對知識型員工組織嵌入、組織忠誠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也是直接套用Meyer和Allen的持續承諾、情感承諾、規范承諾三維度來作為對組織忠誠感的測量。
然而如前所述,西方背景下的組織承諾,與華人社會中所說的“組織忠誠”,兩者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中國的“忠”更多地是基于儒家文化背景下,以下對上的服從、歸屬、犧牲奉獻為基礎的一種道德素養,而西方式的組織承諾則更多地是基于個人和組織間的心理契約。因此,簡單地將組織承諾理論與量表,套用到對華人組織忠誠的研究,顯然是不夠科學的,很容易忽略掉深層的文化脈絡和情感因素等方面的差異。
整體而言,我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在近十多年來對華人背景下的“組織忠誠”,做了較多有系統性的研究。
一般而言,對華人組織忠誠的研究,可以區分為“主管忠誠”和“整體組織忠誠”兩條研究路徑,前者強調下屬對上級的效忠,后者則是對組織本身的忠誠;這兩條路徑正好與劉紀曜所說的古代存在的“私忠”和“公忠”兩種觀念互相對應。
如Chen認為華人所說的組織忠誠,主要是指對主管個人的忠誠,他繼而編制出了主管忠誠測量問卷,其中包含了認同主管、內化主觀價值觀、努力、跟隨、奉獻等五個維度。鄭伯壎、鄭紀瑩和周麗芳所歸納出的主管忠誠五個維度則分別為認同、內化、奉獻、效勞、服從。
在對組織整體忠誠的研究方面,鄭紀瑩對臺灣地區一家民營企業主管進行了深入訪談,提出員工對組織的忠誠包含了情感依附、工作積極、達成要求等方面。Farh、Earley和Lin則借鑒了西方的組織公民行為概念,提出員工對組織的忠誠,應該包括恪守本分、認同公司、協助同事、維持和諧,以及保護公司資源等行為。
姜定宇等人參考了過去與主管忠誠、組織整體忠誠相關的研究,并回顧了中國文化思想中關于“忠”的內涵,進一步將華人組織忠誠界定為:個人角色與組織的緊密結合,個人愿意將組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并且為組織主動付出。他們并且進一步整合了過去的相關論述,從忠誠對象(主管或組織)、忠誠層面(態度或行為)、忠誠內容(情感、規范、工具)等三個面向,提出了組織忠誠的整體模型。
四、 總結與前瞻
在華人社會,對“組織忠誠”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極為重要,但又十分復雜而模糊的研究議題。一方面,無疑華人企業主管都極為重視下屬的“忠誠”,甚至把下屬的忠心與否作為考核、加薪和升遷的重要依據,對“忠”的重視甚至在許多時候超過了對下屬才能或業績的重視;因此,在近年海峽兩岸的組織行為研究中,不乏將組織忠誠感納入研究變量的例子。但另一方面,對于“忠誠”這個概念到底有什么內涵、包含了哪些維度,卻又很少有人能說個清楚明白;概念的模糊和重疊,使得大多數研究者對于組織忠誠的探討,都處在霧里看花、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態。
在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中,雖然已經有不少探討組織忠誠與其他變量(如組織公民行為、工作滿意度、工作績效)之間關系的論文發表,但大多是直接把“組織承諾”的量表套用在對“組織忠誠”的研究上,難免有概念混淆之嫌,且許多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也值得商榷。
而我國臺灣地區的學者,雖然對華人組織忠誠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脈絡有較為系統而深入的思考,并試圖建立真正基于中國文化背景的組織忠誠感理論和測量量表,但到目前為止,大多仍停留在概念探討和定性研究階段,缺乏更有系統的大樣本調查和量表建構工作,對于組織忠誠的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以及作用機制等,相關研究也幾乎付之闕如;此外,不同學者之間,對于組織忠誠的對象(主管或是整體組織)和層面(態度或是行為)等方面,依然未能形成真正的共識。
因此,對于“組織忠誠”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組織行為學概念,目前的研究還有較多欠缺。未來的組織忠誠研究,應該著重在兩個方面:
(1)通過系統性、科學性的扎根理論途徑,對組織忠誠的概念結構和維度進行深入探討,建構出具備足夠信度和效度的測量量表,并通過大樣本的調查,來對量表進行檢驗。此外,由于過去海峽兩岸在組織忠誠研究方面的交流較少,研究取向也大不相同,因此未來應該強化兩岸學者的交流合作,建構出適用于大中華區整體環境的組織忠誠度理論結構和測量工具;
(2)在上述工作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組織忠誠的作用機制,如前因變量、結果變量和調節變量等,以深入了解“組織忠誠”在華人組織當中的真正作用和影響力如何。雖然過去對于華人背景下的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作用機制,已經有了汗牛充棟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組織忠誠本身的特殊性和文化脈絡,對于這一中國特色組織行為理論的實證研究,將是未來相關研究的重點內容。
參考文獻:
1. 楊國樞,余安邦.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中國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2. 鄭伯壎.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心理學研究,1995,(3):142-219.
3. 劉紀曜.公與私——忠的倫理內涵.見黃俊杰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天道與人道.中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
4. 鄭紀瑩.華人企業的組織忠誠:結構與歷程.中國臺北: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學位論文,1996.
5. 張健.知識員工組織嵌入、組織忠誠與組織公民行為的作用機理.天津大學學位論文,2011.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傳媒集團組織文化與組織績效之研究”(項目號:GD11YXW01)。
作者簡介:陳致中,清華大學管理學博士,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靜,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收稿日期:2014-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