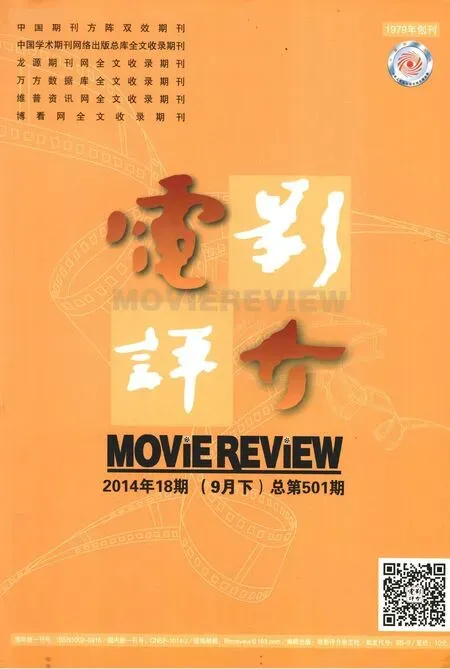談電影的空間敘事——以《無人區》為例
張 穎

電影《無人區》海報
繼“空間”轉向之后,在敘事學領域,人們開始了空間敘事問題的研究。空間敘事,即運用“空間”進行敘事,是推動情節發展的一種手段或方式。按照媒介屬性不同將空間敘事分為文字媒介的空間敘事和非文字媒介的空間敘事。電影是集多種元素于一體的聲像藝術,自然歸屬非文字媒介。電影作為敘事性作品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主要由“一系列畫面的排列與組合(時間畸變)來刻畫形象,描繪事件,從而獲得了強大的敘事性表現力”[1],以時間線性敘事為前提,通過空間,即作為共時性的場景、畫面及人物之間的行為、交流等的呈現在觀眾大腦中形成的完整的故事情節。“電影的空間意識是電影思維一個基本的內容,也是電影研究中屬于知識論范圍的一個與時間觀念同樣重要的、核心的概念。”[2]因此,談電影的敘事問題,“空間”元素必然不能缺場。從空間敘事角度來解讀電影故事情節構成符合電影藝術自身的特殊性。
“電影空間既不是單純的客觀外在空間,也不是純粹的主觀內在空間,而是兩種空間經過制作者的心理空間作用之后,聚焦于膠片、磁帶、光盤或芯片種種介質上,在借助放映設備投射到銀屏上的聲畫空間。”[3]因此,在探討電影空間敘事問題之前,應先廓清“敘事空間”與“空間敘事”兩個概念。在電影藝術中,“空間敘事”是一種敘事策略,分析敘事如何用特殊的“語言”集結形式來進行動態的空間生產,反映空間在電影情節發展的作用,它針對的是具有敘事功能的“空間”;而“敘事空間是電影中直接呈現的用于承載故事的視聽空間形象”[4],是伴隨情節發展的場景,是一種客觀存在。
寧浩導演的影片《無人區》早在2009年開拍,“雪藏”四年后于2013年12月上映,拍攝成本不足2000萬,但票房漲勢兇猛,3日過億,成為2013年內地總票房超越200億的沖線點。它由徐崢旁白兩個猴子摘桃吃的寓言故事作引子,以一只小鳥被成功活擒開始,以余南飾演的滿口謊話的嬌嬌重返嶄新且充滿陽光的生活結束,中間夾雜著倒賣國家稀有珍禽的罪惡、無良律師的追名逐利、“夜巴黎”的“捆綁經營”等等,整部影片充斥著暴力、血腥及黑色荒誕式的巧合,被譽為“好萊塢類型片的本土化移植”。基于電影藝術的特殊性,拋開對影片的表意研究,從空間維度看《無人區》如何敘述故事,何以顯現深層的敘事結構。而“電影敘事是以直觀的視覺畫面為基礎來‘講述’故事的”[5],因此,從鏡頭所呈現的視覺畫面看,除影片所必須的聲音、燈光等技術手段外,對影片敘事起主導作用的空間要素主要包括物理場域空間和演員表演空間,《無人區》也不例外。
一、物理場域空間
關于“物理場域空間”的界定離不開加布里爾·佐倫的《走向敘事空間理論》(1984)中對文本空間結構縱向層面上的劃分,將敘事的空間分為地志的空間、時空體空間和文本的空間,建構了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實用且最具理論高度的空間理論模型。空間的地志學層面“是處于重構的最高層次的空間,被視為獨立存在的,獨立于世界的時間結構和文本的順序安排。文本能通過直接描寫的方式來表達地志的結構……。”[6]據此,在電影鏡頭所呈現的畫面中,物理場域空間主要指視覺直接接收到的影片故事情節所發生的場域性的空間信息,是鏡頭里的一種客觀呈現。簡單來說,即影片故事發生地理性的區域,大到宇宙星系、某個星球、某個國家、某個城鎮,小到海邊、荒漠、花園、房間等等。不管鏡頭畫面有無人物的出場,但是物理性的場域空間總會客觀存在于其中,包括對人或物的特寫鏡頭,而人或物是不會獨立于物性空間之外的。只能說在這種情況下,物性空間對于影片的敘事僅僅起輔助作用。
就電影鏡頭里的物理場域空間而言,按照其真實與否分為現實的與非現實的空間(包括夢境空間、幻想空間等);按照影片故事情節的發生、發展、高潮、結局將其分為交代性的、沖突的、高潮的、回落的四種功能性的物理場域空間類型。物理場域空間還可據影片的類型來劃分,比如美國西部片,表現出明顯的空間地域性,但除此之外,諸如喜劇片、愛情片、歌舞片、警匪片、動作片、恐怖片等等,則需要通過下一小節將要探討的演員的表演空間來實現其分類。在《無人區》中,從片名就可鎖定影片故事發生的地志空間為荒無人煙的地方,且通過安排組合一系列現實的空間而非夢境或幻想空間傳達信息,完成敘事。因此,依據功能性將影片中主要的幾個物理場域空間進行分析,看其在影片敘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西北偏遠小鎮:交代性的物理場域空間
影片從旁白兩個猴子摘桃吃的寓言故事開始,同時鏡頭畫面切換荒漠上不同區域的地貌,廣袤的荒漠正好與片名“無人區”相契合,之后定格到荒漠上的一只小鳥,分別用特寫鏡頭和長鏡頭表現小鳥被掩藏在不遠處的獵人活擒的過程,交代影片所述之事就發生在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警車橫穿疾馳之后的塵土飛揚、需要馬車中轉聯接的火車站和法庭、官司勝訴之后在簡陋的“帝豪大酒店”交涉律師費尾款等,都以荒無人煙的西北大漠為背景,或近景或遠景,交代影片故事情節即將要展開的地質地貌特征,完成其在鏡頭畫面里出現的敘事功能。
(二)“無人區”的公路及公路上的“夜巴黎”:發生沖突的物理場域空間
簡單來說,影片情節向前推進并上升的過程中,勢必會有沖突情節的助推,發生沖突的場域空間稱為沖突性的物理場域空間。影片中律師潘肖最終以紅色轎車成功交涉到服務費的尾款之后,趾高氣昂的驅車飛奔于看不到盡頭的公路上,為“上頭條”與其城里的助手通話,不知不覺進入“五百公里無人區”,手機失去信號,隨即發生了一系列的沖突。鏡頭畫面里的西北地貌廣袤而令人神往,筆直的柏油公路干凈而又靜謐,與西北人粗獷、純粹的本性相契合,但這也恰恰反映了他們野蠻的一面,為故事情節的暴力、血腥埋下伏筆。拉油卡車不讓路及扔酒瓶砸玻璃的霸道習氣、前擋風玻璃碎裂導致撞人事件、為加油而兩次陷入“捆綁經營”的“黑色服務區”、欲焚尸而無奈于Zippo已用于報復卡車司機、與卡車司機在“黑色服務區”再次激烈打斗,進入漆黑夜晚的公路,沖突不斷在“無人區”的公路上升級。這條公路又“黑”又“長”,欲要脫離苦海的嬌嬌被潘肖發現后的爭執、黃渤飾演的角色蘇醒后的報復、卡車上哥倆遭遇到的不幸、父子倆追尋“賺錢工具”及販隼人對傻兒子、潘肖的野蠻行徑等,種種暴力、血腥與這條漆黑的公路相互映襯,發揮沖突性場域空間的敘事效果。
(三)“二道梁子”:進入高潮的物理場域空間
影片情節發展到高潮是對物理場域空間的設置,是故事發展到最高點所選擇的場域空間,與高潮的情節結構相吻合。《無人區》中將“二道梁子”安排為情節進入高潮的場域空間,理由有二:第一,依照故事情節發展的需要,“漆黑”公路上的沖突告一段落,應該安排另一個場域空間與之相區別,迎合高潮的到來,于是選擇了下一站——“二道梁子”,一個有大門的西北大漠上的相對封閉的地域空間;第二,從影片中獲悉,“二道梁子”還是一個罪惡交易的據點或場所。經歷血腥、暴力之后的潘肖人性獲得爆發,為了救嬌嬌舍身取義,完成了對自我的救贖,同時也意味著對罪惡的一種搗毀,賦予了高潮環節的物理場域空間一定的象征意義。第三,長鏡頭給出“二道梁子”的“大門”沒了,相對封閉的空間暴露在外,與影片開始鏡頭畫面所呈現的西北荒蕪廣袤的大漠渾然一體,恢復往日的靜謐。警車載著嬌嬌,鏡頭呈現的車外的景色依舊是安靜的“無人區”,給影片情節達到高潮之后與尾聲銜接處形成一個完美過渡。

電影《無人區》劇照
(四)校園/教室:舒緩緊張狀態、影片情緒回落的物理場域空間
古往今來受“大團圓”結局的影響,影片情節的高潮之后,總會有舒緩緊張狀態,是情緒回落的敘事環節。從空間角度看,往往采用一些充滿陽光、敞亮、和諧、安靜的空間來昭示影片的結局,或帶著對未來美好的情愫,或前途一片光明,或還有很長的人生路要走,等等,使激烈火爆的高潮情節自然回落。正如影片《無人區》中,嬌嬌獲救,鏡頭畫面中兩只鷹在西北天空的自由翱翔,之后鏡頭切換到充滿陽光的校園和教室,以及舞蹈教室里進來童真、活潑、開心的小朋友們,空間選取的是預示著她重獲自由并且即將開始嶄新的人生。
二、演員的表演空間
對于影片故事的講述,“不僅是攝影機的機位,也包括人物的空間安排;不僅是剪接,也包括演員的運動;不僅是變焦鏡頭,也包括對白——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們所看到的實實在在的環境和行為,都是電影敘述創造出來的”[7],強調電影故事的敘述除必須的技術手段外,還應有物理場域空間和演員的表演空間。這里的“環境”即可寬泛的理解為“物理場域空間”,而“人物的空間安排”、“演員的運動”、“對白”及“行為”恰恰就是演員飾演角色塑造人物所涉及到的“演員的表演空間”。換句話說,電影中的人物作為獨立的個體也是一種空間呈現,人物的言行舉止直接關系影片的敘事進程。由此,對影片敘事起助推作用的除鏡頭畫面所呈現出的物理場域空間外,還有一個最關鍵的空間要素——演員的表演空間。它通過演員飾演角色從服飾、表情、語言、行為、動作等方面來詮釋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同時主要靠對白和行為動作推動劇情發展。與物理場域空間相比,最重要的區別在于物理場域空間是客觀性的,而演員的表演空間則具有明顯的主觀能動性。正好“電影與文學相反,用明確的以及可識別的肢體語言來表現人物,而這些因素在提示我們建構關于他們的個人特征方面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8]如下從《無人區》中幾個主要角色看演員的表演空間對影片敘事的重要作用。
首先談影片一開始出現的抓隼人和警察。肉眼直觀二人穿著打扮,除了濃郁的西北樸實民風外,從黃渤飾演的抓隼人在成功捕獵到“小鳥”后對比一張張珍貴飛禽的照片,并操起手機欲要聯絡等一系列的動作,還可捕捉到他常年從事此類工作,且經驗豐富。被捕后和公安干警在警車內的對白讓觀眾獲悉,影片故事開始于為阿拉伯王子抓稀有珍禽——隼,巨額的勞務費可以想象中東國家的富有;同時警車停到公路上的一剎那,“但好人不一定有好報”不屑的話音剛落,警車被撞翻,干警失去寶貴的生命,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熟知路況,嫻熟的撞車技術,淡定的表情,以及一瘸一拐的左腿,足以看出是多年來進行罪惡活動而達成的“默契”。
其次,看徐崢所飾演的律師角色——潘肖。從外貌服飾看,金絲邊眼鏡、長款西裝、白襯衣、領帶、皮手套、黑又亮的皮鞋等,帶有明顯的都市氣息,是律師身份典型打扮,與西北偏遠小鎮的風土人情似乎有點格格不入。正是這種不協調,作為外來者的潘肖卻在“無人區”里成為影片敘事的一條主線,通過他的眼睛看到了廣袤而落后的西北大漠,更重要的是透過他及與他發生沖突的其他人物的對白、行為動作等塑造人格的同時還推進的故事情節的演進,以至于出現那么多的黑色幽默式的巧合。對于他來說,“無人區”不僅無人,而且無情,血腥、暴力不斷沖擊著他的視覺,一次又一次觸碰到他的道德底線,逐漸完成從“無良律師”過渡到“正義戰士”,最終實現其人生價值。
他用極好的雄辯之口在法庭上為販隼人的刑事官司進行強詞奪理式的辯護,以及在帝豪大酒店成功交涉到紅色轎車作為律師服務費的尾款,足見他是一名為追名逐利不惜放棄正義、顛倒黑白、鉆法律空子的“無良律師”。法庭上勝利在望之時,擼下腕上手串放松地捻著以及在帝豪大酒店交涉完畢后緊張的收起自己的Zippo和香煙,鏡頭畫面里對潘肖這兩個小動作的特寫,分別為之后的故事發展埋下伏筆。因為公路路面狹窄與卡車兄弟的爭執,扔酒瓶砸裂前擋風玻璃,把打著的Zippo放入煙盒扔向卡車,視線不好撞傷抓隼人,緊張之下無奈接受“黑色服務”加油,澆汽油焚尸想撇清自己的清白,Zippo已作它用,重返“夜巴黎”加油,與卡車兄弟再次沖突,手串撒落一地,販隼人據串珠尋仇潘肖等等,這些均通過演員精湛的表演(包括表情、對白及動作),以及彼此間相互配合,由這兩個小動作而引出的黑色幽默式的巧合在影片敘事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影片中販隼人對于潘肖雄辯之舌無奈忍痛割愛,但販隼人拿匕首把紅色轎車上的通訊設備卸下,這個舉動為之后潘肖在得意忘形之時進入“無人區”遭遇了一系列的沖突而無法與外界聯絡等種種無助做了鋪墊。
最后,簡單談余男所飾演的舞女——嬌嬌。她,“夜巴黎”老板的兒媳婦,實則為“捆綁經營”的賺錢工具。破了洞的黑絲長筒襪,滿口閃爍其詞,對“奢華”皮草的愛不釋手,緊抓藏有“辛苦錢”的公仔,本性純良的她逐漸與人性大爆發的潘肖開始共進退,但面對罪惡百般無力,只有眼淚和恐懼,最終幸運獲救。對于謊話連篇的表演像是自然流露,讓潘肖心生憐憫,但從潘肖的表情中讀出,礙于車上藏匿有被撞之人,殘忍拒絕。伴著噙著淚水的獨白,“你看那鳥啊,它咋就飛那么高呢,為了口吃的,連命都不要了。我就跟那鳥也差不多了……”,似乎在回憶為謀生而進入“無人區”的無奈,甚至在“無人區”里過著不要命的非人生活。而嬌嬌與邢老師的對話則昭示著嬌嬌將尋找“正經工作”,開始新的生活。到此,嬌嬌平靜的情緒和愉悅地為小朋友服務使影片敘事結束暴力,回歸美好。
電影敘事中,從空間維度出發,主要由物理場域空間和演員的表演空間兩個層次整合鏡頭畫面,利用蒙太奇進行空間銜接與轉換,從而達到空間敘事的目的,完成故事陳述。對于電影空間敘事中蒙太奇的處理方式,如,因果連接法、平行處理、人物語言等,有待進一步深究。此外,還不能忽視聲音的處理、光線的運用等技術手段對電影講述故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5]李顯杰.論電影敘事中的畫格空間與敘事性[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6):92.
[2]林年同.中國電影的空間意識[M]//中國電影美學.臺北:臺灣允晨文化事業公司,1991:67.
[3]王佳寶.中國當代電影藝術的空間敘事研究[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10.
[4]黃德泉.電影的空間敘事研究——以張藝謀導演的作品為例[D].北京:北京電影學院,2005.
[6]程錫麟.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空間敘事[J].江西社會科學,2009(11):29.
[7][8](美)大衛·潑德維爾.電影詩學[M]//楊遠嬰.電影理論讀本.張錦,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2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