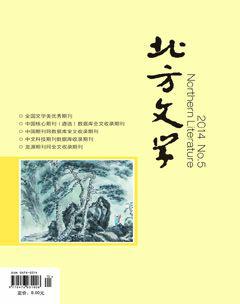清代筆記小說(shuō)中的“女鬼”形象
白凈義
摘要:清代出現(xiàn)了《聊齋志異》、《螢窗異草》、《子不語(yǔ)》和《閱微草堂筆記》四部較著名的筆記小說(shuō),代表了當(dāng)時(shí)筆記小說(shuō)的最高水平,受到許多文人們的狂熱追捧。女鬼形象在其中的頻繁出現(xiàn),一方面是由于當(dāng)時(shí)談講女鬼故事風(fēng)氣的盛行,另一方面則是其包含了作者很多的寓意。本文以女鬼形象為載體,簡(jiǎn)要剖析四部小說(shuō)的不同風(fēng)格,和女鬼形象在四部小說(shuō)當(dāng)中的不同特色。
關(guān)鍵詞:筆記小說(shuō);女鬼;聊齋;螢窗異草;子不語(yǔ);閱微草堂筆記
一、女鬼形象產(chǎn)生的文化背景
我國(guó)是一個(gè)宗教思想非常濃厚的國(guó)家。由于科技不發(fā)達(dá),古代中國(guó)人對(duì)很多自然現(xiàn)象無(wú)法做出合理解釋?zhuān)慊孟肓艘粋€(gè)神話體系,將許多不可解釋的現(xiàn)象都?xì)w結(jié)為神力(或妖怪的法術(shù))作用的結(jié)果。對(duì)于死后的世界,人們也極盡所能地去幻想,而無(wú)論是本土的各類(lèi)原始宗教抑或道教,還是外來(lái)的佛教以及各類(lèi)別的基督教派,都無(wú)一不是這種虛構(gòu)的死后世界和神靈體系為其拉攏信眾的招牌。各種各樣打著死后世界幌子的經(jīng)文書(shū)籍層出不窮。就連宣揚(yáng)正氣的儒教也處于維系宗嗣、禱念先祖的目的而重視鬼神祭祀。可以說(shuō),在中國(guó)古代,任何一種宗教都帶有迷信色彩。
在濃厚的迷信氛圍下,古代中國(guó)的普通家庭終日都要和各種各樣的鬼神打交道,如祖先、神靈、精怪、妖鬼……主持家務(wù)的婦女們大部分時(shí)間都在和鬼神打交道,而身為封建社會(huì)主角的男子,則更是與這些鬼魅之物(無(wú)論是已化為腐朽的先祖英靈,還是處在天宮虛無(wú)縹緲的神靈們)交往密切。他們的故事被一些人抱著某種目的傳播開(kāi)來(lái),后演化成各種各樣的故事版本。
于是一股談鬼說(shuō)神的風(fēng)氣蔓延在社會(huì)各階層。在各式閑侃雜談中,與凡人在相貌、行為上有著極大區(qū)別的妖狐鬼怪們紛紛登場(chǎng)。裝得滿滿一肚子故事的老人們便說(shuō)著一代代流傳下來(lái)的傳奇故事,所以,幾乎所有的器物都可以被賦予靈性而化身為妖魔鬼怪。柳樹(shù)精、花妖、魚(yú)怪、鏡靈、僵尸、狐女、幽魂等等各式各樣的精靈不斷以各種方式出現(xiàn)在數(shù)不勝數(shù)的故事中。[1]在無(wú)窮無(wú)盡的反復(fù)創(chuàng)造和完善之后,到了近代,中國(guó)古代文化當(dāng)中的神鬼故事便形成體系了。
文人自然不甘于寂寞,這些神鬼故事對(duì)他們有著強(qiáng)烈的吸引力。因?yàn)檫@些故事本身便有著極強(qiáng)的趣味性和可塑性,他們自然可以把自己心中所想的東西隨心所欲的添加在其中。這對(duì)于古代哪些視立言為人生三大目標(biāo)之一的文人們自然有著極高的誘惑。他們便開(kāi)始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從而間接地豐富了鬼怪故事的內(nèi)容。從兩晉南北朝時(shí)期志怪小說(shuō)臻于完善伊始,加之清談玄學(xué)的盛行,文人們便自發(fā)地收集起鬼怪故事來(lái)充實(shí)自己的腦海。這一時(shí)期最富盛名的便是干寶的《搜神記》,蒲松齡評(píng)價(jià)其“才非干寶、雅愛(ài)搜神”[1],可見(jiàn)《搜神》流傳千年魅力不減。
自此以后,沿著志怪小說(shuō)的路子,一大批筆記小說(shuō)在文人的辛苦搜集和創(chuàng)作之下陸續(xù)呈現(xiàn)。尤其是到了文字獄盛行的清代,莫談國(guó)事已經(jīng)成為文化界的共識(shí),文人因畏懼災(zāi)禍而決口不談時(shí)政,轉(zhuǎn)而將一身所學(xué)用到了閑侃雜談當(dāng)中[2]。志怪小說(shuō)這種只涉及非人世界的文章自然成為他們的最?lèi)?ài)。因而,延續(xù)了志怪小說(shuō)形式的筆記小說(shuō)便出現(xiàn)了“大爆發(fā)”。其中較著名的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紀(jì)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yǔ)》,長(zhǎng)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
二、女鬼的載體——四部筆記小說(shuō)的鮮明風(fēng)格
四部小說(shuō)雖題材相同,但風(fēng)格卻各有特色:《聊齋》記錄的是一個(gè)幾乎與現(xiàn)實(shí)世界毫無(wú)差距的翻版,書(shū)中內(nèi)容可以說(shuō)是他的激憤之作;《螢窗異草》雖然宣稱(chēng)“其書(shū)大旨,酷摩《聊齋》”[3],但其中所載更多的卻是女鬼與男子風(fēng)花雪月的故事;《閱微草堂筆記》多借用鬼神來(lái)說(shuō)教,“宣圣朝之德化哉”[4];而《子不語(yǔ)》則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丑惡的赤裸裸譏諷。不同的作品風(fēng)格緣于四人各不相同的人生閱歷,他們對(duì)社會(huì)、對(duì)人性的感悟也不同。正因如此,對(duì)待同樣一個(gè)問(wèn)題,同樣一種事物,四個(gè)人用自己的文筆給出了不同的理解。
蒲松齡一生潦倒落魄,臨到老時(shí)方才在科舉上得到一點(diǎn)安慰。他的一生可謂是大不幸的,在經(jīng)歷了無(wú)數(shù)風(fēng)雨,看慣了人世間的冷暖悲歡之后,在字里行間流露地自然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各種不平之事赤裸裸的嘲諷。在他的眼中,死后出現(xiàn)的各類(lèi)鬼神都還保有自己生前的某種習(xí)性:貪財(cái)?shù)囊琅f貪財(cái),好色的依舊好色,賭徒依然不忘賭博,酒鬼自然對(duì)美酒垂涎不已,當(dāng)然那些懲惡揚(yáng)善的英雄到了陰間依舊要除暴安良,宣揚(yáng)正義的清官在底下自然也會(huì)為民伸冤。加上其家族的濃厚佛教氛圍,自然在書(shū)中多次提及因果輪回這一宿命觀理論,也自然會(huì)有一種“天理循環(huán),報(bào)應(yīng)不爽”的態(tài)度和觀點(diǎn)[5]。但《聊齋》中更多的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嘲諷和抨擊,故郭沫若評(píng)價(jià)他“寫(xiě)鬼寫(xiě)妖高人一等,刺虐刺貪入木三分”。
據(jù)傳為尹繼泰之子的長(zhǎng)白浩歌子,作為一個(gè)出身名貴的公子哥,自然對(duì)那些恐怖無(wú)比的鬼神不感興趣。他所看重的是那些大膽開(kāi)放、狂熱追求愛(ài)情的奇女子的故事。若不是作品中夾雜了不少陰陽(yáng)相隔的愛(ài)情故事,恐怕《螢窗異草》一書(shū)也只能算作一本搜集了無(wú)數(shù)才子佳人故事的言情小說(shuō)集罷了。其作品更多地頌揚(yáng)了反禮教的愛(ài)情故事,而絕非含沙射影、直指時(shí)事的諷刺之作。這也是其一直致力于模仿蒲松齡的文筆,卻無(wú)法做到像蒲松齡一樣成功的原因。
介于兩者之間的《閱微草堂筆記》和《子不語(yǔ)》,在內(nèi)容上與前兩者也有極大差別。聊齋里的故事雖與現(xiàn)實(shí)相關(guān),但其中鬼怪妖神卻有著自己的一套“天道”準(zhǔn)則,而這源于蒲松齡家族當(dāng)中濃厚的宗教背景。《筆記》則體現(xiàn)了地域意識(shí)和禮教約束的成分。作品中的“人”,即使做鬼,也要死守一方土地,而其中的鬼怪則“不務(wù)正業(yè)”地站在人群中講夫子或者官員們所謂的“大道理”,卻不去害人、嚇人或者去勾引人、魅惑人。這風(fēng)格與紀(jì)曉嵐的達(dá)官身份相得益彰,而他的《筆記》可算是純粹的筆記小說(shuō):沒(méi)有辛辣的諷刺,亦沒(méi)有嘩眾取寵、鬼氣森然的奇文,即使保有其一貫的幽默,這部筆記也并沒(méi)有太多出彩的地方。紀(jì)的身份決定了其作品必然要多出許多官樣文章在其中。
《子不語(yǔ)》內(nèi)容比《聊齋》更深入。如果《聊齋》算是抨擊社會(huì)黑暗的話,那么《子不語(yǔ)》則是赤裸裸地揭露官場(chǎng)黑暗的內(nèi)幕。《子不語(yǔ)》中的鬼怪們大都“人性化”,它們無(wú)限接近于現(xiàn)實(shí)的人,“生時(shí)索貪,死亦如此”。《子不語(yǔ)》若非帶有許多陰森森的鬼氣,它完全可算作諷刺現(xiàn)實(shí)黑暗的小說(shuō)。這與袁枚人生經(jīng)歷大有關(guān)系。其曾在官場(chǎng)的底層摸爬滾打,自然對(duì)黑暗的現(xiàn)實(shí)有深刻的體會(huì)。故其作品對(duì)時(shí)事固然有辛辣的評(píng)論,但卻并不同于蒲松齡的義憤,更多的是譏諷和嘲弄。
由上可見(jiàn),不同的閱歷和性格造就了不同的寫(xiě)作風(fēng)格,而不同的寫(xiě)作風(fēng)格在同一種人物形象上體現(xiàn)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故事內(nèi)容。
三、女鬼的不同類(lèi)型
綜觀四部筆記小說(shuō),其中的女鬼可謂姿態(tài)萬(wàn)千、性格亦各不相同。但她們身上或多或少有著相同的特性,按作者的立意,可以大致分為不同的幾類(lèi):
第一類(lèi)為吸人精血的兇神惡煞。這類(lèi)女鬼是諸多筆記小說(shuō)中最為活躍的女鬼形象之一。其大多以吸食男子陽(yáng)氣精血為食,且多貌美如花、性格放蕩。她們?nèi)缤瑹熁ㄅ右话愎匆凶樱宰约旱纳眢w為餌,在男子陷入短暫的歡愉之際吸食他的精血,或者吞噬他的血肉。描述之始,文字總是很香艷,在高潮部分卻突然轉(zhuǎn)折讓人措手不及,以此凸顯女鬼的兇惡。
第二類(lèi)是復(fù)仇的羅剎。這類(lèi)女鬼,生前多半蒙受了不白之冤,或者受辱自盡,或者為奸人所還害。總之一腔怨氣幻化為鬼之后,必定要復(fù)仇害人方能消除。而這種兇神惡煞般女鬼的出現(xiàn),必然會(huì)帶來(lái)一個(gè)或幾個(gè)男子的暴斃。作者描述她們時(shí),還敘述出她們幻化為惡鬼的原因。例如,字里行間夾雜著一種復(fù)仇的思想,可能表達(dá)了作者想借用女鬼形象來(lái)懲惡的意圖。但這類(lèi)女鬼,非但不會(huì)引起讀者的恐懼,反而會(huì)讓讀者因女鬼的悲慘經(jīng)歷而對(duì)其產(chǎn)生憐憫之心[6]。當(dāng)女鬼大仇得報(bào)之后,讀者必定會(huì)拍手稱(chēng)快,一掃胸中的惡氣。這類(lèi)女鬼,雖然兇惡,卻也極受讀者歡迎。
第三類(lèi)是賢媳良婦般的善良女鬼。《聊齋》和《子不語(yǔ)》的她們,生前是家庭的主婦,為一家人操勞不已;死后,依然念念不忘家中之人,或者為家人刷鍋?zhàn)鲲垼蛘邽樽约旱恼煞驅(qū)ひ捔寂技丫墸蛘哂H自以鬼魂之軀為丈夫生育子嗣,使得夫家香火綿延。這類(lèi)女鬼,是古代勤勞的婦女形象的化身,是生息艱難的人們對(duì)于生活美好的憧憬,是人間一切美好的總說(shuō),代表了作者心中所念的人間真善美。
第四類(lèi)是年輕貌美的善良女鬼,是四部筆記小說(shuō)都為之津津樂(lè)道的。她們多半多才多藝、性格大方,一心追求自己的理想愛(ài)情,更能為所愛(ài)之人竭盡所能。她們?cè)诓煌淖髡吖P下有不同的形象,更有不同的住處和不同一般的喜愛(ài)。但卻都有著與作者相近的愛(ài)和憎惡,有著與作者相同的人生哲理與追求。除卻性別,可看作是作者自身的形象。
蒲松齡筆下的她們總是在青燈孤舍之下和落魄書(shū)生相遇,在大膽而直白的表白之后,便堅(jiān)決地和他相伴在一起。或談人生、或談理想、或者進(jìn)行甜蜜的愛(ài)情交流。之后,那些落魄書(shū)生們便有如神助一般摘取桂冠、登壇拜相。而女鬼們或還陽(yáng)復(fù)蘇,或?yàn)闀?shū)生另覓佳偶,或便廝守在書(shū)生身邊,結(jié)局團(tuán)圓完美。
長(zhǎng)白浩歌子筆下的這類(lèi)女鬼變成了大膽追求愛(ài)情的象征,男子的榮耀與事業(yè)反而成了一種陪襯。女鬼和男子在一起琴瑟和合、詩(shī)詞唱和,更有內(nèi)中美妙不可言喻。這類(lèi)女鬼最終化身為人,或還陽(yáng)、或附體、亦或自成肉身。最終是繼續(xù)和心愛(ài)的男子幸福地在一起了。
袁枚、紀(jì)曉嵐筆下的她們,二者間或有之,但不如蒲松林和長(zhǎng)白浩歌子二人那樣形象鮮明罷了。這些區(qū)別也與幾人的生活際遇息息相關(guān)。
蒲松齡一生窮困潦倒,一身才識(shí)無(wú)人賞識(shí),只能寫(xiě)一些發(fā)憤之作已派遣心中的凄苦悲涼。現(xiàn)實(shí)中的他,自然無(wú)法獲得一個(gè)完美的愛(ài)情,便以自己為版本刻畫(huà)出一個(gè)個(gè)落魄書(shū)生的模樣[7]。讓一個(gè)個(gè)女鬼去接近這些書(shū)生,無(wú)非是為了圓自己一個(gè)不能實(shí)現(xiàn)的夢(mèng)罷了。而長(zhǎng)白浩歌子,則家境殷實(shí),一生經(jīng)歷的是風(fēng)花雪月,所見(jiàn)的多情女子自然不少。故其作品大多是一些愛(ài)情故事,只是自己誓言續(xù)寫(xiě)聊齋,作品才增添了一絲鬼魅色彩。袁枚和紀(jì)曉嵐,則沒(méi)有上面二人的生活豐富,自然也寫(xiě)不出多少婉轉(zhuǎn)動(dòng)人的愛(ài)情故事來(lái)。
四、結(jié)語(yǔ)
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身份際遇,造就了不同的女鬼形象。但作者們不同的創(chuàng)作目的和寫(xiě)作手法使得一個(gè)個(gè)豐滿的女鬼和其傳奇故事活躍在眼前,讓我們?cè)谔摌?gòu)與現(xiàn)實(shí)之間行走。
參考文獻(xiàn):
[1]蒲松齡.聊齋志異[M].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出版社,1998,298-300.
[2]劉隱溪.焚香品茗話“女鬼”[J].飛(奇幻世界),07(1),62-67.
[3]長(zhǎng)白浩歌子.螢窗異草[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76-98.
[4]紀(jì)昀.閱微草堂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236.
[5]黃治.《聊齋志異》與宗教文化[M].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出版社,2005,37-49.
[6]鄭春元.《聊齋志異》中女鬼形象的文化意蘊(yùn)[N].十堰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3(3),18-23.
[7]王磊強(qiáng).淺析《聊齋志異》中的女鬼形象[N].西安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3(1),82-86.
作者簡(jiǎn)介:白凈義(1990-),女,河南省周口市西華縣人,華中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yǔ)言文字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