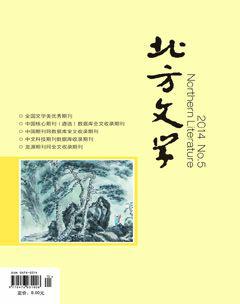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理想女性”觀念探討
摘 要:近些年來,觀念作為一個學術術語被廣泛應用。觀念作為語言文化學的重要范疇,被視作語言文化的核心,是人的意識中文化信息的凝結,更是連接語言和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本文主要對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理想女性”觀念進行分析,以期了解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質。
關鍵詞: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理想女性
一、語言文化學術語“觀念”的相關理論闡述
(一)語言文化學闡述
上世紀九十年代,語言文化學逐漸在俄羅斯形成,其跨越語言與文化兩個學科,其以文化理解與闡釋作為目的,把語言看作是本體的存在,對語言所表達的文化信息進行研究,揭示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本質特征[1]。
(二)語言文化觀念理論闡述
語言文化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其主要研究語言中固化的與表達的民族文化信息。在語言文化學的研究過程中,學者與專家們逐漸發現,語言不僅書寫著一個民族的歷史,并且通過觀念詞傳承民族精神、影響民族的文化行為。因此,學者與專家開始將語言文化學的研究切入點轉移到對一個民族文化觀念詞的研究上。
俄羅斯語言學界第一個提出“觀念”這一學術術語的學者是蘇聯時期的阿斯科爾德夫。阿斯科爾德夫認為,觀念是在快速言語行為和對語詞理解過程中出現在人的腦海中的、難以捕捉到的、一閃即過的東西,具有意識活動特點[2]。觀念是語詞和含義之間的媒介,是具有替代作用的智力構成物,用來替代某種事物或者具體認識。
二、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理想女性”觀念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中主要描寫了多莉、安娜等女性的家庭生活,主要從多莉、安娜的外在形象、心理活動、家庭觀念對其進行了人物刻畫,并借助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對2位主人公的客觀評價,為讀者呈現出了作者托爾斯泰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觀念。
(一)傳統型“賢妻”多莉
在《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卷首“奧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亂了”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象征著當時的社會環境,其在自由主義思潮與新社會制度的沖擊下,人們的生活一切都亂了。奧布隆斯基因為妻子多莉過早的色衰,開始到處尋花問柳,導致家庭生活與夫妻關系日益緊張,從而為《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書序拉開了帷幕。在奧布隆斯基家的日常生活中,為讀者展現了一位恪守婦道、抑制自身個性與思想并富有自我奉獻犧牲精神的傳統型“賢妻”多莉的女性形象。在奧布隆斯基的心目中,多莉只是一個容顏已逝、忙忙碌碌、整天料理家務并照顧孩子但毫無魅力的賢妻良母。但是托爾斯泰對這位恪守婦道、抑制自身個性與思想并富有自我奉獻犧牲精神的傳統型“賢妻”多莉進行描寫的過程中,并沒有褒揚之意,特別是在對多莉的人物形象進行描寫的方面。多莉那曾經豐滿美麗現在卻稀疏了的頭發、那雙干瘦發黃的雙手、憔悴的容顏再加上多莉發脾氣時的粗野喊叫聲,都令讀者為多莉感到憐惜與憐憫,更加對再也無法獲得丈夫奧布隆斯基疼愛的多莉產生了幾分同情。多莉在這種無愛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是不幸與痛苦的。但是隨著多莉年齡的增長與歲月的無情流逝,多莉已經無心再去裝扮自己,任憑歲月的洗禮,再也無法獲得丈夫奧布隆斯基的疼愛。多莉獨自一人承擔生活的重擔,特別是多莉在鄉下生活的那段時間,她要一個人在鄉下帶著6個孩子,并獨自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家務已經成為多莉唯一能夠排解憂傷、獲得幸福的途徑。多莉,正是中世紀保守的、傳統型理想妻子的人物形象代表。多莉在婚后已經成為了家庭生活的奴隸與生育子女的機器,一味的犧牲,傾其所有。雖然多莉也對自己的婚姻生活產生過質疑,幻想著拋夫棄子和情人一起過快樂的日子。但是恪守婦道、天性懦弱、逆來順受、有著虔誠宗教信仰的多莉不敢也不會違背、反抗自己的不幸命運,即使是在多莉知道丈夫奧布隆斯基背叛自己、對安娜的叛逆羨慕不已的時候,多莉還是依然固守著家庭的忠貞與責任。但是,多莉這種傳統型“賢妻”的人物形象并沒有博得作者托爾斯泰過多的青睞,托爾斯泰對多莉的態度并不是褒揚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隨著世俗社會在自由主義思潮與新社會制度的不斷沖擊下,日益開放的新社會日常生活需要的并不是中世紀的傳統賢妻類型,托爾斯泰更加看重女性的外表與心智素養,婚后不注重儀表、頭腦簡單的傳統“賢妻”多莉顯然不是托爾斯泰所向往的“理想女性”形象。
(二)墜入情網并忍受愛情折磨的安娜
安娜同樣生活在無愛的婚姻生活中,安娜將更多的愛傾注于自己的兒子。安娜除了應付社交活動以外,操勞家務、照顧兒子已經成為其生活的全部。雖然安娜和多莉都被日常生活所拖累,但是不同于多莉的是,安娜是迷人的,她是彼得堡社交界人人稱贊的貴婦人。面對著眾多傾慕者的追求,安娜在一開始和多莉一樣,恪守婦道,固守著對家庭的忠貞與責任。但是安娜不同于多莉的完全喪失自我與一味的犧牲,安娜非常注重自己的衣著與打扮,讓安娜保持著獨特的魅力。這也許和人的教育素養、治理素養、個性有關,安娜的迷人魅力不僅僅在于她的端莊、美麗的容顏和豐滿的肉體等外在特征,更多的在于安娜內心飽滿的精神與活力。當多莉和安娜相見時,多莉也不禁為安娜那美麗、健康、魅力的外表而心生嫉妒。安娜的美正如基蒂所說:“令人注目的是安娜的本人,單純、自然、優美、同時又快活又有生氣[3]。”當然,安娜的這種賢妻形象也不禁讓作者托爾斯泰所傾倒,這從托爾斯泰對多莉與安娜人物形象的細節刻畫可以看出。由此可見,托爾斯泰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不是不注重儀表舉止的多莉,而是安娜,這體現出作者托爾斯泰“理想女性”觀念中對上流社會女性在社交活動中追求外在美的肯定,是對自彼得大帝改革社會生活西化后人們對女性審美取向改變的繼承。
端莊美麗的安娜令伏龍斯基公爵一見傾心,展開了對安娜的追求與示愛。一開始,安娜感覺伏龍斯基的示愛令其感到羞愧,她一直遵守著宗法制社會的家庭傳統,被社交界視為敬重的對象。但是在伏龍斯基公爵的追求攻勢下,安娜開始發現自己一直在欺騙自己,伏龍斯基的追求并不讓她感到討厭,反而成為安娜的全部生活樂趣,并深深的愛上了伏龍斯基,最終安娜鼓勵勇氣向虛偽的上流社會發起挑戰,和伏龍斯基走到了一起,并向自己的丈夫坦誠了自己的不忠。但是沒有情感的卡列寧為了顧及自己的尊嚴和顏面,甘愿忍受和不忠的妻子安娜一起生活,而安娜也出于對自己兒子的愛以及對社會地位以及名譽的珍惜,也接受了卡列寧一切照舊生活的要。安娜開始在丈夫與情人之間游走,獨自忍受著精神折磨。向往著浪漫情懷與自由的安娜,受盡了無愛婚姻的生活之苦,為了可以自由、大膽的戀愛,安娜最終犧牲了自己曾經非常珍惜的一切,選擇了曾經為她殉情自殺的伏龍斯基公爵,走上了拋夫棄子、投奔情人、遭人鄙夷的非法生活道路。
自此,不顧社會輿論壓力、沖破婚姻枷鎖、勇敢追求愛情的安娜徹底和社交界絕緣。即使放蕩不羈的培特西也不愿意和安娜來往,因為她認為只有安娜和伏龍斯基結婚才能承認安娜的社會地位。自此,作者托爾斯泰對安娜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日益凸顯矛盾性。要愛情、要生活的安娜,其此時的唯一生活目標就是要牢牢的抓住伏龍斯基的心,安娜不惜利用自己美麗、迷人的外表去誘惑別人來達到引起伏龍斯基公爵注意的目的。借用小說中人物列文與基蒂的口吻,托爾斯泰道出了此時期對安娜美麗、迷人外表的憎惡,“那是一種魅惑,是罪惡的,安娜是一個墮落的女人[4]。”但是安娜這種強烈的欲望對于原本出于向外界炫耀、顯示自己的魅力才追求安娜的花花公子伏龍斯基來說,這只是愛情的枷鎖,導致伏龍斯基被壓的喘不過氣來。最終,安娜和伏龍斯基由愛人轉向了敵對。自此,安娜徹底被這種強烈的情欲所毀滅。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下卷中,作者托爾斯泰為讀者描繪了一個奢侈虛偽,對自己女兒漠不關心但收養馴馬師的兒女并假裝很喜歡的女性形象,而且托爾斯泰對安娜的寫作工作也表現出了輕視。雖然,作者托爾斯泰在中下卷將安娜性格中的不完美一面淋淋盡致的展現在讀者的面前,但是安娜的博學與聰慧還是得到了伏龍斯基與列文的肯定。安娜身上所具備的良好教育素養不僅是她的兩人丈夫所欣賞的,也是作者托爾斯泰也向往的。綜上所述,作者托爾斯泰對女性的愛恨交織態度很好的在安娜的身上得到了集中表現,一方面托爾斯泰渴望安娜的外表美,另一方面又非常的恐懼與抵抗;托爾斯泰在貶低、懲罰安娜的同時,又對安娜較高的教育素養與端莊的氣質稱贊有加;托爾斯泰在肯定安娜追求個性、追逐愛情與渴望新生活的同時,其又無法容忍安娜對家庭的背叛。但是總體而言,相比多莉,托爾斯泰更加傾慕于安娜那美麗、端莊的外表以及她婚后依然注重打扮、儀表以及博學、聰慧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托爾斯泰承認了女性的個性特征,并將女性的個性特征視為“理想女性”必備的內在修養與迷人魅力,這也體現出托爾斯泰對18世紀上流社會“理想女性”觀的發展。托爾斯泰主張妻子要在不傷體統的范圍內張揚自己的個性,保持自身魅力與旺盛的生命力,活出自我,而不是為了家庭一味的犧牲自己,成為“家庭奴隸”,而在這一點上,安娜起到了非常典型的示范作用。但是安娜并沒有得到其所期望的幸福,因為她和伏龍斯基公爵的愛情和家庭的責任是相悖的,而且還夾雜著虛榮心與享樂主義,使得原本獨立、自我的安娜最終再次淪為情人的“無條件奴隸”,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點。
三、結論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命運多舛的民族,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具有一種厚重感,要想理解俄羅斯民族,必須要依靠它的民族精神。而俄羅斯民族“理想女性”觀是其民族精神的一個縮影,在“理想女性”觀的形成過程中包含著俄羅斯民族心智的基本形態,也體現出了俄羅斯民族精神與其自然、社會、歷史、宗教、美學的層層關聯。本文以語言文化化作為研究視角,對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理想女性”觀進行了分析,體現出了俄羅斯民族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其“理想女性”內涵的變化以及俄羅斯民族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現為對妻子言行舉止、外在儀表、教育素養等方面期許的提高,但是這些變化還是要以家庭服務為中心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繼承的還是中世紀傳統“理想女性”觀的宗教性特征,只是在對妻子的言行舉止、教育素養、個人魅力、思想獨立、美麗外表方面有所發展,但是這也只是為了妻子可以更好的服務家庭、相夫教子。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托爾斯泰不褒揚傳統型“賢妻”多莉,贊賞安娜的美麗與博學智慧,但又無法接受安娜背叛丈夫、拋夫棄子的行為了。
參考文獻:
[1] 張婷.列夫·托爾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形象的悲劇意識透析[J].林區教學. 2011(10)
[2] 李吉.再議安娜·卡列尼娜[J].作家. 2013(06)
[3] 楊欣.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剖析[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2014(02)
[4] 鮑濤,倪曉春.永恒的彗星之光——談安娜·卡列尼娜文學形象的塑造[J].池州師專學報. 2013(04)
作者簡介:阿依努爾·塞都, 女, 哈薩克族,新疆伊犁師范學院外語系教師,新疆大學外語學院俄語專業碩士,在伊犁師范學院外語系從事俄語教學,主要研究方向為俄語翻譯及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