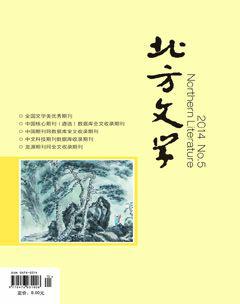人生兩端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人生》是路遙的一部中篇小說,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后,曾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以下,我將通過三個不同的方面,對《人生》這部電影和它所根據的文本進行比較分析:
一、電影語言用自然的符號寫成,這就意味著,電影“用現實表現現實”,它通過外在的形象直接作用于讀者的感官,是一種造型藝術,具有外在性、直觀性。而文學作品的特點卻是用文字“書寫現實”,通過敘事和行為作用于讀者的心靈,是一種思考的、內在的藝術。相對于電影詞匯中語言單位都是可見可聞的實體,文字確實一種抽象的符號。在電影藝術中,日常生活語言的多義性和曖昧性被抽除,代之以單一性和確定性。
我們試以下面的片段為例進行分析:“農歷六月初十,一個陰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熱鬧紛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來……天悶熱提像一口大蒸籠,黑沉沉的烏云正從西邊的老牛山那邊鋪過來。地平線上,已經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閃電,但還沒有打雷。只聽見那低沉的、連續不斷的嗡嗡聲從遠方的天空傳來,帶給人一種恐怖的信息——一場大雷雨就要到來了。
小說開頭出現了這樣一段環境描寫,而在電影里,這樣的一段環境描寫卻被代以局部的影像:外面大風大雨撲打著窗戶,窗戶上的貼紙被吹得嘩嘩作響。繼而鏡頭就轉入了高加林的家里。勞拉?穆爾曾經說,“好萊塢電影中的局部特寫破壞了由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和諧、完美的美學傳統!由于電影只用攝像頭講話,單敘述窗口為展述帶來了很大的不便。”而文學語言中“熱鬧紛繁的大地”“急躁不安的等待”“悶熱得像一口大蒸籠”這樣多義性、形象性、韻味性的詞語,完全不能通過鏡頭進行表達。文學語言是想象性的,而作為電影的影像卻是直觀性的。閱讀文學作品是調動的是我們的思維,進而控制感官系統,達到通感的目的。而我們在閱讀電影畫面的時候,卻是先通過視覺、聽覺感官的作用,因而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信息的喪失為內容的豐富性帶來了很大的缺陷。
二、電影在表現人物復雜的內心和深邃的思想意蘊時不如文學作品來得靈便,內涵的表現力就完全依附于演員的個人表演了。而文學作品的優勝之處,更是值得標榜的地方,就在于對人物的內心描寫。讀者與作品中的人物屬于直接的對話,更或者說,讀者通過自身的介入,將自己人物化,與人物間是零距離接觸,人物等于讀者自己。在決定與巧珍分開的時候,高加林有了一段極度矛盾的心理活動,“他反復考慮,覺得他不能為了巧珍的愛情,而貽誤了自己生活道路上這個重要的轉折——這也許是決定自己整個一生命運的轉折!不僅如此,單就從找愛人的角度來看,亞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他雖然還沒和亞萍像巧珍那樣戀愛過,但他感到肯定要更好,更豐富,更有色彩! 他權衡了一切以后,已決定要和巧珍斷絕關系,跟亞萍遠走高飛了!當然,他的良心非常不安——他還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蛋!……”
在電影中高加林的這一段心理描寫被虛化了,而情節的推進把這段富有表現力,最能突出人物性格的描寫擠壓掉了。觀眾的情感體驗被削弱,而接踵而來的下一個畫面,讓這段心理活動省略,從而,對于整個人物性格的 認識和把握不能像文本一樣來得真切和反復感受。
三、電影語言的空間構成方式是視覺形象產生了“第二表現層”:同一個形象不同的空間地位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而文學語言中單一的符號空間位置永遠是既定的,它沒有“第二表現層”。在這個方面上講,電影無疑占據了絕對的優勢,我們以小說和文本的結尾做一番比較,“當他從公路上轉下來,走到大馬河灣的分路口上時,腿猛一下子軟得再也走不動了。他很快又想起,他和巧珍第一次相跟著從縣城回來時,就是在這個地方分手的——現在他們卻永遠地分手了……”
而在電影表現里面,從正面的鏡頭給了高加林的面部一個表情特寫,他的形象充滿了整個畫面,背景是冬季荒涼的黃土地。進而是從高加林的視角出發,環視了一下他曾經拋棄的黃土地。最后切換到一個遠鏡頭,展現高加林落魄的背影和遼闊的黃土高原,這兩者的對比顯得特別突出。
就文本而言,高加林的位置是平面化的;而就電影而言,它的三維化程度給觀眾帶來的視覺沖擊很大,將高加林的悔恨、無奈、自責、內疚等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電影產生的視覺的“第二表現層”,即面部特寫和遠鏡頭的描述表達出的意義也是不同的。在面部特寫鏡頭中,突出的是高加林的個人情感,而在遠鏡頭中,更多的是代表一種似乎是永恒的結局——農村的孩子不能走出農村,在這片土地上,他們只能默默地留守。高加林的故事只是千千萬萬名向城市進發的農村孩子的縮影,而這種蒼涼,這種永遠無法突破的循環——從土地出發再回到土地,就是他們的命運,沒有例外,沒有特殊。
作者簡介:何家樞(1989-),男,漢族,廣東汕尾人,在讀研究生,南京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方向:文化研究、拉美文學。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