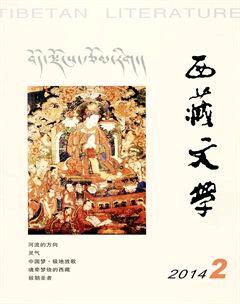時間的舞蹈
魏春春
摘要:以次仁羅布作品的敘述時間為研究對象,展現了其線性時間的敘述、時間的回溯敘述和時空交織的敘述時間類型,及其敘述時間三段論和自傳式敘述的時間敘述特點,以探究次仁羅布敘述時間意識的生成。
關鍵詞:敘事時間類型敘述時間三段論 自傳式時間敘述
一
截止到2012年,次仁羅布共發表小說作品23篇。就其作品的敘述時間類型而言,主要包括線性時間的敘述、時間的回溯敘述和時空的交錯敘述。
線性時間的敘述是一種傳統的時間敘述方式,主要按照物理時間的推進來展開故事的情節,書寫人物的成長史或心靈史,更多的帶有歷史敘事的文化特性。次仁羅布此一類型的敘述作品主要包括《秋夜》[1]、《放生羊》[1]、《神授》[1]、《塵網》[1]等作品。這幾篇作品的敘事時間都有明顯的時間起點。《秋夜》的敘述時間起點是“一個秋月高懸的晚上”,既點明了時節是秋季,又注明了時序是晚上;《放生羊》的敘述起點是年扎老人的一場噩夢,“這聲叫喊,把我從睡夢中驚醒……睜眼,濃重的黑色裹著我……我坐起來,啪地打開電燈”,這一系列前后相續的動作為故事的發展奠定了時間基礎,故事的時間是從凌晨開始的;《神授》中的敘述時間更為明確,“這是公元一九七九年發生的事”;《塵網》的敘述時間起點是“夏季正午”。明確的敘事時間意味著作品以這些時間節點作為作品中人物活動的起點,滲透出一種強烈的當下性的時間特點。線性時間是流逝性的,伴隨著這一進程的是人物生命經驗的生成和生命歷程的形成;而物理時間是確定性的,以明確的刻度標明時間的線性流程。因此,在這幾部作品中,次仁羅布著重展現的是以確切的刻度式的物理時間為標志的線性時間的不可重復性。故此,《秋夜》中的次塔為了擺脫心中的壓抑選擇了進入林場工作,而在“第三年的秋分時節,他把破爛的被子捆好,懷著依戀的心情告別了與他共度三年的強巴,告別了松瓦林場”,這一句話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次塔在松瓦林場工作了三年,在進入松瓦林場共經歷了兩次秋分時節,在第三年的秋分時節選擇了離開;同時,這句話也意味著三年與世隔絕的林場生活蕩滌著次塔的心靈,他已經走出了心理的可怕陰影,決絕地告別過去要開始新的生活。而這一切,次仁羅布都是借助刻度式的物理時間標明和完成的。
時間的回溯敘述主要是立足當下對過往人類經驗的復述,呈現出當下與過往的時間交錯。這類型的作品在次仁羅布的小說中占據絕大多數,如《羅孜的船夫》[1]、《焚》[1]、《前方有人等她》[1]、《德剁》[1]等。這類型的作品也都有明確的敘述時間起點,但不同于線性時間敘述的是這些作品是以回顧過往經驗或生命史為主。因此,敘述時間節點時間有多個,游離在當下與過往之間,帶有某些意識流小說的印記。如《羅孜的船夫》就有兩條時間發展線索,一條是過河的人們在百無聊賴中等待著渡船,為了打發時間而講船夫的故事;一條是船夫的故事。從形式上看,這兩種敘述時間都是依照線性時間的邏輯敘述的,是兩種生命印跡的迂曲表達,但究其實質,是通過船夫的故事表達一種人文情懷,是在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生活方式的交錯與糾結中藏民族的的文化心態,既包括船夫的固執于傳統的生活模式,也包括康巴商人游商的傳統習俗與現代文化的多方面接軌,還包括船夫女兒在康巴商人對外界世界的描繪中的向往與出走,甚至也點染出現代文明對船夫生活的摒棄與蔑視等等。在《羅孜的船夫》中,兩種生命史交織在一起構建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圖景。而在次仁羅布的時間回溯敘述中,時光的穿梭還體現在現實與記憶的不斷分離,現實的生命史不斷地回復到記憶中,記憶的生命史又在現實的某種召喚中被不時地打斷而停頓,以《焚》為例,維色在“七月的一個星期六”與兒子晉扎團聚,享受天倫之樂,同時也開始回憶:
維色的后背被太陽照得暖融融,一股倦意慢慢涌到周身。這種溫暖使她的思想平靜了下來,令她自己也覺得驚訝。她要乘著這份難得的清靜,梳理一下自己走過的那些個感情歷程。
由兒子的活潑可愛引發維色對自己情感選擇的反思,在溫暖的陽光映照下,維色內心的堅冰開始融化了,她開始整理自己的情感歷程。如此,次仁羅布很自如地實現了對維色過往情感歷程的回顧,從現實走向了回憶;而在時間的回溯中,由于兒子晉扎的參與,維色兩次停下回憶回到現實。如此,次仁羅布就在現實中的短暫歡樂與回憶中的無盡憂思中刻畫了現代都市女性維色的情感歷程。另外,次仁羅布在回溯敘述中偏于側重人物的夢幻記憶,無論是夏辜老太太臨終前的回憶,還是德剁嘉央中彈后意識混亂中的敘述,都是一種無意識的時間回溯,都展現的是這些人物生命軌跡中無法釋懷的情感或生活情結,這種過往生活的情結時時激蕩著、沖擊著作品中人物的現實生活,于是現實的確定的意識生活與過往的虛幻的記憶之間形成一種張力,從而完成作品的時間敘述。
時空的交錯時間敘述,這是一種多聲部的敘述時間,就是多個人在線性時間中敘述同一個或同一種類型的故事,在其中傳說與現實糾結,歷史與當下交錯。次仁羅布此類型的作品包括《殺手》[1]《傳說》[1]和《阿米日嘎》[1]等。《殺手》是司機、茶館姑娘、羊倌、瑪扎妻子四個人講述殺手的故事,每個人的經歷和敘述都是自我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非常短暫的瞬間,而司機的追尋則作為線性時間發展線索將四個人的敘述串聯起來,空間場域的轉換與線性時間的時空交錯勾勒出殺手的生命史或者說是心路史;與《殺手》的時間模式建構類似的是《阿米日嘎》,警察接警的簡單案情了解,撿牛糞農婦的旁觀敘述,村主任普瓊的案情匯報,報案人貢布的案情描述,嫌疑人噶瑪多吉的案情記錄,證人洛桑的證言資料,都在線性時間中敘述然堆村一頭種牛的死亡情況,時間都是2006年10月25日這一確定的物理時間節點,在眾人的敘述中既有關于案情發生具體情況的敘述,也有不同人對于種牛及與種牛有關聯的各種人的不同態度,就從回憶而言,既包括當天時間的回溯,也包括對種牛過往記憶的回溯。因此,從物理時間節點而言,就有四個,貢布購買種牛的今年夏末,今年夏末到種牛死亡當天的時間歷程,種牛死亡當天的情況,及眾人在種牛死亡后的敘述與行為,這四個節點貫穿起敘述的整個過程,建構起在然堆村以種牛為中心的各種人的生命歷程和心路發展。在多聲部的敘述時間中,最具有特性的是《傳說》的敘述時間模式建構,強久老頭敘述幾十年前歸還霞帝寺鎮寺之寶金剛橛的經過,蓄長頭發的老師講述薩迦班智達以金剛杵戰勝外道的故事,胖老師講述熱振活佛去世后一個叫人壽十歲的藏兵的故事,“翌日。黃昏。酒館”中酒客們談論前一天“那個農民小伙子”死亡的故事。就敘述的時間而言,是“冬日的白晝極短,不到下午六點半,”和“翌日。黃昏”兩個物理時間節點;就所敘述的故事時間而言,分別是以薩迦班智達二十七八歲,熱振活佛去世后,強久老頭幾十年前,“那個農民小伙子”在“昨天晚上”等作為時間起點的,可以說,時間穿梭在傳說與現在之間,地點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而眾人所講的故事也是各不相同的,唯一一致的就是經過高僧大德加持過的“金剛橛”和“金剛杵”的“刀槍不入”護持人身的“金剛”性。在時間與空間的多重建構中,在傳說與代表現代知識的幾位老師的敘述中,“那個農民小伙子”堅定了對“金剛杵”的信念而慘死。多聲部的敘述時間不僅把多個看似毫無關聯的故事連綴在一起,豐富了敘述內容的厚度和廣度,而且在敘述的線性時間過程中再現了不同類型的個體的生命感受和體驗,極大地拓展了敘述內容的強度和力度。
二
次仁羅布的敘述時間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敘事時間三段論。從物理時間的角度而言,時間包括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作為時間經歷者的個體所能把握的只是現在,確切地說只有當下,包括當下的情緒,當下存在的空間和當下的境遇;作為時間經歷者的個體的過去,在思維序列中屬于記憶,無論是深刻的記憶印跡還是零星的碎片化的記憶痕跡,都是個體在生命時間中的過去式;而作為時間經歷者的個體的將來,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生命憧憬,或者可以說是根據當下的生命體驗和生命歷程而進行的將來時態的推測。在文學書寫中,現實主義類型的寫作者一般都是立足當下反思過去,以期通過在當下境遇中的歷史回顧來改進、完善、促進將來的生命進程;而在理想主義寫作者看來,過往可能是對當下生活樣態不滿的一種詩化表達,是一種生命的隱喻顯現,而將來可能是對當下某些進程的大膽假設,既包含著當下情態的必然化預測,也包括著當下情態的可然性變革。就次仁羅布的創作而言,他擅長在過往與現實之間穿越,習慣于立足當下展現藏民族文化心態的變遷歷程。因此,他的敘事時間三段論更多的是當下——過去——現在的時間構建模式。
以《雨季》[1]為例。這是次仁羅布小說作品中少見的苦難敘事之作。圍繞著一個不幸的家庭展開的。其中時間的當下性表現在旺拉背著亡父回家,一路上不停地和亡父做最后的交流,敘述家庭的苦難。旺拉講的故事包括小兒子格來的故事、妻子潘多的故事、大兒子崗祖的故事,這三個故事呈現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生命史。從這一點來說,這些故事是在物理時間序列中進行的,屬于過往的記憶;但就其順序而言,從物理時間而言,應該是潘多的故事在前,隨后是崗祖的故事,最后才是格來的故事,次仁羅布似乎打破了既有的物理時序,實際上次仁羅布遵循了另一種物理時序,就是死亡的先后順序。敘述者在作品中濃墨重彩地客觀冷靜地描敘旺拉的遭遇,讀者在旺拉的不緊不慢的敘事中,似乎能感受到旺拉所謂的“我知道人既然投胎了,就是經千年萬年的積善,終于修來的福報,哪能輕易放棄生命呢?……這一世無論經歷多少次的劫難,只要挺住,你不就是超脫了嗎,是對苦難的超越”的意味。在對家庭成員的敘述中,只有格拉的故事是最完整的,從出生到上學再到死亡,完整的生命史的展現;其他人如潘多、崗祖的敘述則屬于跨越式的。如潘多先敘述她在田地中分娩格拉的過程,再敘述她的悲慘死亡,然后才是她嫁給旺拉的場景,在強巴老爹的家暴中承認“你在我們家庭里的最高地位”,接著才是分娩崗祖的故事,就這一系列時間敘述而言,次仁羅布對潘多的敘述是分裂的,碎片的,點染式的,沒有遵循既有的物理時序,而是強行撕扯開來。這樣的時序安排既便于把潘多的命運置于家族整體敘事的序列,又突出了潘多的犧牲精神,就是一種忍讓的品格。而強巴老爹的生命敘述從整篇作品來看,以迎娶潘多為起點,以其經歷家人逐個死亡為時間順序的,以強巴老爹生命的結束為時間終點。因此,《雨季》中關鍵性的人物是潘多,以潘多為邏輯時間的起點展開了整個敘述。
在《雨季》中,時間的當下性就是旺拉的生命境遇,敘述者在回顧整個家庭的悲劇命運中展開他的時間性的線性脈絡。從背負著亡父返家的時間流逝中,旺拉也在心理時序中完成了他的物理時序的敘述過程。旺拉是唯一的當下性存在。因而,當“回到三村時”,旺拉完成了他的敘事功能,而成為敘述者眼中的他者存在,次仁羅布通過敘述人稱的變化顯示出旺拉的生命軌跡從某種意義上說,同樣是一種過去的回憶,立足當下的實際上只是敘述者。
實際上,次仁羅布敘事時間三段論貫穿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只有敘述者嚴格執行線性時間的敘述進程,而其他人物只是作為功能性的存在,為了實現整個作品的敘事,敘述者虛假地讓他們回到曾經的生命境遇之中,在他們看似真實的故事的物理時序的占線中,敘述者完成整個敘述。
三
次仁羅布時間敘事中另一個顯著地特點,表現在作品中心理時間的開拓,主要借助故事中人物的自傳式生命歷程完成的。相比較物理時間的流逝性及其空間的附著性而言,心理時間更多的不受線性時間的限制,也不受物理空間的約束,其時間敘述更加自由、時空轉換更為便捷;相比較于意識流動敘述的隨意和散漫而言,次仁羅布的物理時間敘述仍有其時間轉換的鮮明邏輯特點,采用的是時間遞進式的策略。因而自傳式的敘述與回溯式的敘述類型有相似之處,都是對過往的記憶的重新復現。但是,不同的是,自傳完全是一種線性的回溯,敘述主體沉浸在過往的回顧中,基本不受當下的現存的外界的干擾。因此,自傳式的敘述其實是時間三段論的一種變體,但又是次仁羅布試圖突破既定的時間三段論的一種嘗試。以《神授》[1]、《嘆息靈魂》[1]和《綠度母》[2]為例。
《神授》以放牧娃亞爾杰遭遇神授而會吟唱《格薩爾王》為自傳的起點,在線性時間流中,呈現了亞爾杰前半生的悲歡離合,而結尾處亞爾杰的兒時朋友多谷又在延續著亞爾杰的生命軌跡。在《神授》中,自傳已經開始出現端倪,但不是那么的明顯,而在《嘆息靈魂》和《綠度母》中,這種自傳的意味就非常濃郁。《嘆息靈魂》中易瓊為了緩解天葬臺上其他年輕人的緊張情緒,敘述了自己多年的生命經歷,從“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那年剛入夏,那時我正好十六歲。那天臨近中午的時候”的敘述的確定性作為心理時間的起點。在易瓊的自傳中,敘述的時間意識非常明確,以敘述的程序而言,先展現少年易瓊的經歷,再展現他在出走的路途中的空間轉換,從日郭村到縣城,再到昌都鎮,而后到林芝,最后抵達拉薩,完成了他的人生蛻變;以易瓊的心理變遷而言,由對精神的迷戀,到對物質生活的期盼與追逐,隨著親人的去世,引發他深重的人生思索,“死亡,讓我看到了以往我執著的那些個事情是多么的細小、無聊啊,為了那些我把青春都耗損掉了,我的人生在利益、爭斗、憤懣中殆盡。直到死亡,我的靈魂一直要帶著更多的怨恨和貪欲,直到無休止地輪回”。在易瓊自傳式的線性時間敘述中,易瓊完成了他的身體、心靈的成長史。相比較而言,《綠度母》的心理時間的開拓就更為深入,展現的已不是一個人的成長,是幾個人甚至一群人的生命成長史。在《綠度母》中,次仁羅布精心設置了羅布、丹增、巴桑、巴桑的父母親及爺爺的生命史,而實現這一歷程的方式是通過翻譯巴桑的自傳而實現的。通過巴桑的自傳,在時間流動中,作品呈現了以上幾個人物所代表的人群的心理特性,在實現自我救贖的過程中,巴桑也為其他人的自我救贖指明了方向。
因此,可以說,自傳式的時間敘述,糅合了次仁羅布一貫的時間建構的種種模式,既有線性時間的敘述、時間的回溯敘述和時空的交錯敘述等的時間敘述的類型,也有三段論式的敘述特性,即立足當下的線性時間敘述的起點,在時間回溯敘述中展現各色人物過往的時空交錯的生命歷程史,最終回到現在的心理時間狀態,呈現出一種光怪陸離的時間建構整體情態。若從時間的整體開拓而言,次仁羅布可謂是西藏文壇近年來最著力的一位作家,正是他強烈的時間意識敘述意識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在更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容納當代藏民族復雜而纖曲的世俗心態和文化情懷。
參考文獻:
[1]次仁羅布.界[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
[2]次仁羅布.綠度母[EB/OL].http://blog.sina.com.cn/cirennuobu。
責任編輯:次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