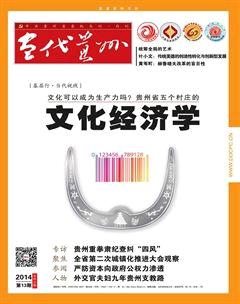赫魯曉夫改革的盲目性
蘇聯全面改革的序幕,嚴格地說, 是赫魯曉夫拉開的。當時,蘇聯面臨著十分復雜的局面。著名政論家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指出,斯大林所留下的蘇聯,除了強大的軍隊和先進的國防科技外,還有“越來越貧困的、實際上半崩潰的農村,技術上落后的工業,最尖銳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數百萬人被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與同期的其他領導人相比,赫魯曉夫較為清楚和明確地洞察了蘇聯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因此頂住來自黨內外、國內外的重重壓力,首先選擇了消除政治恐怖,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
赫魯曉夫傾注了最大熱情和精力的,是對斯大林時期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進行改革。赫魯曉夫認為,導致蘇聯農業落后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違反了物質利益原則。他一上臺,就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改變農業計劃,因為這個時期給予了農民更多的經濟利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明顯好轉。使l958年成為蘇聯農業生產有史以來的最好年景,也使他名利雙收,獲得了列寧勛章。赫魯曉夫也比較注意改善公民生活狀況,提高福利待遇。
但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的改革,盲目性還是很大的。在工業改革上,赫魯曉夫沒有認識到是計劃經濟體制管死了經濟,也管死了企業,生產者和經營者都缺乏積極性,而僅僅認為這是部門權力過于集中的結果。他把中央在物資、生產、工資等方面的很多權限下放給加盟共和國,把許多中央直屬企業下放給地方管理,還在全國設l05個經濟行政區,把以部門為主的條條管理改為以地區為中心的塊塊管理。改革有利于調動地方積極性,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作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地位問題,只是在隸屬關系上換了個新“婆婆”。老問題沒解決,又帶來“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泛濫的新問題。后來105個小經濟區被合并為47個,部分經濟權力又被中央收回,改革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赫魯曉夫在對外關系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主動恢復與南斯拉夫黨和國家的正常關系,承認社會主義各國可以從自身實際出發,選擇不同的發展道路,還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等。但他仍堅持與美國軍備競賽,并因把導彈偷運入古巴而差點引發世界大戰,在肯尼迪以核戰爭相威脅時又匆忙妥協讓步,被毛澤東抨擊為“先是冒險主義,后是投降主義”。
有人說,成功的改革,大致有兩種境界:一種是改革者經過了長期的深思熟慮,胸有成竹,一開始就確定了明確的戰略目標,但為了減少阻力而深藏不露。在實施過程中則是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由易到難,最終確立新的體制。另一種是改革者因為受自身眼界限制,拿不出明確戰略的目標,只能根據眼前需要和力量對比,謹慎從事,隨機應變,經過不斷探索,最終尋求到舊體制的替代物。赫魯曉夫的改革同第一種境界無緣,與第二種境界有些關系,但嚴格地說,他連第二種境界也未達到。他當政11年,可以說是改革的11年,除舊布新,進行了大量的改革。不僅涉及到黨政領導體制、干部、監察、司法等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也涉及到工業、農業、商業和財政等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可以說百廢俱興。他年年出臺新舉措,歲歲有新招數,讓人應接不暇;有的可以說獨具慧眼,精彩紛呈;有的雖有成績,同時夾雜著錯誤;有的很不徹底,前后矛盾;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明確的戰略目標以及正確成熟的指導思想,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旦面臨的迫切問題解決了,或者困難有所緩和,赫魯曉夫便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甚至不知不覺又轉回到老路上去。
應該說,赫魯曉夫盡管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主觀上未必是想搞竭澤而漁的“政績工程”,更多地還屬于“好心辦壞事”。赫魯曉夫改革的失敗,也是與赫魯曉夫的個性特點分不開的。蘇聯學者布爾拉茨基寫道:“赫魯曉夫不僅是環境的犧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犧牲者。急性子、過于匆忙、容易激動,這是他無法克服的缺點。”
赫魯曉夫改革的失敗,從根本上說,和他沒能從體制上懷疑和突破斯大林模式分不開。他本人是在斯大林時代成長起來的,被深深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盡管他不斷想出一些新點子,想改變蘇聯的舊貌,但他始終沒有脫離行政手段為主的經濟工作領導方法,用舊機制去推行新措施的典型做法,他更沒有從根本上觸動中央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