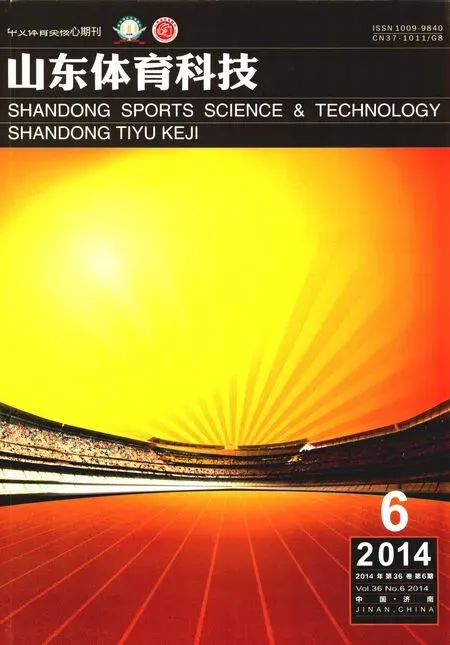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適應性、應對效能感與生活滿意感關系的差異
,
(1.合肥工業(yè)大學 體育部,安徽 合肥 230009;2.江西師范大學 體育學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適應性、應對效能感與生活滿意感關系的差異
袁同春1,邱達明2
(1.合肥工業(yè)大學 體育部,安徽 合肥 230009;2.江西師范大學 體育學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采用青少年適應性量表、應對效能量表和生活滿意感量表對大學生進行調查,探討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在適應性和應對效能之間的差異以及應對效能在適應性和生活滿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1) 除學習適應和生活適應的得分體育專業(yè)學生較低外,其余各變量均為體育專業(yè)大學生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得分高具有顯著性差異(plt;0.05)。2) 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生活適應對生活滿意感影響都是通過中介變量勝任力實現(xiàn)的;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只有一部分是通過中介變量認知水平實現(xiàn)的。即: 適應性與生活滿意感的關系受應對效能的中介影響,不同的專業(yè)特點的個體其作用路徑不同。
適應性;生活滿意感;應對效能;中介作用
近年來,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愈來愈突出,作為未來社會發(fā)展生力軍的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適應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的重要內容之一[1],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fā)展,必須促進青少年良好的適應性。不過,人們并不能徹底、迅速地適應所有環(huán)境,經常會出現(xiàn)適應慢或難以適應的情況[2]。
應對與適應不同,適應是消極被動的心理生理過程,而應對則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心理過程。應對效能是一種經驗的積累,又是一種個人面對壓力時采用的應對資源影。它通過影響人們如何評價應激性事件,支持問題解決為目標的應對意圖、計劃和發(fā)現(xiàn)改變威脅性情境的新方法來影響人們的應對。應對效能又有別于應對方式,前者是“人們對付應激特有的、具有個人特點的、跨情境的特質或風格”,屬于個人風格層面;后者是指“人們面對應激情境時采用的應對方式、方法或策略”,屬于應對技巧層面[3]。研究表明,處于應激狀態(tài)下,應對效能高的個體更有信心接受應激的挑戰(zhàn),從而維護自身身心健康[4];而且,運用某些應對策略的人其主觀幸福感水平較高[5]。
主觀幸福感反映主體的社會功能與適應狀態(tài)[6]。其中心概念是適應或習慣化,這種適應或習慣化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總是適時地調整自己的認知和情緒,從而保持對自己生活的相對滿意度[7]。作為主觀幸福感關鍵指標的一般生活滿意感,是個體基于自身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做出的總體評價[8],其評價的高低則取決于適應的程度以及應對效能的高低。由此可見,三者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關系:應對效能在適應性與一般生活滿意感之間可能具有潛在的重要作用。假設:1. 適應性與生活滿意感的關系受應對效能的中介(或調節(jié))作用影響。2.不同專業(yè)特點的個體具有不同的應對效能,進而影響其適應性和生活滿意感。目前,關于適應性與應對效能對一般生活滿意感影響的研究大部分只針對個別的因素單獨開展[9-11],而沒有進行系統(tǒng)的考察。本研究選擇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綜合個體的主觀和客觀因素對應對效能、適應性和一般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在橫向層面來探討它們之間的深層次關系,最終確定影響大學生一般生活滿意感的結構模型,更準確地解釋一般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因素及其它們之間的關系,為更好地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促進心理健康發(fā)展提供理論參考。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班級整群抽樣方法,于2010年12月在安徽省隨機選擇一所普通綜合性大學,從中抽取體育專業(yè)大學生201人(男120人,女81人),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263(男108人,女125人)人進行測量,收回有效問卷432份(體育專業(yè)200人,非體育專業(yè)232人),回收率93.1%。
1.2 測量工具
1)青少年適應性量表:通過張大均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調查表·適應分量表】[1]進行測量。該量表包括生理適應、情緒適應、人際適應、學習適應、社會適應、生活適應和總分7維度構成,含22個條目。本次測量的克隆巴赫α為0.71。
2)一般生活滿意感量表:一般生活滿意感采用Leungh和Leungh的【一般生活滿意感量表】[12]進行測量。該量表為7級李科特量表,共6個條目。本次測量的克隆巴赫α為0.79。
3)應對效能量表:應對效能量表是用來評估個體在面對應激情境時的應對效能,本問卷由童杰輝編制[3],全量表共17道題,分別為勝任力、認知水平、自信程度三個維度,采用5 點記分。該問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其克倫巴赫α系數(shù)為0.86。
1.3 統(tǒng)計分析: 運用SPSS 13.0 統(tǒng)計軟件中的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等方法對所得數(shù)據(jù)進行管理和統(tǒng)計,以Plt;0.05被認為是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及分析
2.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和相關系數(shù)
各變量的平均數(shù)、標準差及相關系數(shù)見表1。適應性和應對效能的各個維度與生活滿意感均有可靠相關(Plt;0.01)。

表1 總樣本各變量的相關矩陣
2.2 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各變量的比較分析
表2給出了不同對象的全部變量T檢驗的差異比較結果。我們看到,學習適應和認知水平兩個方面差異不具有顯著性(Pgt;0.05);除學習適應(Pgt;0.05)和生活適應(Plt;0.05)的得分體育專業(yè)學生較低外,其余各變量均為體育專業(yè)大學生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得分高具有顯著性差異(Plt;0.05)。
2.3 應對效能的中介作用
2.3.1 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選用溫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13],采用強迫進入法進行回歸分析, 用以考察青少年適應性和生活滿意感之間的關系是否以應對效能為中介。檢驗程序為:1)檢驗回歸系數(shù)c,如果顯著,繼續(xù)下面的第二步,否則停止分析。2)做 Baron 和Kenny[14]部分中介檢驗,即依次檢驗系a、b,如果都顯著,意味著X對Y的影響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中介變量M實現(xiàn)的,第一類錯誤率小于或等于0.05,繼續(xù)下面第三步。如果至少有一個不顯著,由于該檢驗的功效較低(即第二類錯誤率較大),所以還不能下結論,轉到第四步。3)做Judd和Kenny[15]完全中介檢驗中的第三個檢驗(因為前兩個在上一步已經完成),即檢驗系數(shù)c',如果不顯著,說明是完全中介過程,即X對Y的影響都是通過中介變量M實現(xiàn)的;如果顯著,說明只是部分中介過程,即X對Y的影響只有一部分是通過中介變量M實現(xiàn)的,檢驗結束。4)做Sobel[16]檢驗,如果顯著,意味著M的中介效應顯著,否則中介效應不顯著,檢驗結束。

表2 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各變量的比較分析
首先,我們以適應性為自變量,生活滿意感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學習適應(B=0.698,Plt;0.05)和生活適應(B=0.717,Plt;0.05)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作用(進入回歸方程);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人際適應(B=0.5,Plt;0.01)和情緒適應(B=0.508,Plt;0.01) 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作用(進入回歸方程)。以應對效能為自變量,生活滿意感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勝任力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作用(B=1.059,Plt;0.01),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認知水平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作用(B=0.463,Plt;0.01),其余各變量則沒有進入回歸方程(Pgt;0.05),提示后期作中介效應分析時應只對具有預測作用的變量進行分析。具體中介效應結果見表3、表4。

表3 體育專業(yè)學生應對效能中介效應檢驗的等級回歸


圖1 體育專業(yè)應對效能中介效應的示意圖

表4 非體育專業(yè)學生應對效能中介效應檢驗的等級回歸
由表4可知,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作用(B=0.508,Plt;0.01;B=0.5,Plt;0.01),即回歸系數(shù)c顯著;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認知水平 (B=0.379,Plt;0.01; B=0.237,Plt;0.01)的預測作用顯著,即回歸系數(shù)a顯著。另外,在引入認知水平作為預測變量后,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生活滿意感影響非常顯著(B=0.433,Plt;0.01;B=0.454,Plt;0.01),即回歸系數(shù)c′顯著,說明是部分中介過程。即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只有一部分是通過中介變量認知水平實現(xiàn)的。具體路徑圖見圖2。
2.3.2 中介效應的分解


圖2 非體育專業(yè)應對效能中介效應的示意圖

表5 應對效能在適應性與生活滿意感之間關系中的中介效應分解
3 討論
3.1 不同類別大學生各變量的比較分析
本研究顯示,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除學習適應和生活適應的得分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低以外,其余各個維度的得分都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高,且差異具有顯著性。說明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適應性和應對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高。已有研究證明,體育鍛煉能給參與者帶來情緒、人際關系、社會適應、生活滿意感等諸多方面的促進作用[17-18],也對提高兒童社會適應行為具有較好的效應[19-20]。本研究結果基本與上述結果吻合。
學習適應是由學習活動引起的心理和行為反應狀態(tài)。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學習適應得分較低。一方面,因為種種原因導致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文化基礎比較差,對于大學的專業(yè)知識學習存在一定的困難;此外,運動技術的訓練在客觀上占用了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可能使得學生的學習成績下降,最終影響學生的學習適應得分。但是,體育與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在學習適應方面差異不顯著,可能對所有大學生來說學業(yè)任務都是一個大難題,不存在專業(yè)差異。生活環(huán)境的變化會引起個體的心理和行為反應狀態(tài)。本研究調查的對象為綜合性院校的體育專業(yè)大學生,與體育專業(yè)院校不同的是,在綜合性院校中,體育專業(yè)學生的地位尚不盡人意,這是多種因素的結果。除學生自身的原因外,世俗的偏見也影響了人們對待此事的觀點。因此,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生活適應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低。應引起學校各有關方面的關注,確保每位學生的身心健康發(fā)展。在應對效能方面,體育專業(yè)大學生在勝任力、自信程度方面得分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高,而且差異具有顯著性。因為體育運動都是和人的緊張活動、競爭性以及克服各種困難相聯(lián)系。實踐表明,經常參加體育運動能培養(yǎng)人的意志力,使活動者具有勇敢、自信、頑強等性格特征。這也進一步印證了體育活動有利于人格發(fā)展的結論[21-22]。大學生的認知水平差異不具有顯著性,說明不同專業(yè)的大學生解決問題的努力程度以及采用積極的策略的可能性沒有太大的變化。
3.2 不同類別大學生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因素比較
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學習適應(B=0.698,Plt;0.05)和生活適應(B=0.717,Plt;0.05)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力。因為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文化基礎較差,來自學習方面的壓力是大學生活中主要壓力源之一。此外,作為綜合性院校的體育專業(yè)大學生,他們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不盡人意,經常面對別人異樣的眼光。這些因素對生活滿意感帶來一定影響。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勝任力對生活滿意感同樣具有預測作用(B=0.941,Plt;0.01)。鍛煉者會把在體育活動中獲得的處理各種困難的技能技巧以及信心遷移到現(xiàn)實生活當中,因此,體育專業(yè)大學生能以較高的勝任力接受應激和挑戰(zhàn),最終獲得較好的生活滿意感。
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人際適應(B=0.5,Plt;0.01)和情緒適應(B=0.508,Plt;0.01)對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力。由于適應新的生活環(huán)境以及自身特殊的生理心理發(fā)育階段的需要,決定了大學生更加渴求和諧的人際關系[23]。但是,調查表明大學生中人際關系問題非常突出[24-26],而且人際關系又是影響生活滿意感的因素[27],因此,困擾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對其生活滿意感當然至關重要。情緒對生活滿意感具有一定的預測效度[28],然而,年輕、易沖動的大學生偏偏對情緒難于控制,于是也成了影響生活的一大事件。此外,認知水平對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生活滿意感具有預測作用(B=0.463,Plt;0.01)。不同的認知評價對心理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29],生活滿意感本身也是個體對當前現(xiàn)實狀況作出的認知評價,因此,認知水平對于維持較高水平的生活滿意感具有積極意義。
3.3 應對效能在適應性和生活滿意感關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fā)現(xiàn),應對效能在適應性與生活滿意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這驗證了假設1。具體而言,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勝任力因素在生活適應對生活滿意感影響中起完全的中介作用,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認知水平因素在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生活滿意感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這驗證了假設2:不同專業(yè)特點的個體具有不同的應對效能。
綜合性院校中的體育專業(yè)學生,雖然因各種原因導致生活適應下降;但是,因專業(yè)訓練獲得的強烈的拼搏精神和自信以及較高的應對應激情境的能力,因而他們完全能夠通過出色的勝任力來調整低生活適應帶給生活滿意感的不良影響。此外,從差異分析的結果來看,盡管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學習適應和生活適應都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低,但是生活滿意感要高,而且差異具有顯著性,也可以認為是勝任力的調節(jié)作用。不過,勝任力在體育專業(yè)的大學生的學習適應與生活滿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并不顯著。經了解,相當一部分體育專業(yè)的學生,因基礎太差幾乎喪失了認真學習的信心,特別是英語課程,甚至有學生干脆就放棄了;此外,本研究還發(fā)現(xiàn)學習適應對勝任力應對效能(B=-0.035,Pgt;0.05) 起削弱作用,雖然作用不顯著,但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所以說,在學習方面,學生們因缺乏自信而影響他們在學習方面的應對效能,認為已經無法改變他們的學習成績狀況,也就無法通過學習成績的改善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滿意感。
Lazarus等人認為,在許多方面人們對事件的認知評價會影響他們對事件的反應[30],而人們心理反應的變化又必然影響其生活滿意感狀況。與體育專業(yè)不同的是,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每天花大量的時間進行認知、思維訓練,這個過程對其認知能力產生非常明顯的影響,因此他們習慣對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但是,為什么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對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只是部分通過認知評價的中介作用,而不是全部呢? 其可能的原因是情緒適應和人際適應兩個因素對大學生的生活滿意感太密切、太現(xiàn)實了,以至于無法通過這個中介因素得到較好的調節(jié)。
不同專業(yè)大學生在面應激情境時,為什么采用了不同的應對效能來調節(jié)?可能是專業(yè)的教育對學生產生深刻而長久的影響,由此形成一定的風格特征;而應對效能本身就是“具有個人特點的、跨情境的特質或風格”。按照教育要培養(yǎng)“復合型人才”的要求,復合型人才在面對應激情境時,其應對效能又將如何?這應該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4 結論
4.1 體育專業(yè)大學生的適應性和應對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比非體育專業(yè)大學生高。
4.2 適應性與生活滿意感的關系受應對效能的中介影響,不同的專業(yè)特點的個體其作用路徑不同。
[1]張大均, 江琦.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調查表-適應分量表的編制[J].心理與行為研究, 2006 ,(2): 81-84.
[2]Ed Diener, Eunkook M. Suh,e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3]童輝杰. 應對效能: 問卷的編制及其理論模型的建構[J]. 心理學報, 2005 ,(3):37-38.
[4]王建平, 李董平, 張衛(wèi). 家庭經濟困難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應對效能的補償、中介和調節(jié)效應[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22-32.
[5]譚春芳, 邱顯, 清李焰. 初中生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J]. 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 2004,18 (10) : 723-725.
[6]陳妹娟, 周愛保. 主觀幸福感研究綜述[J]. 心理與行為研究, 2003,1(3):214-217.
[7]吳明霞. 30年來西方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理論發(fā)展[J]. 心理學動態(tài), 2000,4:23-28.
[8]丁新華, 王極盛. 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研究述評[J]. 心理科學進展, 2004,(1):59-66.
[9]劉旺, 馮建新.初中生的學校適應及其與一般生活滿意度的關系[J].中國特殊教育, 2006, 6:77-80.
[10]劉衛(wèi)春.青少年的應對方式、應對效能與心理適應的關系[J]. 蘇州科技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7(2):75-80.
[11]董旭冉, 童輝杰.大學生應對方式、應對效能與心理健康的關系[J]. 社會心理科學, 2010 ,(25) 4:75-79.
[12]Leungh J P, Leungh K. Life satisfaction, self-concep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in adolescence [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2, 21: 653-665.
[13]溫忠麟,張雷, 侯杰泰,劉紅云. 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 2004,36(5):614-620.
[14]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15]Judd C M, Kenny D A. Process analysis: Estimating mediation in treatment evaluations[J].Evaluation Review, 1981, 5(5): 602-619.
[16]Sobel M E. Asymptot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A].In: S Leinhardt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2[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82. 290-312.
[17]晏寧.身體活動與身體鍛煉的情緒效應[J]. 北京體育大學學報, 2003,26(1):30-32.
[18]李京誠.身體鍛煉心理某些領域的研究綜述[J]. 北京體育師范學院學報,1999,1(3):42-47.
[19]陽海英, 張慶建. 體育活動對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J]. 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06,22(3):15-17.
[20]潘春燕.體育對兒童社會適應能力發(fā)展影響的研究[J]. 浙江體育科學,2008,30(1):28-32.
[21]張力為,李翠莎. 運動員個性特征的評價及其實踐意義[J]. 精英(香港體育學院學報),1993,11:17-24.
[22]Morgan, W. P., The trait psychology controversy[J].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1980, 51: 50-76.
[23]張厚粲主編.大學心理學[M].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
[24]張翔, 樊富珉.大學生人際沖突行為及其與心理健康的關系[J].心理與行為研究,2004,2(1):364-367.
[25]程艷林.大學生人際關系中的普遍性缺陷及產生的原因與對策[J].社會心理科學,2005,20(2):97-101.
[26]汪雪蓮, 許能峰.醫(yī)學生的人際關系困擾及其影響因素[J].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2005,19(4):247-249.
[27]張靈,鄭雪,嚴標賓,溫娟娟,石艷彩.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J].心理發(fā)展與教育, 2007,(2): 116-120.
[28]王春花.大學生情緒調節(jié)方式與生活滿意度研究 [D]//華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007.
[29]張向葵,柳楊,田錄梅.認知評價與心理控制感在中年人對社會政策變化感受與心理健康之間的作用[J]. 心理發(fā)展與教育,2006,(4): 91- 96.
[30]Lazarus R 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M].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287-327.
Difference among adaptation, coping efficac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PE and non-PE students
YUAN Tong-chun1,QIU Da-ming2
(1. Dept. of P. E.,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Anhui, China; 2. School of P. 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Jiangxi, China)
Through using the adaptation scale, coping efficacy scale and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this pap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among adaptation, coping efficacy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 on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between adaptation and coping efficacy.Results:1) The score of study adaptation and life adaptation of sport major students is lower, but the scores of other variables are much higher than college students of non-sport majors. 2) There ar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adaptation and coping efficacy on sport major students, and there are part mediating effect among emotional adaptation,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of non-sport major. There ar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adapt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 acting path on different majors.
adaptation; life satisfaction; coping efficacy; mediating effect
2014-04-26
袁同春(1969- ),男,安徽壽縣人,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體育教育。
A
1009-9840(2014)06-008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