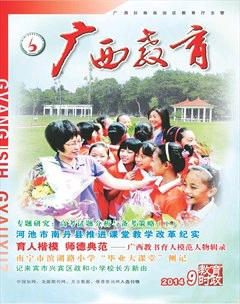回憶我的“雙語”教學
何凡

從廣西壯文學校畢業至今,我已當了近30年老師了。
畢業那年,學校分配我去一所地處中越邊境、離國境線不到兩公里的鄉中心校任教,我心里很不情愿。父親對我說,一個山旮旯的窮孩子,能走出農村吃“皇糧”,你還有什么不滿足的?面對現實,我雖心有不甘,也只能無奈地背起行囊到學校報到。
那所鄉中心校的辦學條件確實很艱苦,教學樓就建在懸崖邊下。學生很少,我任教的壯文實驗班只有26名學生。校長見我一個人無牽無掛的,就撒手讓我全權負責壯文班。
在當時,壯文進入學校是新娘子上轎——頭一回,家長們都不理解、不放心。開學后,家長見我是個毛頭小伙子,心里更放心不下了,隔三岔五地跑到學校找我,希望我批準孩子轉到普通班(漢語班)。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學生們才算安穩地坐在壯文班的教室里。
經歷一番折騰,我想:“我一定要讓家長放心,讓學生愛上我的課堂。”課堂上,我先用壯語解釋漢語,讓學生明白漢語字詞的意思;然后讓學生對比兩種語言的特點,引導他們分析在表達方式上兩種語言有什么不同;特別在習作上加強輔導,學生的寫作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對于壯文,學生由開始的顧慮到樂意接受再到由衷地喜愛,我一直懸著的心也終于放了下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縣小學畢業統一考試中,我教的第一屆壯文班學生壯語、漢語均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優異成績,特別是漢語,平均分超過普通班十幾分,成為當地轟動一時的佳話,我也因此被評為縣級優秀壯文教師。后來,附近村屯的群眾都主動送孩子到壯文班學習了。
壯文教師其實有雙重任務:一是教學,二是掃盲。這兩個任務的最終目的都是為學好、用好普通話服務。白天,我在學校教學生;晚上,我隨村干部到村屯里給群眾掃盲。邊境地區環境惡劣、條件艱苦,壯族同胞能上學的寥寥無幾,特別是中老年人中有很多文盲。剛開始開展掃盲活動時,壯族同胞們大都不愿意參加。后來,鄉里發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他們才意識到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才樂意參加壯文掃盲班。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圩日,邊防團的兩位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到街上買喂豬的米糠,賣米糠的壯族大媽只會說壯話,解放軍小伙子聽不懂,在一旁不知所措。在旁邊賣芭蕉的壯族大叔情急之下,揮舞著雙手,對著解放軍戰士吆喝:“解放軍同志,你們要‘瘋嗎?”“我的‘瘋很好的。”“便宜點給你‘瘋,要不要?”在靖西壯話里,“糠”和“風”讀音相似,大叔不知“糠”這個字的普通話讀音,就自作聰明地用“風”的普通話讀音來代替。誰知在普通話里“風”與“瘋”同音,加上那位壯族大叔語無倫次,兩個二十歲出頭的解放軍戰士誤以為他是瘋子,被嚇得不輕,大叔的話沒說完,他們就已轉身狂奔,趕圩的人們以為發生了什么意外狀況,也三五成群地躲避。后來,鄉干部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對大叔說:“不學普通話不行吧?我們開了掃盲班,你應該去那里學習文化知識。”
后來,這位大叔帶頭參加壯文掃盲班,我也使出渾身解數教鄉親們,經過共同努力,掃盲工作成效顯著。脫盲后,大叔自豪地對我說:“參加掃盲班讓我受益終身,如果我早幾年脫盲,就不會鬧出那樣的笑話了。何老師,謝謝你!”聽到這句話,我既滿足又開心。
雖然壯文教師的工作只做了幾年,但它對我的影響卻極其深遠:對待一份工作,無論初衷如何,只要不怨天尤人,不把它當成兒戲,它就會把美好的一面贈予你。
(責編 秦越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