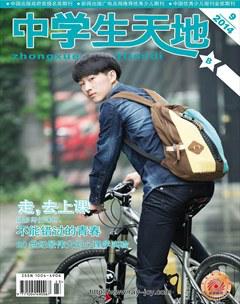攝影師任曙林:不能錯過的青春


上世紀(jì)80年代,攝影師任曙林在工作之余,潛入中學(xué)校園,用他的鏡頭定格下80年代的青春,那些不經(jīng)意間的一顰一笑,那些美麗綻放的少年氣息,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全被留在了照片里;30年后,一位當(dāng)年的女中學(xué)生在參觀《80年代中學(xué)生》攝影展時忍不住流下眼淚,因為她看到當(dāng)時的自己是怎樣用埋首伏案的姿態(tài)掩蓋住青春悸動的心緒,曾經(jīng)和她隔著一張桌子的男生,與她悄然相戀而后結(jié)婚,卻又最終離開了她的生活。
采訪任曙林,原本想請他談?wù)劗?dāng)攝影照見青春,會發(fā)生怎樣的化學(xué)妙用,80年代的青春又是怎樣的肆意飛揚(yáng)。可他卻說,那只是當(dāng)時的青春,每一代的青春都該有自己的內(nèi)容。真正的青春是經(jīng)歷和感悟,是帶著自己的想法獨(dú)自闖蕩世界,是批判和傳承,是吸納各種繽紛的色彩和聲音,是走過和領(lǐng)略更多的風(fēng)景。真正的青春沒有固定的樣子,每個人都該成長為一個獨(dú)立的個體,發(fā)出獨(dú)特的聲音。
拒絕說教,只談感受,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說好的攝影作品是攝影師獨(dú)特觀點(diǎn)的表達(dá)。
青春不是拿來懷念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這組照片在展覽時曾引起轟動,現(xiàn)在也出版了同名書籍,請問您當(dāng)時是怎樣想到拍攝這一組照片的?
任曙林(以下簡稱任):當(dāng)時我在國家機(jī)關(guān)任職,是中國煤炭科學(xué)院的準(zhǔn)公務(wù)員,我有自己的工作,但攝影是我的個人愛好,拍這組照片完全是個人行為。其實(shí)拍攝這組照片,最早可追溯到1975年的時候。當(dāng)時我愛爬山,有一天早起去爬山,看到北京五中的學(xué)生在學(xué)農(nóng)勞動。我當(dāng)時看著他們聚在一起指指點(diǎn)點(diǎn)的側(cè)影,覺得好像有什么東西忽然攪動我的內(nèi)心,似乎有一種力量魅惑著我。我對那整個場景特別有印象,總在心中琢磨。后來,當(dāng)我有了一定的拍攝基礎(chǔ)后,就想拍一個專題來追尋自己內(nèi)心那種感覺,就選擇了“中學(xué)生”這個主題。
記:聽說這組照片您前后拍了10年?
任:是的,最早的照片攝于1980年,最晚是在1989年3月,在87、88年之后去得少了。當(dāng)時選這個學(xué)校就是因為近,離我的上班地點(diǎn)和我家都不遠(yuǎn),5分鐘就能走到。中午或者學(xué)生們放學(xué)的時候,我沒事就溜達(dá)去學(xué)校拍點(diǎn)兒。幾年稀稀拉拉拍下來,慢慢成了習(xí)慣,就把學(xué)校當(dāng)成一個親戚朋友的家,沒事就去轉(zhuǎn)轉(zhuǎn),感受一下。
記:能談?wù)勀?dāng)時拍照時的感受嗎?
任:我特別喜歡放學(xué)的時候,這是我感悟特別深的時候,也是最難拍的時候。因為放學(xué)鈴一響,學(xué)生就像潮水涌出校門,全騎著自行車,一眨眼走光,就剩下靜靜的校園。我特別喜歡坐在操場上籃球架下感受寂靜的校園。我曾經(jīng)寫過一段話:“學(xué)生們越喧鬧,校園越寂靜,這寂靜中各種聲音都存在著,平時可能聽不見,但只要你也靜下來,各種聲音就會滾滾而來,滾過你的心頭,把你淹沒。這是我最享受的時刻,這是我休養(yǎng)生息的時刻,也是我舔舐自己傷口的時刻。”我拍攝的時候,有很多強(qiáng)烈的感受支撐著我,也許是對學(xué)生的愛,也許是對童年的眷戀,也許是對人生奧秘的一種探索,對永不得解的壓抑的一種探尋。校園空了之后,好像很多靈魂都轟鳴起來,壓上你的身心,讓你思考的同時,獲得自由,暢快地呼吸。
記:有當(dāng)年被拍攝的對象來參觀您的展覽嗎?
任:印象最深的,是當(dāng)年無意中拍了兩個學(xué)生,一個男生、一個女生,當(dāng)時我比他們老師更能感覺到他倆之間有一種微妙的東西存在。后來兩人好了,結(jié)婚了,又離婚了。那位女生現(xiàn)在45歲左右,在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她來參觀時說,“原來我以為我們的青春已經(jīng)過去了,看了展覽后,感覺青春留下來了”。因為那個年代的中學(xué)生活對他們來說更值得回憶,那是個挺幸福、詩意、理想、自由的年代。辦展覽時,有許多認(rèn)識不認(rèn)識的人,聽到消息都來了,一看照片,就覺得,哎,真是那會兒的狀態(tài),自己都沒有注意到。
記:所以您覺得青春是什么?
任:青春有內(nèi)容,每個時代都不一樣,有“五四”時期的青春、也有20世紀(jì)80年代的青春。80年代的青春的確有很多好東西,很多民國的、老一代傳承下來的東西,逢著那個時代的氣候和土壤,全部滋生出來了。所以80年代不是孤立的,這些東西在今天看來依然有生命力。但是青春不需要懷念,而需要創(chuàng)新。每個時代都有時空變化,都會有新的東西與時俱進(jìn)地生長。有時候我們會想,比如,雖然80年代有很多問題,但為什么當(dāng)時每個人心靈充實(shí),特自信,還能寫詩,而現(xiàn)在的很多中學(xué)生卻感覺都戴了面具呢?我們應(yīng)該鼓勵學(xué)生享受青春。因為青春是個過程,是釋放,是成長,是不固定。它不是結(jié)果,不是功利的。從不懂事的少年到懂事的青年,這個過程特別應(yīng)該珍惜。
不懂視覺文化的人是殘疾的
記:再說說攝影,能談?wù)勀窃鯓雍蛿z影結(jié)緣的嗎?
任:很小的時候,我父親買了照相機(jī),我和妹妹就跟著他去拍照,那會兒他不讓我們動,只能當(dāng)個小助理。到文革的時候,我父親去了干校,照相機(jī)就落到我的手里,可以自己拍了。初中開始,我就拿著照相機(jī)出去,平時爬山、聚會啊,什么時候都拍。
記:你覺得攝影是什么?
任:簡而言之,就是在記錄生活,是觀看、記錄和傳達(dá)信息的方式,然后再把這些三維的東西轉(zhuǎn)換成平面,使人們在面對景和物的時候,產(chǎn)生感受和觸動。陳丹青說過,現(xiàn)代藝術(shù)在某種程度上,就體現(xiàn)在影像上。作為一種現(xiàn)代的、視覺的文化,相對于文字和聲音,視覺語言是嶄新的,攝影迄今才180多年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上天悲憫人類,賜給我們一種重新認(rèn)識自己、看待周圍世界的方式。影像符合人類基因中天生的信息傳遞規(guī)律。人類從原始人進(jìn)化,最開始就是畫巖畫、結(jié)繩記事。所以影像是最透徹的,它具備多義性和可能性,是最迅速、最有效率的傳達(dá)信息的方式。在當(dāng)今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各方面都離不開影像,它是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方式,你要是不懂,就是半殘的。
記:現(xiàn)在我們有很多中學(xué)生也喜歡拍攝,從一個業(yè)余的拍攝愛好者到職業(yè)的攝影師,需要經(jīng)歷什么樣的轉(zhuǎn)變?
任:我要糾正一下你的說法。好的攝影者都應(yīng)該是“業(yè)余”的。其實(shí)從攝影師誕生的那天起,真正的大師全是業(yè)余的。許多所謂的“專業(yè)”,把攝影掏空了。攝影無處不在,沒有什么題材是不可拍、不能拍的。你在山中,何用尋山?endprint
記:好的攝影作品需要具備什么元素?
任:不管拍什么,景(包括自然景觀和城市景觀)物(人物、動物)都好,都得有你自己的東西,過去說文如其人,影像也一樣,要有你自己獨(dú)特的見解和感受,潤物細(xì)無聲地融合在里面。攝影基本功就不談了,這是必須的,在這之上,你得具備“借尸還魂”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拍的東西是死的,但是有了你的魂,這東西才能活。比如齊白石畫蝦很柔,和八大山人那種陰冷就不一樣。這里面有他的人生閱歷,無可替代。所以,在注入魂的過程中需要各種磨練和基本功修養(yǎng),才能達(dá)成這個結(jié)果。這個東西也許是一層窗戶紙,也許是萬水千山,一輩子都達(dá)不到,就看個人修為和幸運(yùn)程度了。
記:中學(xué)生應(yīng)該怎樣訓(xùn)練自己的攝影技能?
任:首先訓(xùn)練的是眼睛和心靈。你不會觀察,不會觀看,不熱愛生活就不行。過去我們上課看電影,通常是上午連看兩遍,下午復(fù)述時99%都能背出來,包括臺詞啊鏡頭啊什么的。好的電影符合人的思維規(guī)律,懂得用視覺說話。另外,一個對周圍世界沒有感情的人,沒有寬大胸懷的人,知識不淵博,感情不豐富,不合群,沒有激情,甚至太善良的人都搞不好藝術(shù)。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記:作為一名攝影師,想必您已走遍千山萬水,中國有一句話叫作“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能否談?wù)勀睦斫猓?/p>
任:不讀書,光走道,就是一個普通的行者,沒有自己的思想。而書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傳承,變成你的,需要一個過程。青年人應(yīng)該一有機(jī)會就多出去走走,這樣才能把書上的東西消化成自己的,能拆開了,揉碎了,活學(xué)活用。在行路過程中,才能知道什么書值得讀,怎么讀書,包括和朋友聊天,也像是讀書。出去走了之后,人的心情會特別開闊。你會學(xué)到慈善精神、寬恕精神、互助精神、感恩精神,很多東西是從花草鳥獸、天地日月中悟出的。你如何獨(dú)立面對生存,比如買東西討價還價等,也是行萬里路。
記:您在行走中,有沒有碰到特別值得紀(jì)念的時刻,就是有一種似乎攝影和人生的關(guān)竅被打通了的感覺?
任:談兩個。一是1978年的時候,我因為1977年恢復(fù)高考后沒考上,又不想一輩子當(dāng)工人,于是請了幾天假,獨(dú)自一人上山思考自己的前途。我弄個小帳篷,帶了一小捆掛面,呆在山上,天天看日出日落,寫了一萬多字的感悟,突然覺得很輕松了。下山后雖然還是工人,但覺得自己看清了很多東西,變得特別陽光,踏實(shí)地面對腳下的每一步,充滿了奮斗的精神。所以,人在年輕的時候一定得獨(dú)自出去旅行一次,把自己拋在陌生的環(huán)境,學(xué)會獨(dú)立面對問題,對自己負(fù)責(zé)。再一個就是2012年,辦完《80年代中學(xué)生》展后,無形中有了壓力,別人對你的認(rèn)識有了一個標(biāo)準(zhǔn),我就想怎樣把這些東西都打碎了,繼續(xù)自由地活著。我先去了一趟西藏,還是沒解決,后來想找別的旅游點(diǎn),就去找古鎮(zhèn)。我到了浙江建德的梅城,那里有千年古寺和百年名校。我在那里呆著,天天睡到自然醒,回到放松狀態(tài),到處走走拍拍,游游蕩蕩,有點(diǎn)時光倒流的感覺。后來認(rèn)識了一位僧人,跟他說自己的煩惱。他與我交流,送了我三句話,一.不管你做什么,都要把自己的事做到極致;二.你要相信天上不會掉餡餅;三.你走道的時候別把道擋死了,給別人留條縫。又給了我一個法門,就是用出世心做入世事。
采訪手記:其實(shí)采訪進(jìn)行到最后,我們慢慢離開了攝影這個話題,指向了更深遠(yuǎn)的人生。在任曙林看來,攝影只是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每個人都應(yīng)該把自己手中的事做到極致,因為這才是一種活著的精神。他希望自己所分享的內(nèi)容,像他的作品一樣,都是開放的,而感悟世界和成長的方式,因人而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