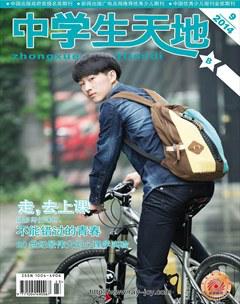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
何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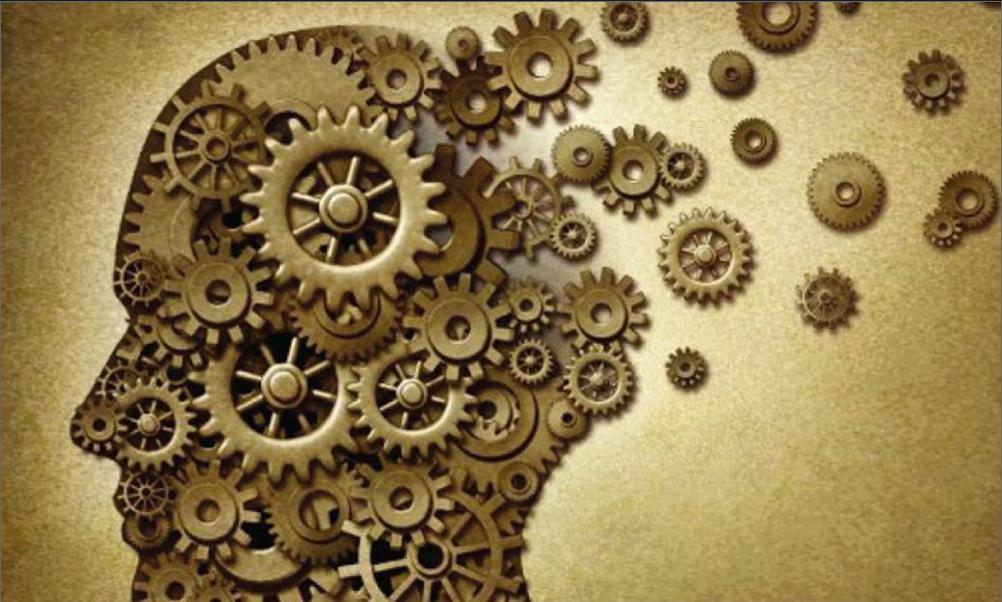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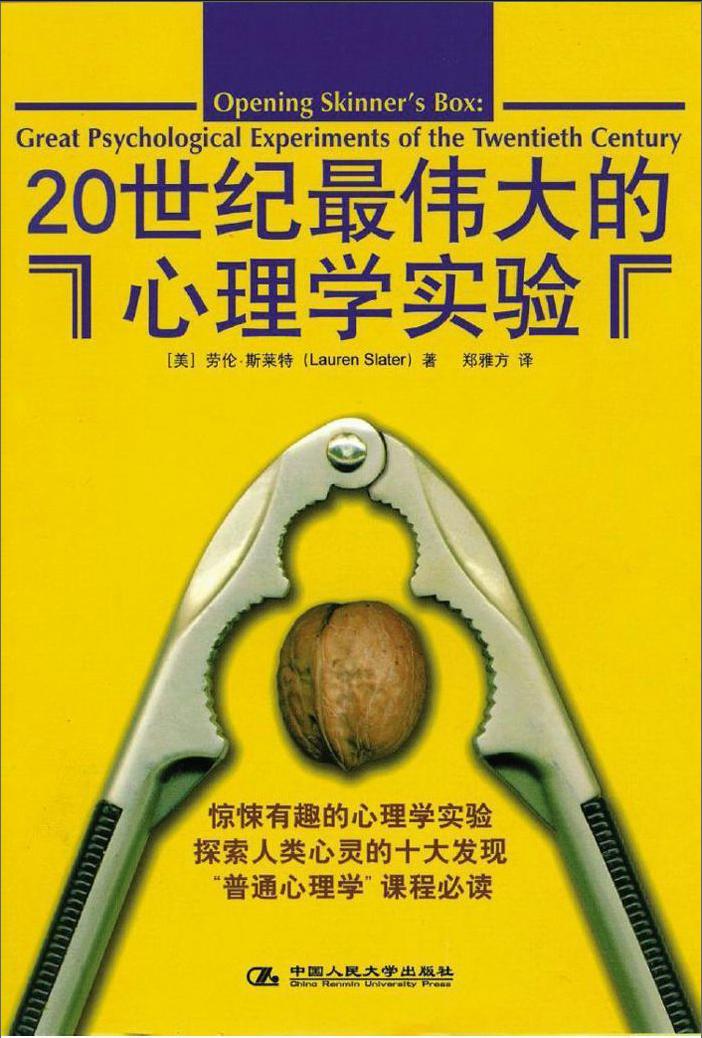
今年上半年,山東招遠“5·28血案”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我是學傳播學的,除了了解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更關注社會大眾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反應。
事件發生之初,觀者幾乎是毫無例外地深感震驚。這個好理解,因為招遠血案發生的場景有點挑戰人們的普遍認知。如果這個案件發生在背街小巷,甚或家庭爭執的現場,可能它就不會有這么強的爆炸性影響。可是它偏偏發生在招遠市的商業中心,發生在麥當勞這樣熙來攘往、熱鬧到經常找不到座位的公共場所。而且,大部分市民都在麥當勞里用過餐,熟悉那個場景,馬上能夠聯想到畫面。這種心理上的沖擊自然很強烈。
震驚引發了人們的思索,在真相未明的那幾個小時,人們首先感到的是憤怒,然后是深深的不安全感。設身處地,如果換成是我,會有怎樣的遭遇?我能夠避免口角嗎?我能夠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嗎?如果對方6個人執意行兇,我能夠逃脫嗎?最關鍵的是,周圍的人會幫助我嗎?
隨著越來越多的真相被披露,人們關注的焦點逐漸集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焦點是“冷漠”,即旁觀者的“不作為”。看看這時候的新聞標題——《殘忍和冷漠,哪一個更可怕》《招遠慘案我們為什么如此冷酷》……一些公眾人物也開始發聲,崔永元在微博中問到: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不沖上去,我們還能給自己找到足夠的理由,這就是我們吧?我們是什么時候因為什么變成了這副德行?”
或許因為我們在社會新聞版塊見過了太多“見死不救”,招遠血案很容易就撕開了人們遠未愈合的心靈創口。有人從社會結構、民族特性、法律約束等角度審視我們的“冷漠”,甚至分析出了這樣的原因:在德國、法國、意大利、巴西、加拿大等很多國家,不僅從法律上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權益,更明確規定“當看到他人遇到危險而沒有提供必要的救助”將會被判處監禁和罰款。
慢著慢著,我這里倒不是非得要挑別人的毛病,來映襯自己其實沒有那么糟糕。只說一個在美國發生的陳年舊案,論血腥和駭人聽聞,比起招遠血案來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完整記述了案件的全過程。
時間是1964年3月13日,星期五,凌晨時分的紐約皇后區(同樣的市中心地帶),在酒吧擔任經理的珍諾維斯下了夜班,正要回家。她停好車,向公寓所在的大樓走去(同樣的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她一下車就發現遭人尾隨,一名男子形跡可疑、來意不善。她毫不猶豫立即走向街角的緊急報警電話。但是幾步就能跑到的短短距離,她此生未能抵達。
名叫莫斯里的行兇男子拿刀朝珍諾維斯背部猛刺,她轉過身,腹部也中刀了。她渾身是血,大聲呼救:“救命呀!他拿刀刺我,誰來救救我!”案發地區住家密集,她一呼喊,燈光紛紛亮起。
事后莫斯里受審時說,他看到燈光亮起,但他認為“這些人不會下樓”。情況果真如此,莫斯里跑開,而身中數刀的珍諾維斯,勉強爬行到路邊,躺在一家書店門口。
公寓住戶的燈光熄滅了,街道又恢復寂靜。莫斯里走回他的車,發現四周安靜下來,燈光也暗了,于是決定回頭繼續殘害受害人。這起案件前后持續超過35分鐘,歹徒三度施暴,每次受害者都尖聲呼救,附近住戶應該都聽見了。盡管他們開燈察看,甚至目睹事件經過,卻沒有人伸出援手。總共38名證人隔著窗戶,眼睜睜看著一名女子身中多刀。罪行結束后,終于有人打電話報警,不過受害女子已經身亡,救護車前來把她載走,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繼續睡覺。
兇徒在街區行兇,38位目擊者無一施以援手,美國人民怎么了?只要拿起電話報警,就能馬上幫助受害人,可是偏偏沒有一個人這么做,在半個多小時里放任歹徒行兇。歷來重視隱私的美國人,甚至要求報社公布38個人的姓名、照片、地址和聯系方式,把他們永遠釘在“虧欠道德”的恥辱柱上。
美國的科學家不愿意繼續容忍無知,他們深信看似違反人性的事件背后,必然有我們未曾發掘的科學邏輯。
于是,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之一,姑且稱之為“助人行為實驗”吧,在紐約大學拉開帷幕。不知情的受驗者被關在一個小房間里,通過麥克風與從未謀面的陌生人交談。當然,“陌生人”是心理學家安排的演員。交談過程中,演員的癲癇癥突然“發作”,一陣急促的喘氣聲和短暫的呼救后,麥克風陷入寂靜。
你應該能猜得到受試者的反應。85%的受試者在第一時間向主試官報告,發生了緊急情況,有人需要幫助。這個實驗結果,與人們對社群的普遍認知是相符的。
科學家開始調整實驗方式。新的被試者得知,當他用麥克風交談的時候,還有人數不等的其他人也在聆聽對話。這時候,演員的癲癇癥再次突然“發作”。
猜猜看被試者會作出什么反應?
實驗結果顯示,被試者如果以為當時在場者有4人以上,就不會采取行動幫助受害者。反復實驗后得到一個結論:如果人們知道事故現場存在其他可以施以援手的人,大部分人自己就不會動手施救,這個“大部分”達到近70%之多。
讓我們再說得明白點,如果某人在電梯里看見一位老人心臟病突發,電梯里只有他和等待救助的老人,他有八成的可能性會立即幫人,至少會拿起手機打個求助電話;如果在大街上遇到同樣的情況,這個人則有七成可能掉頭走開,什么也不做。
你也許認為,人越多,你就會越勇敢,越不怕危險,更會主動伸出援手,事實并非如此。本質上,你的判斷與人性是否冷漠無關,不如說是一種責任。“助人行為實驗”說明,群體規模與采取行動的比率相關。越多人目睹一起事件,個別目擊者會自覺責任越少,因為有越多人分攤責任。美國心理學家將這種當時還無人知曉的現象,稱之為“責任擴散”。
《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這本書里充滿了既瘋狂又現實的“奇思妙想”。再舉幾個例子。科學家將剛出生的小猴與各種各樣的人造母猴關在不同的籠子里。結果,小猴并不依戀能提供乳汁的母猴,而是時時刻刻廝磨用柔軟的布料編織的“母猴”。就算布料母猴體內暗藏尖針,或者不時發射高壓水槍,小猴痛苦呻吟但是仍然不離不棄。做這個實驗的心理學家想說明,我們人類(最接近猴子的動物)視作情感最高級別的“愛”,也許只是一塊破抹布帶來的柔軟錯覺。endprint
還有一個實驗與我們生活中的消費習慣密切相關。這一次頂替人類勇敢躺上試驗臺的不是猴子,而是可憐的小白鼠。心理學家發現,把小白鼠關在籠子里,給它一個可以踩踏的按鈕,很快它就能學會踩踏按鈕取食物。如果踩踏三次按鈕才能掉一次食物呢?小白鼠沒費多少時間,就學會了直接踩踏按鈕三次取得食物。
更有意思的來了,科學家改變壓桿獲得食物獎勵的比例,多數時候小白鼠空手而回,但也許在壓桿第40或60次時,突然獲得食物獎勵。一般人直覺地認為,隨機且間隔如此長的獎賞,會使小白鼠對獲得獎賞不抱希望,致使壓桿行為消失。但是進一步研究證明,間歇給予食物獎賞的方式,反而讓這些小白鼠像染上毒癮一樣,不斷壓桿,而不論能否得到獎賞。
有沒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們人類何嘗不是如此。中學生朋友們愛玩的網絡游戲,就是憑著簡單的一招“隨機掉裝備”,讓許多玩家欲罷不能。推而廣之,商家的抽獎送大禮、彩票中心不斷沖擊高位的獲獎公告,利用的都是人們為了虛無縹緲的獎勵而奮不顧身的心理。作者勞倫·斯萊特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抒發了她觀察社會生活的感受,“為什么我們做出許多蠢事,即使得不到回報,仍舊執迷不悟?為何我們的好友會癡癡守在電話旁,苦候惡劣男友偶爾心血來潮打來的電話,居然還覺得這是莫大的恩惠?為什么有人身心健全,卻在煙霧彌漫的賭場里散盡家財,終致身敗名裂?為何女性總是愛得不能自拔,男性總喜歡玩股票?”究竟是小白鼠太“智能”了,還是我們人類其實太單純?
《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個個另類,它突破世俗認知的意義,讓我總想用20世紀最“過分”的心理學實驗來稱呼它們。在我看來,實驗得到的所謂結果,其實沒有那么重要。而它倡導的理性思考,不被所謂社會普遍觀念所蒙蔽的精神,才真正值得去追隨。
落筆至此,有必要再回頭談談文章開頭時提到的招遠血案。事實一步步明朗,原來,圍觀者并不曾冷漠。麥當勞的值班經理,幾乎在兇犯行兇的第一時間沖過去力圖制止。只是對方深受邪教蠱惑,殺意正濃,才使慘劇不可收拾。如果以道德與否來判斷,這位女經理由此就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嗎?還是她深知責任不可推卸,在當時的情境下,獨自逃脫了“責任擴散”的心理迷局呢?
多思考,多了解不同的觀點,我們才能擺脫社會普遍認知施加的強大影響力,擺脫人云亦云的思維模式。或許,這就是閱讀的意義所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