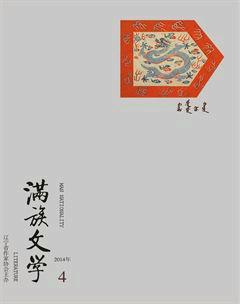有難度并有誠意的詩歌
《滿族文學》雜志社于今年5月16日至18日,在寬甸河口長河島舉辦了詩歌筆會。歷史上,《滿族文學》曾多次舉辦過詩歌筆會,為培養本地詩人做出過重要貢獻。追溯最后的一次詩歌筆會是在1992年,距今已有22個年頭。22年后,丹東地區老、中、青詩人們又一次聚首,眾議詩歌創作,感慨頗多,受益匪淺。丹東市文聯的所有領導均參加了筆會,給予了關懷和支持。筆會上,除了創作修改新作品外,主要以座談的形式交流了詩人們彼此的詩歌文本認知、詩歌創作體會和詩歌行為誤區。現將座談紀要整理刊載,以與詩人、讀者進一步探討交流。紀要的題目摘自于詩人宮白云的發言。
遼寧著名詩人林雪因公來丹,也應邀出席了筆會。她的即興發言,得到了詩人們的強烈呼應。
林雪:在某一個時刻會有一種頓悟,在某個時段詩歌會與土地上的歷史、風俗、民情相傳承。我在1992年期間比較頻繁地回到家鄉撫順,因為內心總感覺到迷茫,人的需求是什么呢?說不清。只要在家鄉的街上走走,就會找到一種出口。大家可能有一種同感,寫到一定程度,就會有一種迷茫。下一個路口該往哪里走?未來是什么?之后我把與撫順相關的歷史、傳說,甚至黨史等進行搜集,再創作,大約有三年的時間,最終出了一本詩集。詩歌創作資源還是有限的,在一塊土地上,歷史感越早建立越好。我們的寫作認知錯過了就非常遺憾了。多民族的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造成的沖擊和思考是有渲染的。個體作品如何面對讀者,地方團隊如何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影響。宮白云是丹東的一位作者,她的詩歌創作在詩人中脫穎而出。我想,是因為宮白云參與多家網絡平臺,參與策劃與點評,在釋放自己上比較積極。
林雪的發言引起了詩人們的積極互動。
叢黎明:昨天我閱讀林雪的詩集《大地葵花》,其中《在蓋牟城》這首詩里,有這樣的句子:“除了幸福沒有什么能傷害我/如同蝴蝶,傷害不了/一枝花的標本”讀到此處,讓我的內心深感震撼,這樣的語言看上去好像很直白,但細細品味,卻有極強的張力,讓我們透過語言的表象,直達內心最柔軟的地方,這是詩歌創作很難抵達的一種高度。請問林雪,你當時是如何創作出這樣一首詩歌的?
林雪:這里有幾個關鍵詞,痛苦,傷害,標本,花朵,形成互文的關系。痛,該如何寫才能突破?我們把痛苦轉移一下,在痛苦的對面或者反面來寫。無論明喻還是暗喻,利用技巧語言來描述。創作的主體不一定要被痛苦融化了,你可以在情境中充當一個絕緣體,融化、融合不如換一個角度,這樣,就有可能更充分、更準確地表達出你想表達的東西。
姜慶乙:您說的詩人應當具備一個歷史感,您在創作中有沒有一個階段性的轉變?我們對現實、歷史的見證是否是一個社會的進步?《陳鴻雁之死》詩歌的創作背景是怎樣的?
林雪:先談歷史感的問題。除了艾略特,還有龐德、阿斯伍德也都非常明確地提出歷史感非常重要。我們有必要加深這個命題。《陳鴻雁之死》這首詩寫于2001年春天,開始用的引文,中間穿插解說,大概有120行左右的小長詩。當時是坐在出租車上聽新聞,剛開始的新聞是有娛樂性質的新聞,陳鴻雁死亡就是其中的一個新聞。放在一個不起眼的新聞里面,當時給我的感覺很難過,因為播完這條之后主持人又用非常娛樂的口吻播誦下一條,包括音樂、主持人的語氣都混在一起,讓我難過。陳鴻雁的死去,在這樣一個商品時代的組成部分的分量如此之低,讓我很是感慨,所以我就寫出了這首詩歌。今后社會中還會有各種各樣的死亡,希望把人命作為一個時代的政治,提到一個國家的保障體系里。后來,《詩刊》、《綠風》都選了這首詩。
姜慶乙:詩人發出的呼聲,是對一種時代的把握與見證。詩歌作為一種文明的呼聲,具有一定的影響。當下的詩歌局面您怎么看?
林雪:新詩從白話詩歌運動到現在剛好一百年。我們新詩的母體是一種翻譯詩,胡適的語言特點是從我國古典小說演變而來的。回首百年,翻譯體詩歌作者寫了許多作品,那么引申現代新詩的問題,翻譯體作為我們詩歌的母體的正源在引用,對我們新詩是一種走彎路。我們詩人如何認知現實,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傳統的文學理論體系闡述得都比較清楚。物質的、精神的,現實有一部分是遮蔽的,并不是真相。這個問題比較敏感,我們現在正在還原本真。詩人應還原現實,通過認知、媒體解剖、還原真相。我們詩人要把熱愛轉化成文字,可以通過閱讀、感受,提升對認知的能力,盡可能達到本質的現實。觸及真相,不讓我們的作品成為一種笑柄。
黃文科:在詩友交流中,有一種提法,古典好詩到唐代就終止了,詩歌以后就沒有發展了,您怎么看?
林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的小說,不是發展了嗎?進化論不能庸俗,就新詩而言,新詩的質感、情境的營造,都是發展。新詩和唐詩有內在的傳承,但不能說新詩就是沒有發展。既不能說超過了唐詩,又不能說停滯,要辯證地看待。
詩人們與林雪的互動引發了大家心中對詩歌已久的思考,交流性發言越來越熱烈而深入。
黃文科:從新詩來源來說,新詩從黃遵憲倡導詩歌革命開始,也有種說法,新詩從胡適在《新青年》發的詩歌開始。毛主席說,新詩要借鑒民歌來寫。中國古典詩歌為新詩之母,外國詩歌為新詩之父。自由詩不能完全無規矩,新詩作為經典之作要具備三性:現代性、傳統性、當下性。
姜慶乙:大多數人認為,新詩應該命名為:現代漢詩。新詩還遠遠沒有達到成熟期。
王永利:中國古典詩歌和外國詩歌結合,產生新詩。對詩歌評價應是廣泛的。
叢黎明:因為我們曾經有一段文學的荒漠期,在那個時期,詩歌是以其非詩的面貌呈現的。詩歌創作已經離開它應該具有的含蓄——這一本質內涵。于是一些直白、粗俗的順口溜被誤認為是詩歌。當人們走過那段文學的荒漠期,詩歌漸漸覺醒過來,開始回歸到它的本真,很多人就看不懂它了,就把它命名為朦朧詩。我們現在再讀那些朦朧詩,就會意識到那些詩并不朦朧。因此說朦朧詩的命名是很不準確的。詩歌創作,一定要遵循它的藝術規律來寫。很多詩歌看不懂,除了詩人本身就不明白,寫了一些晦澀難懂的詩句外,其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對新詩的發展跟不上,沒有掌握新詩解讀的密碼。換一句話說,審美是有層次的;沒有一定的審美能力,就讀不懂新詩。
王永利:新詩是形式概念,還是內容概念?首先是形式。傳統詩歌和新詩形式上是不一樣的。是兩個體系。
芒點:形式不一樣是一種形而上。如果僅在文本探討,如加入內容,形式就多了。詩歌的大眾和小眾問題,詩歌是寫給誰看的?席慕容和汪國真的詩歌,倍受爭議,他們的詩雖然簡單,但他們的詩歌在一定層面上還是好的,現在討論的詩歌還是屬于小眾的。
姜慶乙:紙媒上發表的詩還是小眾的。詩歌雖然屬于小眾,但詩歌的內容是大眾的。
芒點:詩歌是金字塔的形式,最頂尖的是最上層的,像汪國真這樣的則是在底層,詩歌受眾是可以培養的。
叢黎明:談到詩歌語言簡潔的問題,我想,用顧城的《遠和近》,最能說得清楚:“你,/一會看我,/一會看云。/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這首詩雖然很短,語言也極為簡約,但顧城用很短的詩句,最簡約的語言,卻表達出了很深刻的思想和情感,亦即當人與人的心靈無法溝通時,即便是近在咫尺,也是遠在天涯的,還趕不上與遠在天際的云那么親近。這就是我常說的,一首好的詩歌,一定要有形而上的思索。何謂形而上?何謂形而下?古人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道者,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思想情感和真理;所謂器者,就是能夠看得見摸得著具體可感的萬事萬物。詩歌就應該是用具體可感的事物,來表達對社會、人生、人性、人情的價值體認。詩歌好與否,常常類似于白水和酒,它們都是液體,好詩是酒,不好的詩是水。
張濤:反過來說,亦可。好詩是水,不好的詩是酒。
叢黎明:張濤的這個觀點很對,他把詩歌的品級,又推向了欲造平淡而不能的更高境界。這是詩歌創作,一個更應該引起人們重視和思索的話題。
包貴韜:新詩從五四以來到現在,已經非常豐富了。在技術上再有重大變化,已經很難了。詩歌的關懷層面非常重要,當下性作為作者是要具備的。在道義層面了解了,整合你要用的東西來寫詩。地域性詩歌是抵御全球化的策略。所有層次越來越明顯,行為和裝飾是關鍵藝術。詩歌要有坐標,三性。漢語言本身是發展的,要有時代特點。林雪的角度很重要,具有道義層面的方向性。
叢黎明:差異化顯示個性,寫作資源不一樣。林雪挖掘本地特色,寫出詩歌。文學創作資源其實在創作者本身的地域就很豐富了,只是有人忽視了它。
姜慶乙:地方性資源來說,甘肅詩群很活躍。是否是見山寫山,見水寫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寫景的時候,要加入人文因素。
張濤: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師。現代詩的界定,是理論界的事情。寫作者應該有一種悲憫。地域性的問題,可否換成寫作的版圖,文化和歷史的縱深感。地域是一種載體,陌生化是詩歌的要求,如何與別人不同?創作要有特點。美術強調師傅,文學強調個性化、陌生化。寫作需要技巧嗎?技巧沒有用,像木匠一樣,不需要技巧。無論小說還是詩,是一種宿命,它本身已存在,不僅要關注地域,還要注重思想。每個詩人要忠實自己的內心。一部分的詩有一部分的受眾。有詩就寫,忠于內心。詩的受眾是小眾,就像表演服裝很漂亮,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穿一樣。
高鵬吉:如何雕刻出好作品?把多余的去掉,留下好的就行了。詩歌也一樣。
鄒云賦:昨晚看張濤的詩歌,有些感想。他的詩歌自然而發,是一種文學修養所應企達的最高境界。初學者要有技巧,表現技巧,中期注重表達智慧,后期表現人格,自然而發。
叢黎明:張濤的詩歌,不學哲學而用哲學,其語言簡單又很純凈。
雪茜:我讀一下木心的詩歌。他的詩歌意境優美,給人以美感。
任國良:張濤老師的《孤山獨白》、隋英軍的《鳳凰城舊憶》是一種目的性寫作。隋英軍目前在寫《詩經里的植物》。詩人要寫自己的資源,是一個方向。玉上煙、宮白云剛出現就寫得很好,老作者卻無法突破。
黃文科: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英軍用詩歌把本地域豐厚的資源挖掘出來了。
祁頂:讀一首王錄升老師的詩歌《吃奶》很有感觸,詩歌要有自己的感情,才能去打動別人。
王永利:詩歌是很個體的,標準不一。資源是主體對文本認知的程度,對自己不動搖。為什么寫詩?為什么讀詩?就是共鳴。審美層次不同,標準不一。
丁顯濤:我寫新詩的時間較短。新詩的發展非常豐富,中國的新詩一直在路上,還沒達到頂峰。看似水的句子,達到一種酒的味道,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邢培紅:我不是詩人,作為一個讀者來談談。張濤老師的詩歌平直,而又有韻味。從中能悟出很多道理,悟出現實中的東西。很多好詩,能引起有識之士的共鳴。用文學啟發大家思考,是文學的意義。詩雖小眾,詩歌是藝術,也是文化,起到教化的作用,所散發出的人文關懷是社會需要的。
張啟東:詩人要具備悲憫的心,生活中的很多事讓人感動。講一個故事:有一位敬老院的老人,看我往家走,就問我冷不冷,要給我他的棉襖穿。我說不用,但他的目光是那么真誠,透露著關懷,讓我心情很沉。一些小細節真的打動人。張濤老師講的資源我不缺,但我沒有把握住。平常我要多積累,多讀書,讀好詩。
王永利:啟東講的故事,是一種形而下的部分。你的感動是一種形而上的部分。他的棉襖雖然沒穿在身上,但他的棉襖穿在我身上一輩子溫暖。
姜慶乙:詩歌有一種善的力量,教化的力量。我們對詩歌不能簡單理解為語言,詩歌真正的力量是善。
張忠軍:現代詩歌,有一部分細節非常好。啟東說的這個棉襖的故事,用非常樸素的語言說出來,回避修辭,就是一首優秀的詩歌。有時候,用修辭就是對詩歌的傷害。
遲鳳忱:詩歌不要有技巧,憑感覺寫。寫作要有資源,我大部分詩歌都源自土地,是我的根,所謂地域性,就是找到自己的根。詩歌語言可以用口語化,也可以用靈動的語言,在一首詩里要統一。自己的詩,在自己的心里動了一下,這就是好詩,詩歌要多讀,理解多少算多少。
李世俊:我寫詩歌時間較短。詩歌必須有生命性,否則就不是好詩歌。賦予現實性和未來與意義,詩歌才是好的。就詩歌創作而言,我覺得一切均可入詩。不存在技巧高低,而在于詩核的構成,境界決定層面。詩歌去掉虛偽,傳遞生命本真,就是詩歌的意義和價值。我寫詩到現在,感受到寫詩讓我快樂。無論做什么事情,能讓我們快樂是最重要的。
劉國慶:讀好詩,直到讀出毛病,就不讀了。想寫的時候,把想出來的列到紙上,耐心地等,它一定會出來。
張忠軍:一首詩的寫成,從文本意義上說,詩歌結束了。一首詩真正的結束,就像一個小盒子,關上的時候有咔嚓一聲,才算結束。詩歌是需要耐心的。讀書是一種閱歷在讀。以前我們認為漂亮的,現在看起來覺得平平。有些東西需要重新認識,對自己也是一種檢閱、審視。
劉國慶:詩歌的繼承問題。文化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種自然的東西,不能太刻意,詩歌要關照現實。
黃文科:理論是有一種規律性的,流派、文本解析,寫作者與評論者在靈魂上是平等的。
姜慶乙:讀經典文本是一種創作的經歷,外國文本的翻譯與原著之間是有一定差異的。
黃文科:現代詩歌難于古典詩歌。新詩沒有固定的格式、框框。新詩在于新意。
邢培紅:詩歌創作是小眾的,但從受眾來說是大眾的。寫作資源就在你的身邊,你的經歷就是你的資源。創作是否需要看,或者寫,都是自然而然的行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詩歌要有自信。人類的感情是共同的,好的詩歌要感動人。
年輕詩人姜慶乙、宮白云是丹東地區近些年來涌現出來的新詩人群體中的代表,他們兩人在接下來的座談中,做了主題發言。
姜慶乙:在詩歌寫作上的經驗,每個人都是不同的。談詩歌不落實到文本的話,就是紙上談兵。先說說詩歌的命名功能。語言之所以有各種表達,在命名的基礎上,加以新的發現,別人沒想到的,你給予重新的發現、重新的表達,可歸結為命名。有新的定位和認識,我們如何處理現實經驗上升到審美經驗?如果讀者沒有感受的話,就是失敗的,我們沒有寫到最接近人心力量的詩歌觸動他們。詩歌給我們撫慰,安定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的。比如管一的《離婚室》,后面的幾個排比句,這個…這個…這個…,加重了語氣,當我們讀到這首詩的時候,我們有聽到過反映特殊時期打工者的境遇,那種傷痛感與詩歌聯系起來。八零的《飯桌上的幽默》。通過警察的問,有些荒誕,但對瞎婆子來說,也是現實的。公民是這個社會最底層的人,眼淚竟然也被搶劫了。我們能為別人流淚的機會太少了,以瞎婆子為這個故事的線索,八零把握這首詩的結構特別巧妙,骨架、詩魂眉目分明,沖擊力顯而易見,我們的眼淚是否被打劫了,我們是否還有流淚的機會。張忠軍《依據》提到的眼淚,心靈經驗播散到四方。一首好詩有詩的品質,緬懷鄉土。娜夜的《村莊》,講述了孤寡老人悲涼的情緒,反映了農村的現狀以及現實問題。張強的《數字村莊》,沒有任何技巧,這里有一個陡然的抖起,真實地披露了農村的一個概況,詩歌不僅是數字的統計,而且是一種痛訴,詩對現實的呼聲。這首詩能感動一些人,我們如何面對現實的眾生態,用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藝術記錄下的真相,會有長久的影響力。我想,詩歌缺少讀者,是因為缺少駕馭現實的能力。如果受眾是廣大的人群,詩歌會有更大的發展。詩歌《觀相》中,人民是一切,人民到底在哪里?當下的政策是民生而這首詩表現的是一種巧合與吻合。中國古典詩歌之所以被認知,主要源于賞析和解讀。現代詩歌同樣需要解析。胡弦的《更衣記》昭示或暗喻:我們每天都需要換衣服,衣服如此,生命如此,人生如此。
叢黎明:慶乙的詩歌扎進人生的深處。其對詩歌的把握也已具有相當的理論高度。就姜慶乙剛才談到的這三首詩歌《數字村莊》、《飯桌上的幽默》、《更衣記》大家談談自己的感受。
王永利:《數字村莊》入選了2013年《中國詩歌》選本。今天上午涉及的詩歌文本定義,具有不可定義性。《餐桌上的幽默》確實有詩的深刻。瞎婆子這樣一個人物,很有撞擊性。眼淚是一種感情的表達方式,方式被搶劫了,對人類本身來說就是一種悲哀,深刻表達了人性的一面。忠軍的《依據》,面對生活的發現,因一種憤慨或同情,而引發感慨。
張濤:忠軍的《依據》我十年前讀過,我們很慶幸我們還有眼淚。《數字村莊》更單純,作為個案,它記錄了一種文本意義。文無定法,現代詩在選擇上沒有技巧。文本強調真實性。
張忠軍:抒情與反抒情的問題。反抒情非常客觀,如果用抒情手法就是傷害。類似這樣的還有很多,就這首詩而言,無法用修辭手法來修飾。
姜慶乙:我們如何注入文本以新的意義、思考和命名。胡弦的《清明》,使我們看到了當下人如何賦予它一種新的東西。
芒點:《數字村莊》是一種羅列手法。羅列手法不一樣,詩歌的手法多變。《餐桌上的幽默》是一個點,對這樣的詩歌,忠軍老師把握得好。我對胡弦的詩歌非常崇拜,他的詩大氣,從火中取出冰冷的銀兩,充滿了沖擊力。
張忠軍:《餐桌上的幽默》描寫的眼淚,被掠奪,財產被掠奪,這是一種漠視苦難,這種題材已到極致,寫詩不能放棄難度,并應適當提高。
高鵬吉:愛爾蘭詩人寫的《大麥》,用我們這個人稱敘述,一直到遇害。詩歌簡潔,前兩首有些不夠簡潔。
姜慶乙:娜夜的《青海,青海》中,有四個“還在那”怎么樣怎么樣的排比。我們知道在詩歌中,排比修辭是最膚淺的方式,但放在一定的情境當中,也是最深刻的方式。后兩句包含的容量,美倫美奐的轉換,油菜花和蜜的搭配,佛光里的蜜是一種極致。從娜夜的《起風了》等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詩歌漢語言的價值。一個詩人寫詩最終是為了漢語言的價值,同時也提升了國家的文明。
宮白云:在這里談一點詩歌方面的寫作與閱讀體會,不恰當的地方請各位老師、詩友們批評。
每個詩歌寫作者都有自己的寫作體驗與創作經驗。在我看來,詩歌總與生活和心靈密不可分,生活為寫詩、為心靈提供明確的觸及,它讓日常的發生,在語言的條件下形成一個個程度不同的圖景或心靈境遇與心理的需要。當然,詩歌可以直面生活,但不能直陳,你不能讓詩歌又回到原初的生活狀態,你要在詩歌中把生活引向更深的層面,讓生活或心靈的某些瞬間、某些事件在詩意的擴張中不斷得到意義上的裂變與重生,而這些詩歌效果的產生不僅需要足夠的生活積淀,更需要掌控語言的能力與修辭技藝和良好的感知、感悟力、想象力等,它避免你粗制濫造,充當現場“直播”和寫出大量的庸常之作。
要想寫出有難度并有誠意的詩歌,破格與變形是種必需。古語說“詩貴出格”,我說的出格,實際上就是對原形“常格”的一種改變。拿什么改變?當然是靠詩人的審美、思維、視野、素養、修為、情趣、學識等多方面綜合的質素來改變。我認為詩歌最有效的表達,就是語言與想象力和內在情感的融合。它的特點就是打破傳統與常規的寫法,讓語言進行“偏離或者扭曲”,讓語言離開人們所習慣的軌道,有明確性的將某些詞語破壞然后重建,違背常理,運用反思維,恰當地使用悖論等,“使它所觸及的一切都變形”(雪萊語),這樣才有可能寫出獨出心裁、別有洞天的詩來。
詩歌不是再現生活,不是對外部世界的敘述,它是心靈的呈現和思想的深邃,是語言與想象力的藝術。要用詩的思維、詩的形式和詩的語言去建構。羅馬有位詩人賀拉斯說過這樣一句話:“一首詩僅具有美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魅力,必須按作者愿望左右讀者的心靈。”一首好的詩歌,總有某種魅力牽引著你,語言、結構、形式、音調、情感等。
海德格爾說:“詩人,是記憶的守護者,是一個詢問存在和語言問題的人。”在詩歌的路上,愿我們是那個“詢問存在和語言問題的人”。
姜慶乙:海德格爾的語言再發現,上升到宗教層面,重新確立詩歌地位。人類文明的種子,詩意的種子在大地上棲居。寫詩的原因在哪?點和動機在哪?詩歌有三種認識方式:分析方式、直覺方式、圣經中的方式。優秀的詩歌文本應具備這三種方式。
馬云飛:我很羨慕宮白云,在語言上敢于重組、陌生化具有一定素質。詩歌在語言上要有破壞力,再一個就是想象力。弦子的《關節痛》,就非常有想象力。頭一句的表達很直白,甚至是笨拙的,但第二句開始就給人一種想象,“我被含在一只蟲子的嘴里/一寸寸地蠶食/我身體里的森林,到“其實/這都算不了什么”,接受疼痛,接受植入,接受阿司匹林,甚至接受河水斷流于河床,太陽熄滅于泥土,但是這還沒完,這還是算不了什么,最終“我將以草木般順從的姿態/從身體里取出鹽分/又不斷在痛處上撒鹽”。 詩歌打破現行思維,給人一個立體的想象。按照陳中義的說法,最不認識的東西,就是最陌生的東西。
接著宮白云的發言,詩人們又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開來。
姜慶乙:首先是打破事物經驗的外殼,再呈現出語言新意。
王永利:詩歌發展史就是文本變化的歷史。這種變化就是讓詩歌有多種可能,《數字村莊》就是讓詩歌變形,詩歌有無限的可能,后來發展到當下,現代詩讓主體思想靈魂變形,無論是羅列、季節式的語言變化,詩歌的本質是創造可能,內容的可能,形式的可能。變形用千變萬化的形式表現詩歌,是詩人的使命。超現實主義,在于人有另一種真實,潛意識的真實。語言是詩歌的重要因素。
李世俊:寫詩的人談如何寫詩、寫好詩很有必要。但能不能跳出詩歌,反看詩歌。藝術是不應該分離的,比如用書法、攝影的角度看待詩歌。要求、標準、方式、方法都有變化,可以解決自我歷程的很多問題。跳出本身回看本身也很必要。
王永利:藝術如何產生,詩歌如何產生,其規律性、歷史性很重要。研究藝術的時候,只有獲得文本關照,才能更直觀地進行詩歌創作。
(弦子記錄整理)
〔責任編輯 叢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