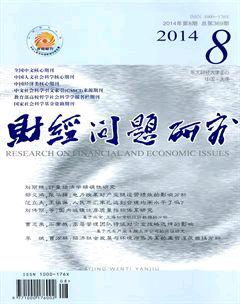轉型時期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宋科艷 曹明福
摘要:本文利用超越對數形式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采用一步法進行估計,測度了中國30個省區1981—2011年的農業生產效率,并分析了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研究發現:中國農業生產存在嚴重技術非效率,1981—2011年間中國30個省區的農業技術效率平均值只有055。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存在隨時間不斷下降的趨勢。人均農業GDP代表的人力資本和農業技術因素、有效灌溉率反映的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條件等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有積極影響,工業化程度、受災率以及財政支出占GDP比率反映的政府干預程度對農業生產效率有負面作用,農業GDP占全部GDP比重代表的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和農業機械動力密度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農業生產效率;農業GDP;技術效率
中圖分類號:F323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80118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8—2011年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59%,第一產業GDP年均增長455%,農業總產出和農業增加值均實現了快速增長。這一方面源自于農業機械、農藥和化肥等農業投入使用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則源自于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增長源泉的不同對中國農業發展的未來有著不同的意義。依賴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無限擴張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對人口眾多而資源稟賦又十分有限的中國而言并不可取;依靠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集約型增長模式是未來中國農業必須走的發展道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擴大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對農業產出增長的貢獻,才能實現中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是一項綜合性指標,它包括技術進步、效率改善、規模經濟、制度創新和專業化分工等多方面的內容,代表了要素投入以外的所有部分。一些學者把它的變化分解為技術進步、技術效率、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率。其中,生產可能性邊界的移動表示了技術進步的作用;技術效率衡量了在既定的技術水平和要素投入下,生產單元實現最大可能產出的能力,用實際產出與最大可能產出的比值表示,是效率的集中體現,本文的生產效率就是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則主要指生產規模報酬的變化對產出的影響;當價格信息已知且有合適的行為假設時,還可以計算出配置效率,它表示實際要素投入比例與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條件下新古典標準生產模型要求的要素比例的偏離情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趨勢如何?農業生產效率水平的變化在各個省區是否存在差異?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因素是什么?科學地回答這些問題一方面可以對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有更加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實現集約型增長及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很強的政策參考意義。因此,對中國農業生產效率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作用和政策意義。
二、文獻回顧
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生產前沿模型的引入,運用前沿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前沿方法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以數據包絡分析(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1-2];一是以隨機前沿分析(SFA)為代表的參數方法。
數據包絡分析是一種數據驅動型的方法,它通過線性規劃技術來確定生產前沿面,非常靈活,目前在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中已得到了廣泛應用[1-2]。李谷成[1-2]、時悅和趙鐵豐[3]、周端明[4]、方福前和張艷麗[5]、方鴻[6]郭軍華和李幫義[7]及曾福生和高鳴[8]采用DEA方法、超效率DEA方法或者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利用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對中國農業生產率進行了測度分析。但是DEA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無法進行統計上的顯著性檢驗;將隨機干擾對產出的影響也納入到技術效率當中;分析結果對數據十分敏感,極端數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很大等。
農業作為受自然因素影響非常大的產業,隨機性是分析中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但DEA方法無法將隨機干擾從技術效率中分離出來。SFA的最大優點是原則上能將影響產出變化的隨機因素(例如天氣變化、運氣的不同和數據的統計誤差)從技術有效性中分離出來。但是SFA方法需要預先設定某種特定的生產函數形式和技術非效率項分布形式,如果設定有誤,可能會導致很嚴重的分析誤差問題。SFA方法的這一缺陷限制了它在農業生產率研究中的廣泛應用,目前采用SFA方法的研究相對比較少。全炯振[3]、李谷成和馮中朝[4]等、匡遠鳳[11]、曾國平等[12]和彭代彥和吳翔[13]應用SFA方法對中國農業技術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分析,重點關注了技術效率對TFP增長的推動抑或抑制作用。SFA方法充分考慮到隨機因素對生產前沿面的影響,與農業生產的特征非常一致,對農業而言,SFA的應用前景應該更廣泛。此外,王兵等[14]、李谷成等[15]和劉玉海和武鵬[5]還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對中國農業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研究。
然而,現有的研究對影響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率的因素分析考察較少,Monchuk等[6]利用中國近2 000個縣的橫截面數據,首先運用DEA方法估計了農業生產效率指數,其次使用Tobit模型及半參數自導法解釋生產效率指數的差異,對中國農業生產非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方鴻[2]利用DEA方法測度了1988—2005年中國各省份的農業生產效率,再運用面板數據中的隨機效應Tobit模型對影響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了研究。劉玉海和武鵬[5]首先采用SBM-DEA模型估算了1985—2008年中國各省份的全要素耕地利用效率,在此基礎上應用受限隨機效應面板Tobit模型對全要素耕地利用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檢驗。
總的來看,非參數的DEA方法在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中已得到廣泛運用,參數的SFA方法逐漸成為新的趨勢。目前,對農業生產率進行測定的研究較多,對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研究還很缺乏。少數研究運用兩步估計方法,先估算出技術效率,再采用面板回歸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不具有理論上的一致性,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首先在時間維度上予以擴展,使用1981—2011年的中國30個省級單位的面板數據,應用SFA一步估計法,對生產函數和技術非效率項的形式采用更加一般性的設定,在發揮SFA方法優勢的同時力圖避免模型誤設帶來的偏差,對1981—2011年中國30個省區的農業生產效率進行測度,對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超越對數形式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采用一步法進行估計,測度了中國30個省區1981—2011年的農業生產效率,并分析了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研究發現:中國農業生產存在嚴重技術非效率,1981—2011年間中國30個省區的農業技術效率平均值只有055。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存在隨時間不斷下降的趨勢。人均農業GDP代表的人力資本和農業技術因素、有效灌溉率反映的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條件等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有積極影響,工業化程度、受災率以及財政支出占GDP比率反映的政府干預程度對農業生產效率有負面作用,農業GDP占全部GDP比重代表的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和農業機械動力密度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農業生產效率;農業GDP;技術效率
中圖分類號:F323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80118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8—2011年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59%,第一產業GDP年均增長455%,農業總產出和農業增加值均實現了快速增長。這一方面源自于農業機械、農藥和化肥等農業投入使用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則源自于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增長源泉的不同對中國農業發展的未來有著不同的意義。依賴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無限擴張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對人口眾多而資源稟賦又十分有限的中國而言并不可取;依靠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集約型增長模式是未來中國農業必須走的發展道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擴大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對農業產出增長的貢獻,才能實現中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是一項綜合性指標,它包括技術進步、效率改善、規模經濟、制度創新和專業化分工等多方面的內容,代表了要素投入以外的所有部分。一些學者把它的變化分解為技術進步、技術效率、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率。其中,生產可能性邊界的移動表示了技術進步的作用;技術效率衡量了在既定的技術水平和要素投入下,生產單元實現最大可能產出的能力,用實際產出與最大可能產出的比值表示,是效率的集中體現,本文的生產效率就是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則主要指生產規模報酬的變化對產出的影響;當價格信息已知且有合適的行為假設時,還可以計算出配置效率,它表示實際要素投入比例與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條件下新古典標準生產模型要求的要素比例的偏離情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趨勢如何?農業生產效率水平的變化在各個省區是否存在差異?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因素是什么?科學地回答這些問題一方面可以對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有更加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實現集約型增長及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很強的政策參考意義。因此,對中國農業生產效率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作用和政策意義。
二、文獻回顧
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生產前沿模型的引入,運用前沿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前沿方法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以數據包絡分析(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1-2];一是以隨機前沿分析(SFA)為代表的參數方法。
數據包絡分析是一種數據驅動型的方法,它通過線性規劃技術來確定生產前沿面,非常靈活,目前在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中已得到了廣泛應用[1-2]。李谷成[1-2]、時悅和趙鐵豐[3]、周端明[4]、方福前和張艷麗[5]、方鴻[6]郭軍華和李幫義[7]及曾福生和高鳴[8]采用DEA方法、超效率DEA方法或者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利用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對中國農業生產率進行了測度分析。但是DEA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無法進行統計上的顯著性檢驗;將隨機干擾對產出的影響也納入到技術效率當中;分析結果對數據十分敏感,極端數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很大等。
農業作為受自然因素影響非常大的產業,隨機性是分析中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但DEA方法無法將隨機干擾從技術效率中分離出來。SFA的最大優點是原則上能將影響產出變化的隨機因素(例如天氣變化、運氣的不同和數據的統計誤差)從技術有效性中分離出來。但是SFA方法需要預先設定某種特定的生產函數形式和技術非效率項分布形式,如果設定有誤,可能會導致很嚴重的分析誤差問題。SFA方法的這一缺陷限制了它在農業生產率研究中的廣泛應用,目前采用SFA方法的研究相對比較少。全炯振[3]、李谷成和馮中朝[4]等、匡遠鳳[11]、曾國平等[12]和彭代彥和吳翔[13]應用SFA方法對中國農業技術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分析,重點關注了技術效率對TFP增長的推動抑或抑制作用。SFA方法充分考慮到隨機因素對生產前沿面的影響,與農業生產的特征非常一致,對農業而言,SFA的應用前景應該更廣泛。此外,王兵等[14]、李谷成等[15]和劉玉海和武鵬[5]還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對中國農業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研究。
然而,現有的研究對影響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率的因素分析考察較少,Monchuk等[6]利用中國近2 000個縣的橫截面數據,首先運用DEA方法估計了農業生產效率指數,其次使用Tobit模型及半參數自導法解釋生產效率指數的差異,對中國農業生產非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方鴻[2]利用DEA方法測度了1988—2005年中國各省份的農業生產效率,再運用面板數據中的隨機效應Tobit模型對影響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了研究。劉玉海和武鵬[5]首先采用SBM-DEA模型估算了1985—2008年中國各省份的全要素耕地利用效率,在此基礎上應用受限隨機效應面板Tobit模型對全要素耕地利用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檢驗。
總的來看,非參數的DEA方法在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中已得到廣泛運用,參數的SFA方法逐漸成為新的趨勢。目前,對農業生產率進行測定的研究較多,對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研究還很缺乏。少數研究運用兩步估計方法,先估算出技術效率,再采用面板回歸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不具有理論上的一致性,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首先在時間維度上予以擴展,使用1981—2011年的中國30個省級單位的面板數據,應用SFA一步估計法,對生產函數和技術非效率項的形式采用更加一般性的設定,在發揮SFA方法優勢的同時力圖避免模型誤設帶來的偏差,對1981—2011年中國30個省區的農業生產效率進行測度,對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超越對數形式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采用一步法進行估計,測度了中國30個省區1981—2011年的農業生產效率,并分析了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研究發現:中國農業生產存在嚴重技術非效率,1981—2011年間中國30個省區的農業技術效率平均值只有055。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存在隨時間不斷下降的趨勢。人均農業GDP代表的人力資本和農業技術因素、有效灌溉率反映的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條件等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有積極影響,工業化程度、受災率以及財政支出占GDP比率反映的政府干預程度對農業生產效率有負面作用,農業GDP占全部GDP比重代表的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和農業機械動力密度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農業生產效率;農業GDP;技術效率
中圖分類號:F323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80118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8—2011年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59%,第一產業GDP年均增長455%,農業總產出和農業增加值均實現了快速增長。這一方面源自于農業機械、農藥和化肥等農業投入使用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則源自于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增長源泉的不同對中國農業發展的未來有著不同的意義。依賴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無限擴張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對人口眾多而資源稟賦又十分有限的中國而言并不可取;依靠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集約型增長模式是未來中國農業必須走的發展道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擴大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對農業產出增長的貢獻,才能實現中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是一項綜合性指標,它包括技術進步、效率改善、規模經濟、制度創新和專業化分工等多方面的內容,代表了要素投入以外的所有部分。一些學者把它的變化分解為技術進步、技術效率、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率。其中,生產可能性邊界的移動表示了技術進步的作用;技術效率衡量了在既定的技術水平和要素投入下,生產單元實現最大可能產出的能力,用實際產出與最大可能產出的比值表示,是效率的集中體現,本文的生產效率就是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則主要指生產規模報酬的變化對產出的影響;當價格信息已知且有合適的行為假設時,還可以計算出配置效率,它表示實際要素投入比例與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條件下新古典標準生產模型要求的要素比例的偏離情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趨勢如何?農業生產效率水平的變化在各個省區是否存在差異?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因素是什么?科學地回答這些問題一方面可以對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有更加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實現集約型增長及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很強的政策參考意義。因此,對中國農業生產效率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作用和政策意義。
二、文獻回顧
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生產前沿模型的引入,運用前沿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前沿方法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以數據包絡分析(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1-2];一是以隨機前沿分析(SFA)為代表的參數方法。
數據包絡分析是一種數據驅動型的方法,它通過線性規劃技術來確定生產前沿面,非常靈活,目前在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中已得到了廣泛應用[1-2]。李谷成[1-2]、時悅和趙鐵豐[3]、周端明[4]、方福前和張艷麗[5]、方鴻[6]郭軍華和李幫義[7]及曾福生和高鳴[8]采用DEA方法、超效率DEA方法或者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利用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對中國農業生產率進行了測度分析。但是DEA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無法進行統計上的顯著性檢驗;將隨機干擾對產出的影響也納入到技術效率當中;分析結果對數據十分敏感,極端數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很大等。
農業作為受自然因素影響非常大的產業,隨機性是分析中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但DEA方法無法將隨機干擾從技術效率中分離出來。SFA的最大優點是原則上能將影響產出變化的隨機因素(例如天氣變化、運氣的不同和數據的統計誤差)從技術有效性中分離出來。但是SFA方法需要預先設定某種特定的生產函數形式和技術非效率項分布形式,如果設定有誤,可能會導致很嚴重的分析誤差問題。SFA方法的這一缺陷限制了它在農業生產率研究中的廣泛應用,目前采用SFA方法的研究相對比較少。全炯振[3]、李谷成和馮中朝[4]等、匡遠鳳[11]、曾國平等[12]和彭代彥和吳翔[13]應用SFA方法對中國農業技術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分析,重點關注了技術效率對TFP增長的推動抑或抑制作用。SFA方法充分考慮到隨機因素對生產前沿面的影響,與農業生產的特征非常一致,對農業而言,SFA的應用前景應該更廣泛。此外,王兵等[14]、李谷成等[15]和劉玉海和武鵬[5]還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對中國農業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研究。
然而,現有的研究對影響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率的因素分析考察較少,Monchuk等[6]利用中國近2 000個縣的橫截面數據,首先運用DEA方法估計了農業生產效率指數,其次使用Tobit模型及半參數自導法解釋生產效率指數的差異,對中國農業生產非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方鴻[2]利用DEA方法測度了1988—2005年中國各省份的農業生產效率,再運用面板數據中的隨機效應Tobit模型對影響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了研究。劉玉海和武鵬[5]首先采用SBM-DEA模型估算了1985—2008年中國各省份的全要素耕地利用效率,在此基礎上應用受限隨機效應面板Tobit模型對全要素耕地利用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檢驗。
總的來看,非參數的DEA方法在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中已得到廣泛運用,參數的SFA方法逐漸成為新的趨勢。目前,對農業生產率進行測定的研究較多,對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研究還很缺乏。少數研究運用兩步估計方法,先估算出技術效率,再采用面板回歸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不具有理論上的一致性,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首先在時間維度上予以擴展,使用1981—2011年的中國30個省級單位的面板數據,應用SFA一步估計法,對生產函數和技術非效率項的形式采用更加一般性的設定,在發揮SFA方法優勢的同時力圖避免模型誤設帶來的偏差,對1981—2011年中國30個省區的農業生產效率進行測度,對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