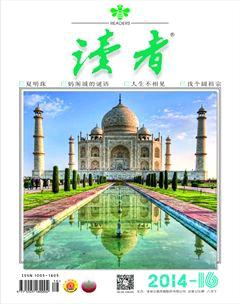謝謝收看
劉瑜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歲那年夏天的一個(gè)深夜。那天我又在鄰居楊麗麗家看了一晚上電視。先是楊麗麗困了上床睡覺去了,后來是她妹妹楊萍萍上床睡覺去了,再后來?xiàng)畎职帧顙寢尅钅棠倘Я松洗菜X去了。只有我,6歲的鄰居小朋友,還死皮賴臉地坐在他們家客廳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著一閃一閃的屏幕,目不轉(zhuǎn)睛地看完了一個(gè)又一個(gè)節(jié)目,直到電視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個(gè)大字:謝謝收看。
我只好戀戀不舍地回家去了,一邊鉆進(jìn)被窩一邊意猶未盡地回味著電視屏幕上的一切。這時(shí)候爸爸問我:“你在楊麗麗家都看了什么電視啊?”我思緒翻滾,但其實(shí)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于是腦子里靈光一閃,鄭重地告訴爸爸:“謝謝收看。”
之后就是我的初中時(shí)代,那大約是我一生中最蒼老的時(shí)期。那時(shí)候,為了傳說中金燦燦的未來,我學(xué)會(huì)了“存天理、滅人欲”這個(gè)變態(tài)哲學(xué),這一哲學(xué)最重大的表現(xiàn)就是不看電視。每天晚上吃完飯,我像個(gè)機(jī)器人一樣,啪,開始看書做習(xí)題。啪啪啪,做完了一切習(xí)題之后心滿意足地睡去。在這個(gè)過程中,另一個(gè)房間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個(gè)夢》等經(jīng)典電視劇卻在如泣如訴地上演。
上大學(xué)以后住宿舍,聽電視都不可能了。其間電視上發(fā)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劇里一個(gè)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給劈了個(gè)窟窿,我就接近崩潰了。什么啊,不就是個(gè)“武林至尊”的地位嗎,這么多年了,這么多電視劇,這么多演員,還沒分出高下啊。
到2000年年末,在紐約一個(gè)小公寓里再打開電視時(shí),我悲哀地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不愛看電視了。外國的電視劇和中國的一樣不好看。美劇分為午間的和晚間的兩類。午間的就是美式瓊瑤劇——總有一個(gè)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親爸爸,總有一個(gè)女青年在不該懷孕的時(shí)候懷孕了,總有一個(gè)好人聽信了壞人的讒言,總有一個(gè)壞人最后變成好人。晚間的電視劇就是美式武打劇——破案。當(dāng)然了,美式破案劇比中式武打劇還是稍微人道一點(diǎn),基本上沒有考驗(yàn)神經(jīng)的“號(hào)啕”片段。中國的電視劇,無論武打劇、家庭劇、破案劇、歷史劇,都有陣發(fā)性號(hào)啕防不勝防地出現(xiàn),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盤”。不過,美劇在這方面又走向另一個(gè)極端。美式破案劇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無表情、語氣冰冷,那些辦案人員似乎人人都見識(shí)過大世面,看到一具慘死的尸體,就像看到一塊石頭一樣無動(dòng)于衷。
讓我恢復(fù)對電視愛好的,是發(fā)現(xiàn)了各類情景喜劇和脫口秀。我之所以喜愛情景喜劇和脫口秀,是因?yàn)槠渲械膶υ捥貏e聰明,那小機(jī)智、小幽默,那線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殺,比乒乓球決賽還好看。
到了英國之后,我驚恐地發(fā)現(xiàn),英國人的電視節(jié)目里幾乎沒有情景喜劇和脫口秀。而英國的電視劇真不好看,既沒有中國式波瀾壯闊的號(hào)啕,也沒有美國式胸有成竹的緊湊。他們也有一兩個(gè)類似脫口秀的節(jié)目,一群喜劇演員聚在一起損政治家、電影明星、體育明星。那些殘酷的笑話,明顯賣弄的成分超過了娛樂的成分,所以我不愛看。如果說美式幽默是幫觀眾抓癢,英式幽默則如一把匕首飛過來,躲得過算你命大,躲不過算你倒霉。
英國的電視節(jié)目相對好看的是紀(jì)錄片和時(shí)政新聞,比如Panorama。就是通過這個(gè)紀(jì)錄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貧困階層有多窮,蘇丹的近況,聯(lián)合國的腐敗……時(shí)政新聞的好看之處在于,任何一個(gè)問題,主持人都會(huì)請正反兩方表達(dá)意見,但是英國的國內(nèi)政治,大多是雞毛蒜皮的爭執(zhí),正方反方似乎都是無聊方。
出國時(shí)間長,對國內(nèi)與時(shí)俱進(jìn)的電視業(yè)發(fā)展已經(jīng)無法追蹤了。每年回家,發(fā)現(xiàn)號(hào)啕的還在號(hào)啕,劈大山的還在劈大山。韓劇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個(gè)噴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紙巾來。
在美國的時(shí)候,我認(rèn)識(shí)一堆家里沒有電視的人。這些人有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就是很有文化。他們很清高,而電視則是很低俗的東西,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他們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電視。對此我很困惑:一、他們家來客人又沒話說的時(shí)候,他們的目光都往哪里投放呢?二、在他們懷疑人生的時(shí)候,通過什么方式來找到更倒霉的人,從而重新樹立生活的信心呢?三、如果他們家里有孩子,他們怎樣讓正在哭鬧的、滿地打滾的小朋友迅速恢復(fù)安靜呢?啊,小朋友多么熱愛看電視,至少有一個(gè)小朋友曾經(jīng)如此。很多年前的那個(gè)夏夜,她仰望著那個(gè)閃閃發(fā)光的小盒子,堅(jiān)持把所有的電視節(jié)目看了個(gè)底朝天,看到“謝謝收看”為止。她后來成了一個(gè)沒有故鄉(xiāng)的人,但是當(dāng)時(shí),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的世界從那個(gè)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裝著全世界的驚喜。
(如 花摘自上海三聯(lián)書店《送你一顆子彈》一書,本刊有刪節(jié),勾 犇圖)endprint